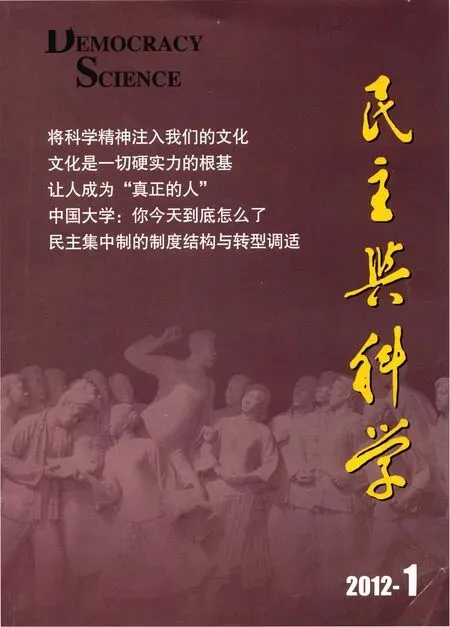再議科學精神
■若 水
科學精神,在近十幾年的黨中央文件、國家政策和社會宣傳中提到的不算少,但它真的在我們的精神家園占有一席之地了嗎?現實中,它成為先進文化的一部分,但它內化到社會文化與人們的素養中了嗎?這是值得再思考的問題。
如同科學沒有統一定義一樣,關于科學精神,眾說紛紜,但也不妨礙人們理解與使用。概括起來,大致有四個方面:一是求知和探索精神——人們從事一切科學認識活動的原動力;二是求真務實精神——科學認識的基礎和出發點;三是理性的懷疑與批判精神——科學精神的核心與靈魂;四是創新精神——科學的內在要求和本質。
我個人認為這些觀點雖然總結得很好,但沒有主次之分或層次遞進關系,又缺乏簡明性,不易被人記住。
現實中,一方面公眾常常被人“忽悠”,事后專家都在指責他們缺乏科學精神,但是公眾真的無從把握;另一方面,社會上多把科學精神的宣傳當作一個名詞說教,如同宣傳“馬克思主義”一樣,很少提到實際內容。由于空洞,不知所云,因而對其理解與把握就似是而非,不可能自覺運用,因此也不能形成一種很好的文化認同,扎根于社會與公眾中。相反一遇到有些人以科學精神之名任意“創新”“懷疑”“批判”,販賣迷信和偽科學時,社會思想就容易出現混亂。
科學精神到底應該怎樣向公眾表述,既簡潔又精準呢?我認為就四個字——實事求是。
這個觀點并非我的專斷,而是眾多科學家的共識。著名的自動控制專家、中國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胡啟恒說:“科學精神的本質就是實事求是。我們分析事物的來龍去脈時,一定是要分析事物包含了哪些內容,這些內容又怎樣決定了事物的性質。任何一個客觀存在的事物都是有原因的,它表現出來的現象都應該是可以解釋的。這些解釋要基于客觀事實,用科學的方法在事實的基礎上去分析、歸納,總結得出科學的結論。對于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問個為什么。如何解釋這些事物,首先就要相信世間任何物質都是客觀存在的,這就是科學精神。”我國科技史學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席澤宗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雖然研究對象不同,所用方法也有差別,但為擴大認識領域,尋找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一致的,它們都要求公正、客觀、實事求是,不允許偽造證據和做任何藝術的夸張,這種共性應該說就是科學精神……竺可楨是我國近代科學的主要推動者,他心目中的科學精神包括三個方面,是從近代科學家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開普勒、牛頓、波義爾等人身上總結出來的。一是不盲從、不附和,一切依理智為歸。如遇橫逆之境遇,則不屈不撓,不畏強暴,只問是非,不計利害。二是虛懷若谷,不武斷,不蠻橫。三是專心一致,實事求是,不作無病之呻吟,嚴謹毫不茍且。這三點歸納成兩個字:‘求是’。”
“實事求是”,既簡潔樸素,又深刻豐富,正所謂“大道至簡”。因為,我們只有立足于實事求是這個基礎,才會面對真實存在的問題去探索發現,而不會輕易相信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才會在現有的基礎上繼承與創新,而不是無中生有、毫無根據性地虛構;才會對出現了矛盾與謬誤的問題進行理性的懷疑和批判;才會對不同觀念與見解保持謙遜和包容的態度;才會團結協作、不帶偏見地解決問題。實事求是是科學精神的本質,是核心,其他的如求知和探索、求真和務實、理性的懷疑與批評、創新與協作等精神,都是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和圍繞它衍生和展開的。對老百姓而言,只要凡事問問“這是真的嗎”?或是老老實實地實事求是就行了。
科學的品格是樸素老實、平常而不華麗,平淡而值得信賴,應該最容易為公眾理解與接受,沒有必要把科學精神復雜化或“玄化”。席澤宗先生曾于1994年在《光明日報》上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科學精神”,表明科學精神在中國早就有,無非就是公正、客觀、實事求是。再次提出科學精神就是實事求是,其實是想在當今繁華浮躁的世界中,在社會上作假成風、信譽掃地、道德下滑的現實中,提倡回歸真理的樸素,呼喚回歸事物的本真。
在科學與社會公眾領域中,如何讓公眾提高科學文化素質,辨假識偽,不受迷信和邪教的侵害,提倡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還是非常必要的。
雖然歷經400多年的近現代科學發展,科學技術帶給人類物質和精神雙重文明,科學精神作為科學文化的主要內容之一,理應在社會公眾中形成共同的文化意識,并作用于日常生活與社會生活中。但是,現實情況并不樂觀。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國度里,科技發達,公眾科學文化素養相對較高,但依然有不少人相信各種超自然現象,聲稱相信占星術這類的迷信,相信批判達爾文進化論、推行智能設計論這樣的偽科學或“神創論”。同時,以復興傳統宗教為標志的新蒙昧主義,以“后現代”和“新時代運動”為標志的反科學、反理性主義,在世界尤其是美國十分流行。一些科學家、批評家們指出,這些現象的本質是對現代科學進行挑戰,是試圖拋棄科學的基本思想方法,拋棄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學理性精神。在我國,經過對近30年特別是取締“法輪功”后10年神秘主義思潮流變軌跡的研究,我們也可以看到,科學與迷信、偽科學、反科學在理論和實踐上仍在反復較量,科學精神遠沒有內化到社會文化與公眾素質中。弘揚科學精神還任重道遠。
我們不妨回顧這段歷史:從20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末,各種奇怪學說,比如辟谷,長生不老,返老還童,永動機,水變油,耳朵認字,隔墻見物,發外氣治病,遠距離發功使導彈航向改變,發功撲滅森林大火等反科學內容,經由社會各種途徑的不當擴散,混亂了公眾思想。由此,各種愚昧迷信包括洋迷信沉渣泛起,從“神功異能”到“偽氣功”造就神奇大師,再到產生李洪志這樣的邪教“教主”。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見》,2002年頒布了《科普法》,都提出了弘揚科學精神、破除迷信、反對偽科學的長期、復雜和艱巨的任務,很多科技工作者和社科工作者們也紛紛揭露和批評現代迷信與偽科學,批評超自然的神秘主義和反科學思潮,在取締“法輪功”之后,社會上也一度形成了“崇尚科學 反對邪教”、大力弘揚科學精神的宣傳氛圍。
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冰凍亦非一日能解”。打著“科學”、“傳統文化”和“宗教”招牌的現代迷信,諸如以“環境科學”為名的“風水術”和以“周易”為名的“科學算命”熱度不減;“占星術”、“相術”仍在社會暢銷;“非典”時期鬼神迷信回潮;在中學生中流行的“筆仙”巫術游戲導致悲劇;李一假道士和張悟本神醫等欺騙一時。這些違背科學的非理性的社會現象,直接腐蝕影響著公眾的思想靈魂,導致他們恐懼鬼神、追求神秘、陷于“宿命論”;而另一方面,如“為偽科學正名”、“科學也是迷信”、“反科學”、“反反偽科學”等各種叫囂,向科學提出挑戰。這些違背科學精神的社會現象,直接對社會價值的判斷標準,對公眾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使很多原本科學素質不高又不明真相的公眾,對科學產生懷疑,對現代社會世俗道德產生懷疑。
從上述情形看,科學與迷信、偽科學、反科學以及神秘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反復辯爭與較量,從來沒有停止過,只是各個時期表現形式不同而已。有人說,上述的迷信之類就像一只“沉不下去的橡皮鴨”,經過科學家、社會學家、新聞媒體的批評,沉寂一段時間后,又會重新浮出水面,只是在表現形式上因話題、事件、背景等不同而各式各樣。但它們所反映問題的實質是一樣的,即在科學與社會公眾領域中,是堅持科學精神的實事求是,還是要重新走蒙昧主義和神秘主義的道路。實際上,現代科學精神的普及不僅要從具體的迷信、偽科學、神秘主義的案例中,以圖書、活動、宣傳報道等為重點,澄清具體問題,而且要開始轉向科學與社會價值、公眾“三觀”的領域,即轉向社會文化建設領域。在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與教育中,加強對公眾的科學精神教育,形成一種“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的社會文化氛圍。
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決定》,提出了推動先進文化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任務。在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時候,科學精神不可缺項,它可以提高公眾科學文化素質,為我們社會文化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與支撐,是實現國家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因素。
希望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成為一種時代精神,注入我們的社會中,成為一種文化觀念,成為社會行為與評價的準則,成為一種社會價值取向,使社會空氣更加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