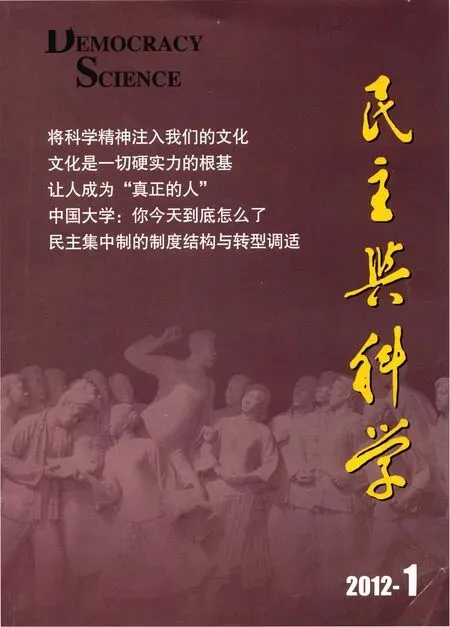猗蘭之思
——中西隱士文化的比較
■孫慕天
猗蘭之思
——中西隱士文化的比較
■孫慕天
日前看了《空谷幽蘭》一書,引起了許多聯(lián)想。
就是今年春節(jié)前后,關(guān)于終南山隱士的報(bào)道突然竄紅網(wǎng)絡(luò),緣起與比爾·波特關(guān)于終南隱士一書被譯成中文出版有關(guān)。比爾·波特(Bill Porter)是翻譯和闡釋中國古典著作的美國學(xué)者,中文筆名“赤松”。他曾于上世紀(jì)80年代訪問終南山的隱居者,并出版《Road to Heaven: Encounters with Chinese Hermits》( Mercury House,1995),直譯是《通天之路:邂逅中國隱士》。該書在西方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但直到十年后的2006年才譯成中文由中國當(dāng)代出版社出版,又等了五年由南海出版社再版才突然走紅,引起國內(nèi)記者循蹤訪幽探勝,拍照錄影,著文發(fā)聲,并在媒體上透露說,現(xiàn)在隱居終南者竟有5000人之多,一時(shí)間輿論大嘩:詫異者有之,感慨者有之,嘆惋者有之,艷羨者有之,追慕者有之,責(zé)難者亦有之。這是一個(gè)頗有意思的文化現(xiàn)象,是社會思潮泛起的漣漪,很值得反思。
明潔先生將波特此書譯成中文時(shí),書名改為“空谷幽蘭”,可謂別具匠心。幽蘭在空谷,孤傲高潔,一直是中國詩詞中經(jīng)典的美學(xué)意象。傳孔子作有《猗蘭操》,中有“習(xí)習(xí)谷風(fēng),以陰以雨。何彼蒼天,不得其所”,“時(shí)人暗蔽,不知賢者”之語,據(jù)云為“孔子傷不逢時(shí)而作”。后韓愈仿作《猗蘭操》亦有“蘭之猗猗,揚(yáng)揚(yáng)其香。不采不佩,于蘭何傷”,“君子之傷,君子何守”等句,抒發(fā)潔身自好、遺世獨(dú)立的情懷。后世以幽蘭自許、怨艾傷時(shí)的詩句不知凡幾。《通天之路》被譯者更名為“空谷幽蘭”,意在將當(dāng)代隱者比擬古之高士,確有褒義存焉。
我少年時(shí)代即已接觸到中國的隱逸文化。11歲那年讀到王維的山水詩,不知是因?yàn)槲淖州^為明快淺顯,還是因?yàn)槟乔逍碌诺囊饩嘲岛狭宋业奶煨裕幌伦颖惚晃×耍铝嗽S多名句,至今大多仍能背誦,當(dāng)時(shí)抄詩的那個(gè)筆記本還保存著。其中有王維的一首《田園樂》,是我的最愛,近日翻箱底,重見此詩,不由感慨系之。這是一首六言詩,流傳不廣,知之者稀,《王維詩選》雖有收入,僅為節(jié)選,未見全豹,所略去的頭兩首,恰恰是點(diǎn)睛之筆。這詩使我悟出了中國隱逸文化的神髓,值得全文引述:
厭見千門萬戶,經(jīng)過北里南鄰,
官府鳴珂有底,崆峒散發(fā)何人?
再見封侯方廣,立談賜璧一雙,
詎勝耦耕南畝,何如高臥東窗。
采菱渡頭風(fēng)急,策杖林西日斜,
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里人家。
萋萋芳草秋綠,落落長松夏寒,
牛羊自歸林巷,童稚不識衣冠。
山下孤煙遠(yuǎn)村,天邊獨(dú)樹高原,
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
桃紅復(fù)合宿雨,柳綠更帶朝煙,
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客猶眠。
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
南園露葵朝折,東谷黃粱夜舂。
據(jù)說六言詩起源于漢司農(nóng)谷永,歷來作者甚少。唐皇甫冉說“六言難工”,而王維此詩卻是六言中的極品,明黃升《玉林詩話》贊之曰“最為警絕,后難繼者”。就形式說,六言詩囿于“二二二”的節(jié)律,缺乏五七言那種關(guān)洪下注、長虹貫日的氣勢,板滯不暢,所以洪邁《容齋隨筆》也說六言“信乎其難也”。但凡事都有兩面,六言的這種凝重在大家手里卻化出雍容和雅、古淡悠閑的韻味,王維的這首《田園樂》正是把這種風(fēng)神發(fā)揮到了極致,用來表現(xiàn)隱者孑身獨(dú)處、飄飄出世、心與天合、陶然忘機(jī)的情懷,堪稱絕筆。胡仔《苕溪漁隱叢論》說,“‘桃紅復(fù)含宿雨’云云,每吟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閑適于其間也”,著實(shí)令人神往。
芳草寒松、孤煙遠(yuǎn)樹、柳綠桃紅、花落鶯啼,粗讀此詩,都會和胡仔一樣,陶醉于詩人摒絕塵囂、嘯傲山林的恬淡情思之中。但是,仔細(xì)玩味就會發(fā)現(xiàn),詩人別有用心,所謂“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詩的頭一首就說“官府鳴珂有底”,鳴珂,馬飾美玉,典出武周和玄宗兩朝顯宦張嘉貞,其人官至中書令(宰相),弟張嘉祜封金吾將軍,每朝“冠蓋騶從盈閭”,招搖過市,前呼后擁,不可一世,想來馬頭玉飾當(dāng)必光耀奪目,所居街坊即號“鳴珂里”;后因貪腐罹罪,兄嘉貞受牽遭貶,病死洛陽。王維生于公元701年,小嘉貞36歲,對此案想必知之甚詳。“底”者止也,“官府鳴珂有底”,是說仕途兇險(xiǎn),別看現(xiàn)在顯赫一時(shí),遲早有落幕那一天。離開官場是非之地,遁入山林,“崆峒散發(fā)”,才是上策。順便說,有的本子作“蹀躞鳴珂”,隱去詩人直面官府齷齪黑暗的厭惡之情,竊以為“官府鳴珂”其意更勝;所以第二首接著說,“再見封侯方廣,立談持璧一雙”,雖冠蓋如云,高俸厚祿,不如“耦耕南畝,高臥東窗”來得泰然瀟灑,怡然自適。詩中隱隱道出了自己退隱的深層動機(jī),完全是出于對仕途的厭倦。
王維可說是中國隱士階層的典型代表。他出身仕宦家族,21歲中進(jìn)士,隨即任大樂官步入仕途,所以他后來說自己是“少年識事淺,強(qiáng)學(xué)干名利”(《贈從弟司庫員外絿》)。王維一生主要混跡于官場,是典型的中國士大夫,仕途一波三折,對宦海沉浮,有著深刻的體味。大樂官大概相當(dāng)于時(shí)下文化部藝術(shù)司的領(lǐng)導(dǎo)吧,因伶人為皇帝享宴表演黃師舞逾制,王維“負(fù)有領(lǐng)導(dǎo)責(zé)任”,獲罪謫官外放,這是王維仕途的第一次挫折。直到公元733年32歲時(shí),他才回到長安干謁宰相張九齡,獻(xiàn)詩表明心跡:“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壯志滿懷,要為國家大干一番,所以急切地叩問“可為帳下不”(《獻(xiàn)始興公》)。果然得到張九齡的賞識,官拜右拾遺。不料好景不長,剛直的張九齡在朋黨斗爭中被權(quán)奸李林甫構(gòu)陷謫貶,王維雖未受重大牽連,但政見與李黨不合,始終未受重用,不得一申抱負(fù)。面對李林甫爪牙吉溫、羅希奭為首的特務(wù)政治(“羅鉗吉網(wǎng)”),王維只有委曲求全,“既寡遂性歡,恐招負(fù)時(shí)累”(《贈從弟司庫員外絿》。他官職凡七遷,卻并未急流勇退,而是始終戀棧,一味茍且因循,委屈求安,這是他仕途的第二次挫折。公元755年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fā),時(shí)任給事中的王維為敵俘獲,稱疾未獲免,迫任偽職,乃暗賦《凝碧池》詩,表達(dá)對國殤的哀思,題斥安祿山為“逆賊”。公元757年平逆后肅宗還朝,王維因《凝碧池》詩免罪,但仍遭薄懲降職為太子中允,這是王維仕途的第三次挫折。正是波詭云譎的官場,使他漸生倦意,萌生了退隱之心。早在張九齡貶官荊州時(shí),36歲的王維就興起了“方將與農(nóng)圃,藝植老丘園”(《寄荊州張丞相》)的念頭,并在終南山置了別業(yè),時(shí)不時(shí)在山水間“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他最早關(guān)于終南隱居的詩《終南別業(yè)》下限是天寶三年即公元744年,詩人43歲,自述“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寫出了“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shí)”的名句。但是,王維其實(shí)仍然沒有徹底辭官,而是一邊作官一邊隱居,因安史之亂降職后不久即復(fù)得寵招,58歲一年連升數(shù)次,做到尚書右丞,61歲死于任上。所以,王維是邊做官邊隱居,去終南別業(yè)頗像時(shí)下領(lǐng)導(dǎo)到自己在海南三亞的別墅稍事休閑,放松放松。
王維的隱逸觀核心在于仕途情結(jié)。一般說來,中國隱居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是仕途的順逆。隱居是官場失意后的最佳選項(xiàng),這首先是因?yàn)榭梢栽鍖W(xué)的正統(tǒng)言說作為理論根據(jù),使隱士身份堂而皇之地取得合法性。王維晚年所寫的《告魏居士書》對此有過綱領(lǐng)性的論述:“若有稱職,上有致君之盛,下有厚俗之化,亦何顧影局步,行歌采薇”,假若有能力當(dāng)官,治世撫民,又何必遁世隱居?自己求隱不過是因“足力不強(qiáng)”,上不能“裨補(bǔ)國朝”,下不能“博施窮窘”,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只好“偷祿茍活”,拿著官餉混日子,“誠罪人也”。所以,在王維心中,清高和從政并不矛盾,倒是把許由的毀瓢洗耳,嵇康的頓纓狂顧,陶潛的不恥折腰,看作是悖道之舉,“惡外者垢內(nèi),病物者自我”,毛病出在自己內(nèi)心。在朝在野只要此心耿耿,就“無可無不可”:生逢其時(shí),出將入相,經(jīng)世濟(jì)民;生不逢時(shí),退隱江湖,韜光養(yǎng)晦。這篇《告魏居士書》可稱之為“中國隱士宣言”,其思想源頭直溯孔子。孔子反對不問世事、消極遁世的隱逸觀,“無可無不可”一語就出自《論語·微子》篇。孔子評價(jià)了古代隱士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雖然肯定他們高尚的品德,但結(jié)論卻是“其斯而已矣”,也不過如此罷了,就是說,不能認(rèn)為只有做一個(gè)世外高人才是正確的人生道路;孔子宣稱:“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我和他們不一樣,沒有什么可以的,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的。孔子的意思是,入世為官和出世退隱,無論是進(jìn)是退,行仁義的目標(biāo)是不能放棄的。《論語·述而》提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為官之道,并且說只有自己和得意弟子顏回才能做到,“唯我與爾有是夫”,可見這是一個(gè)高標(biāo)準(zhǔn)。此后“用行舍藏”就成了中國士人模范的為官準(zhǔn)則。王維就此發(fā)揮說,“用舍又時(shí),行藏在我”,識時(shí)務(wù)者為俊杰,要審時(shí)度勢,何時(shí)行何時(shí)藏,看自己是否知機(jī),不能逆勢而為。在送友人綦母潛棄官南歸的詩中,王維嘆息說,“明時(shí)久不達(dá),棄置與君同”,“微物縱可采,其誰為至公”,沒有遇上好的政治環(huán)境,自然要被邊緣化,縱然一身本事,誰會來賞識你?不是不想入仕,而是無人識荊,報(bào)國無門,無奈只好“余亦從此去,歸耕為老農(nóng)”了。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對這一原則做了完美的詮釋,“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yuǎn),則憂其君”,時(shí)時(shí)處處以天下和蒼生為念,“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換言之,廟堂也罷,江湖也罷,在朝在野,仕進(jìn)退隱,不過是處境造成的生活方式轉(zhuǎn)換,而生命的基本價(jià)值取向是不應(yīng)改變的,所以說“微斯人,吾誰與歸”,這才是做人的最高標(biāo)準(zhǔn)啊!
總之,古人雖不乏長沮桀溺、巢父許由這樣的“純隱士”,但被主流文化所認(rèn)同的隱逸觀還是孔子的“用行舍藏”論。理想的模式是隱以待時(shí),期望有機(jī)會復(fù)出一申抱負(fù),得償建功立業(yè)的夙愿。最受推崇的范本是謝安的東山再起。謝安,字安石,東晉人,“累違朝旨,高臥東山”,隱居會稽山陰二十年;赴江陵時(shí)有中丞高崧者送行,揶揄說:“人們都說:‘安石不出,如蒼生何’?”你不出山,老百姓怎么辦啊?直到年逾40,奉詔入朝,阻止了恒溫篡權(quán)陰謀,并于公元383年指揮淝水之戰(zhàn),打敗了苻堅(jiān)80萬大軍,保住了東晉半壁江山,所謂“暫因蒼生起,談笑安黎元”(李白:《書情題蔡舍人雄》),傳為千古美談。李白也許是謝安最著名的粉絲,詠嘆這位名士的詩竟達(dá)15首之多,主要是因?yàn)槠淙似鹾狭嗽娙说娜松硐搿@畎纂m然糞土公侯,笑傲江湖,詩酒煙霞,游戲人間,其實(shí)從未放棄政治理想。早在《與韓荊州書》中,他就毛遂自薦,袒言“心胸萬夫”,要韓賜予“階前盈尺之地”,使自己得以“揚(yáng)眉吐氣,激昂青云”。他心中的標(biāo)桿正是這位“談笑靜胡沙”的東山謝安石。“小隱慕安石”,希望自己“小隱”后也能如謝公一樣,“入侍瑤池宴,出陪玉輦行”,得獲寵信,執(zhí)秉國鈞,兼濟(jì)天下,治國安邦,“談笑遏橫流,蒼生望斯存”(《秋夜獨(dú)坐懷故山》)。遵循孔子遺教,退隱并不是心如槁木,茍全性命,而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闕,所以李白對許由頗有微辭,認(rèn)為他以接詔拜官為聞惡聲,洗耳自高不過是沽名釣譽(yù),主張與其洗耳,不如洗心,退隱以后,好好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yǎng):“歸時(shí)莫洗耳,為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買名”,歸根結(jié)底,是應(yīng)當(dāng)像謝安一樣,高臥東山仍然不忘經(jīng)國安民的宏愿:“謝公終一起,相與濟(jì)蒼生。”(《書情題蔡舍人雄》)
遵循“用行舍藏”原則的隱者,是儒家思想的守護(hù)者,是主流派。漢末以降,特別是魏晉兩百年間,社會陷入空前的動亂和黑暗之中,統(tǒng)治集團(tuán)血腥、殘暴,無序而又短命,仕人的處境異常險(xiǎn)惡,命運(yùn)乖蹇無常,社會心理與傳統(tǒng)儒家的理念發(fā)生激烈沖突;相應(yīng)地隱者心態(tài)也發(fā)生了變化,出現(xiàn)了對正統(tǒng)隱逸觀的偏離,另類隱者隨之應(yīng)運(yùn)而生。近來有人把中國隱士歸納為十類,為了更準(zhǔn)確,這里略加修正列舉如下:真隱全隱,半官半隱,假隱虛隱,先官后隱,忽官忽隱,名隱實(shí)官,以隱求官,無奈而隱,真隱后仕,暗隱于朝。這一分類,其實(shí)是現(xiàn)象學(xué)的,如果按隱者的精神走向分類,我以為不外乎三派:
第一類是縱情派。朝綱失紀(jì),上層腐敗糜爛,“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三綱五常的儒家倫常土崩瓦解,這促使士人重新思考生命的價(jià)值和主體的定位。一些上層知識分子向自我回歸的道路就是走向“越名任心”,擺脫禮教的枷鎖,“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們雖常遁跡林泉,有時(shí)則不遠(yuǎn)離市廛,但無論在哪里,卻都狂放任達(dá),縱酒狂歌,蔑視世俗禮法,行事乖張荒誕,世稱名士風(fēng)流,“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和嵇康就是這一派的代表。阮籍在司馬氏王權(quán)的淫威之下,常以驚世駭俗的言行,隱蔽于朝市,迷惑當(dāng)權(quán)者。他常大醉終日,既以縱情,亦以避禍。母喪飲酒二斗,吐血數(shù)升;晉武帝為子求婚,他飲酒大醉六十日,搪塞過去;醉臥當(dāng)壚少婦之側(cè),為不相識美女吊喪;駕車胡亂穿行,走到盡頭則慟哭返回,“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凡此種種給他披上了一層保護(hù)色,隱匿了反抗現(xiàn)實(shí)的內(nèi)心世界。阮籍并非沒有中國士子普遍懷抱的仕途夢,他同樣期待著帝王的召喚,“王業(yè)須良輔,建功俟英雄”,以求大展宏圖,青史留名,“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后世,氣節(jié)故有常”。但是,他認(rèn)識到盛世不再,時(shí)乖運(yùn)蹇,“陰陽有舛錯(cuò),日月不常融”(《詠懷詩》),時(shí)勢是“虐興賊生”,“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qiáng)者睽視而凌暴,弱者憔悴以事人,假廉以成貪,內(nèi)險(xiǎn)而外仁”(《大人先生傳》)。世情澆漓,國事蜩螗,自身難保,遑論仕途?所以這種佯狂乖張任性而為的行徑,只是“用行舍藏”理念的特殊表現(xiàn)。阮籍傾吐心曲說:“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詠懷詩》)這是一種無奈,但也不違圣訓(xùn)。子曰:“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這說的是衛(wèi)大夫?qū)幬渥樱赫吻迕骶吐斆鳎位璋稻脱b傻,我輩聰明也許跟寧某人有一拼,裝傻就難與比肩了。看來這種縱情佯狂倒是一種難以企及的境界呢!
第二類是悲情派。陶潛生活在晉宋(劉宋)換代之際,整個(gè)人生是在仕與隱的矛盾中展開的。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人,他早年同樣懷抱著內(nèi)圣外王、匡世濟(jì)民的雄心壯志,心態(tài)是昂揚(yáng)激越的:“進(jìn)德修業(yè),將以及時(shí);如彼稷契,孰不愿之”,蓄勢以候,等待時(shí)機(jī),干一番堪比古圣先賢的事業(yè)。直到40歲時(shí),數(shù)度為官,卻均為小吏,不能一展才華;但還心存幻想,以為自己尚有可為:“先師遺訓(xùn),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詩》),還想振作一番,來一個(gè)大器晚成。然而事與愿違,揚(yáng)眉吐氣的希望完全幻滅了:一個(gè)顢頇俗吏,只因官大一級就可以對他頤指氣使。彭澤令任上,督郵以上官蒞縣,令須“束帶見之”,陶潛拂袖而去:“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xiāng)里小人邪!”遂掛冠而去,歸田園居。詩人的怨怒是長期積郁的爆發(fā),他閱盡滄桑,備受欺凌,看透了官場的傾軋虞詐。但與阮籍不同,他已出離憤怒,在道釋兩家思想中找到了思想支點(diǎn),“人生似幻化,終當(dāng)歸虛無”(《歸田園居》),理想失落的痛苦,在本體論的虛無妙諦中得到了解脫,對功名利祿的幻滅感,成為陶詩的基調(diào)。“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怨詩楚調(diào)示龐主簿鄧治中》),“去去百年后,身名同翳如”(《和劉柴桑詩》),他已失去了“用行”的期望,對仕途悲觀絕望,只能以回歸自然撫慰心靈創(chuàng)傷,隨遇而安,詩酒自娛,以此自終,“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fù)奚疑”(《歸去來辭》)。不過,士的傳統(tǒng)是根深蒂固的,悲觀中常不能忘情于儒家理想的烏托邦,所以仍然在《桃花源記》中書寫心中的樂園,偶爾也歌詠荊軻,慨當(dāng)以慷,發(fā)出“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讀山海經(jīng)》)。那種金剛怒目式的吼聲,可見陶潛的悲情式隱逸仍是正統(tǒng)隱逸理念的特殊變體。
三是矯情派。正統(tǒng)儒者是以入仕為官、建功立業(yè)為士人本分。子貢曾問孔子,如果有美玉,是藏在箱子,還是等著好價(jià)賣出去?孔子明確地回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論語·先進(jìn)》),賣掉,賣掉,我是在等待識貨者哩。當(dāng)然,上品人物如南陽諸葛、東山謝安是謀猷籌畫、養(yǎng)精蓄銳、審時(shí)度勢、選擇進(jìn)路,準(zhǔn)備憑真本事治國平天下,既不怨天尤人,也不干進(jìn)務(wù)入,自有明主三顧茅廬。但也有一些待價(jià)而沽的隱者,時(shí)或抒發(fā)隱逸之情趣,雖不乏真情實(shí)感,但總是怨誹自憐,流露出對金闕紫綬的艷羨,干求晉身,一付急不可耐的模樣,而為其博得社會聲譽(yù)的隱者形象,倒顯得鏤冰刻脂、矯情遏性了。李白稱贊孟浩然“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表示“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贈孟浩然》)。孟詩的疏朗清淡的韻致早有定評,那種飄逸悠遠(yuǎn)的情思一直使我為之傾心,至今仍然時(shí)常吟誦。但是,毋為賢者諱,如論者所說,孟浩然確實(shí)難入清高之品。他年輕科舉落第,終生未仕,卻既未如阮籍憤俗疾惡,佯狂忤世,也不像陶潛徹悟人生,出世離塵。他時(shí)時(shí)流露躋身仕途的夙愿和對仕進(jìn)的渴想,“執(zhí)鞭慕夫子,捧檄懷毛公。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固窮”(《書懷貽京舍故人》),明說自己不能安貧樂道。“為學(xué)三十載,閉居江漢陰”,襄陽高臥,所為何來?念茲在茲的是“沖天羨鴻鵠”(《秦中苦雨思?xì)w贈袁左丞賀侍御》),要像揚(yáng)雄那樣獻(xiàn)《甘泉賦》,一朝為皇帝賞識青云直上。可惜,時(shí)不我與,干謁無門。“當(dāng)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留別王維》),只能不停地宣泄懷才不遇的郁悶,到處表白被邊緣化的委屈:“今日龍門下,誰知文舉才”(《姚開府山池》),逢人便拜求晉身之階,“欲濟(jì)無舟楫,甘居恥圣明”(《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有誰能使我“青萍結(jié)綠,長價(jià)于薛卞之門”?“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在巧妙的詩筆掩飾下,對功名祿位的垂涎之情溢于言表。孟詩中那首傳誦不絕的名篇《歲暮歸南山》說:“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滿紙牢騷:說“不才”正是懷才,感嘆無人賞識;說“明主”正是昏君,指責(zé)埋沒賢良;說“故人疏”,實(shí)是為人棄,抱怨無人引進(jìn)。傳說孟浩然被王維邀至內(nèi)署,恰遇玄宗,向孟索詩,孟有意讀了此詩,玄宗聽出話音,不快地說:“卿不求仕,而朕不誤卿,奈何誣我?”(《唐謶言》卷十一)你隱居避仕,不想為官,我不是不用你,而是成全你的志向,你干么誣陷我呀?這真是適得其反,表演過分了。有人認(rèn)為,孟浩然隱居不過是以退為進(jìn),是“曲線做官”,他被皇帝誤讀為“不求仕”,是弄假成真。不過在我看來,這樣說孟浩然也有點(diǎn)過度詮釋,有些矯情倒是不假,明明熱衷仕途,卻裝出一付超脫的樣子,但這是他內(nèi)心矛盾的表露,并非作偽。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語境下面,這樣的心理扭曲是歷史所使然,而孟浩然的詩歌成就和他內(nèi)心的這種糾結(jié)掙扎是分不開的,我們還是不要苛求前人吧。當(dāng)然確有等而下之者,借隱居沽名養(yǎng)望,酷似《紅樓夢》中的官迷賈雨村:“玉在匧中求善價(jià),釵于奩中待時(shí)飛。”南齊孔稚珪《北山移文》,是開同僚周顒的玩笑。周顒雖不是文中所說的那種人,但文章是指桑罵槐,意在鞭笞假借隱逸之名張揚(yáng)造勢,伺機(jī)以求聞達(dá)的卑污行徑,嘲諷假隱士心懸爵祿,欺騙松桂云壑,一旦得遂官欲,便“敲撲喧囂,牒訴倥傯”,官態(tài)十足,俗氣沖天。這篇文字是中國隱士文化中的奇文,雖是一篇游戲文字,卻有強(qiáng)烈的針對性,蘊(yùn)含著深刻的社會學(xué)意義,成為膾炙人口的名文,并被收入《古文觀止》,可謂童蒙皆知。明人陳繼儒是這類假隱士的現(xiàn)實(shí)標(biāo)本,他曾隱居小昆山,卻奔走于官紳豪門,清蔣士銓的傳奇《臨川夢·隱奸》諷刺他是“翩然一只云中鶴,飛來飛去宰相家”,活畫出這類矯情隱者的虛偽嘴臉。魯迅在《隱士》一文中一針見血地點(diǎn)明了此中關(guān)竅:“登仕,是噉飯之道,歸隱,也是噉飯之道”,隱與官其道一也,一樣利欲熏心;魯迅引唐末左偃的《寄韓侍郎》詩“謀隱謀官兩無成”,總結(jié)說:“七個(gè)字道破了所謂‘隱’的秘密。”
說到底,中國的隱逸文化其實(shí)是中國社會官本位特質(zhì)的一種表現(xiàn)。傳統(tǒng)上中國社會控制的核心是官吏階層,官者,管也,官為民之宰,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中軸就是對官僚治理機(jī)制的維護(hù)。對士人而言,他的生命活動是被這個(gè)主軸帶動而運(yùn)轉(zhuǎn)的,或正向或反向,總是與為官作宰緊密相關(guān)的。在正相關(guān)的向度上,士人們焚膏繼晷,兀兀窮年,擢高科,登顯士,“仕宦而至卿相,富貴而歸故鄉(xiāng),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歐陽修:《相州晝堂記》),就是俗話所說的“學(xué)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這是中國傳統(tǒng)精英的正途。反過來,如果時(shí)運(yùn)不濟(jì),命途多舛,造成仕途坎坷,在負(fù)相關(guān)的向度上,就會出現(xiàn)逆反:對于仕途,清高之士逃避或鄙棄,失意之士哀怨或絕望,耿介之士詈罵或抗?fàn)帲渲须[逸就是為官的一種逆向選擇。所以,隱逸和仕進(jìn)不過是中國官本位文化的一體兩面而已。
有趣的是,中國隱逸思想中,一直存在著將兩者統(tǒng)一起來的努力,其中最有影響的命題就是“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西漢時(shí)東方朔寫過《非有先生論》,大談伴君如伴虎,討論了“養(yǎng)命之士”如何“避世以全其身”的隱逸山林之道。該文似乎意猶未足,這位曼倩先生又根據(jù)自己的從政實(shí)踐,補(bǔ)充了一個(gè)“避世于朝廷間”的對策,這是“朝隱”論的濫觴。西晉郭象在《莊子注》中已經(jīng)提出:“圣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在朝與歸隱只是外在境遇的變化,內(nèi)心一以貫之,所以本無所謂朝野。殆至東晉,王康琚《反招隱詩》與傳統(tǒng)隱逸論大唱反調(diào),喊出“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的口號,公然把朝市之隱奉為高出山林之隱的“大隱”,認(rèn)為隱于野傷身促壽,違背自然和人性,“矯性失至理”。同為東晉人的鄧粲則為朝隱論做出了進(jìn)一步的論證。《晉書》說鄧粲“道廣學(xué)深,眾所推服”,但卻應(yīng)刺史恒沖之聘出任別駕,好友劉尚公、劉驎之說他“忽然變節(jié),誠失所望”。這位鄧粲是隱逸理論的創(chuàng)新者,他振振有詞地回應(yīng)二劉說:“足下可謂有志于隱而未知隱,夫隱之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于物。”明確提出“朝隱”和“市隱”的概念與傳統(tǒng)的“野隱”并立,指出隱之道不在外物,而在內(nèi)心,只要心地空靈,在朝在市,又有何妨?鄧粲的朝隱論對后世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為留戀官場又清高自許(或真心或釣譽(yù))的行為,提供了頗有說服力的理由。王維就根據(jù)這種理論重新解釋了“適意”的本質(zhì),認(rèn)為“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jì)仁為適意”(《與魏居士書》),所以或朝或野,只求心之所安,無可無不可。在探索仕與隱統(tǒng)一之途方面,白居易更有重大的突破,提出了“中隱”論,他在《中隱》詩中分析說:“大隱往朝市,小隱入樊谷丘。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什么是留司官?就是無實(shí)權(quán)亦無重責(zé)的閑官、散官,既沒有朝市重臣的風(fēng)險(xiǎn),也沒有山林荒野的孤苦,而且照食俸祿,“致身吉且安”,何樂而不為。中隱思想有宋一代大受眾多士人的青睞,龔宗元、司馬光、王安石、蘇軾、陸游、范成大、張孝祥等名流都是中隱論的擁躉,他們還創(chuàng)造了中隱的近義詞“祿隱”、“半隱”、“吏隱”,真是妙不可言。北宋初年有個(gè)張去華,甚至還修了個(gè)亭子就叫“中隱亭”。司馬光一語道破了天機(jī):“既知吏可隱,何必棄軒冕”(《登封龐國博年三十八自云欲棄官作吏隱庵于縣寺俾光賦詩勉率塞命》),既然能夠兩全其美,棄了官去隱居,不是傻帽是什么?
總而言之,我的感覺是中國隱士文化本質(zhì)上是仕途文化的流變,名為隱逸,實(shí)為變相的政治。當(dāng)然,這是就主流而言,屬意于修行悟道的純隱者不是沒有,但那是支脈,不入正統(tǒng)。反過來,西方的隱士文化卻迥乎不同,英語中隱士一詞常用hermite,引申為hermitage,指隱居生活或隱士住處,來自希臘文ερημιτηζ,原意是野居者。常用的另一個(gè)詞anchoret或 anchorite,是隱居修道的人,而recluse則是指幽居遁世的人。后來,在基督教中出現(xiàn)了專門隱居修行的修士,又有了專門的名詞monk,源于希臘文μοναχοζ,意為離群索居的孤獨(dú)者,中文譯成隱修士。深入考察可以發(fā)現(xiàn),西方隱士文化的主流是出世和屬靈,與政治和官場很少有關(guān)聯(lián),倒是和宗教的發(fā)展密切相關(guān)。牛津版《人人百科全書》對anchorite的注釋是:“摒棄與同時(shí)代人的一切交往致力于靈修而自愿隱居的人。”
這類西方隱者的先驅(qū)似乎是施洗約翰(John the Baptist),“那孩子漸漸長大,住在曠野”(路,1:80),他過的是沙漠中的生活,是苦行者,穿野駱駝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蟲和野蜜。施洗約翰的隱修負(fù)有“預(yù)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太,3:4)這一神圣使命。后來,耶穌也在曠野隱修過,禁食40晝夜,受魔鬼的試探(太,4:1-2),也許基督教后來的隱修模式就是從這里發(fā)源的。這種隱居的要件是:第一,目的是靈修,提高自己的靈性;第二,遠(yuǎn)離塵囂,遁入條件惡劣的沙漠或曠野;第三,禁欲苦行,不僅將生理需要降到最低限度,而且用種種殘酷的手段折磨肉身,以砥礪信仰。第一個(gè)這樣的隱修士是埃及特貝德的保羅,隱修修道的奠基人安東尼就是他的追隨者。此后的公元三、四世紀(jì),隱居靈修在埃及中部和尼羅河三角洲一帶盛行起來。與此同時(shí),帕克米烏在尼羅河的小島塔本納上創(chuàng)立了第一個(gè)隱修院,建立了集體隱修制度,其核心就是所謂“三絕誓愿”:絕財(cái),絕色,絕意。隱修主義對基督教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通過苦修和禁欲進(jìn)達(dá)于神性,在長時(shí)間內(nèi)左右著基督教的宗教生活。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中西隱士文化的根本差異。中國隱逸文化是入世的,人性的;西方隱修文化是出世的,神性的。不像中國的隱者,悠游于青山綠水,享受幽靜閑適之樂,恬淡怡然,心靜如水;西方隱士則要嚴(yán)酷地壓抑自己追求安樂的天性,要把肉體的需要當(dāng)作魔鬼,以自虐的方式通過生理上的忍苦,獲得神性,而節(jié)欲和自我折磨就成了衡量靈修程度的基本指標(biāo)。在埃及隱修士中甚至出現(xiàn)了苦行上的比拼,競相突破所能忍受的最低生理底線,被稱作“競技者”。例如當(dāng)聽到別人每天吃一磅面包時(shí),就有人立刻把自己的定量降到四英兩;有一個(gè)苦修者甚至在沙漠的石柱上枯坐了四十年。更重要的是,中國隱士時(shí)刻縈懷的是在仕途上的得失利害,或等待,或企慕,或憤懣,或鄙棄,或失望,或幻滅;西方隱士刻意尋求的卻是在靈性上的超越提升,或讀經(jīng),或祈禱,或齋戒,或懺悔,或自苦,或冥想。中國隱士所求于隱逸的,或是為今后復(fù)出官場獲得精神上的準(zhǔn)備,或是為仕進(jìn)中的挫折失意獲得精神上的補(bǔ)償;而西方隱士所求于隱居的,則是戰(zhàn)勝“罪惡的”人欲,獲得靈魂的凈化以博取神的眷顧。中國稱隱士生活為隱逸,一個(gè)“逸”字,道盡其中奧妙。
我們不妨比較一下中西方兩位隱者的文字:
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崗,輞水漣漣,與月上下。寒山遠(yuǎn)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fù)與疏鐘相間。此時(shí)獨(dú)坐,僮仆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dāng)侍春中,草木蔓發(fā),春山可望,輕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斯之不遠(yuǎn),儻能從我游乎?非子天機(jī)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wù)相邀?然是山中深趣矣。(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
當(dāng)那達(dá)到了靈性之完美的靈魂,洗凈了一切情欲,同保惠師圣靈神交默契之后,它便也成了靈,與圣靈親密結(jié)合在一起。由此它乃成為全光明,全洞見,全靈性,全喜樂、宏福和歡愉,全仁愛和憐憫,全善意和友好的了。(馬卡里烏講道錄)
馬卡里烏是四世紀(jì)埃及的隱修士,以嚴(yán)格苦修著稱。這里是兩種迥然不同的隱居生活,有著兩種目標(biāo)迥異的追求。一個(gè)陶醉在美景中,盡情享受感官的愉悅,流連徜徉,怡然自樂,神游于天機(jī)清妙;另一個(gè)卻克制肉體享樂,壓抑感官需求,洗凈一切情欲,回到內(nèi)心世界,進(jìn)入神秘的精神幻境。中國隱士求今世的身心安逸,“逍遙撰良辰”(左思:《招隱詩》),“歲駕從所欲”(陸機(jī):《招隱詩》),逍遙自在而從心所欲;西方修士要摒絕欲念,攻心虐身,以身心康泰為敵。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是入世的,正統(tǒng)儒家也主張不違天人之本,例如孔子聽韶樂也曾入迷而三月不知肉味,他明言向往“浴乎沂,風(fēng)乎舞雩,詠而歸”的瀟灑人生。西方宗教文化的主體則是出世的,認(rèn)為人背負(fù)原罪,必須時(shí)時(shí)刻刻與心中的魔鬼斗爭,以致隱修院對修士的思想規(guī)約竟多達(dá)72條,要他們“每天想到死就在眼前”。顯然,善生和惡生成為中西隱者文化的另一重要區(qū)別。
也許在這一點(diǎn)上,中國的隱士文化更合乎人性。扭曲天性的隱修影響了整個(gè)基督教的信仰生活,靈與肉的沖突成為靈修的主題。文藝復(fù)興以來,啟蒙思想謳歌了人性的美好,首先就是向中世紀(jì)的禁欲主義宣戰(zhàn),從而促成了近代西方社會的世俗化,這是偉大的歷史進(jìn)步。我少年時(shí)讀法國作家法朗士的小說《泰綺絲》,留下了深刻印象。小說的基本情節(jié)是,苦修士巴甫努斯要拯救當(dāng)紅妓女泰綺絲的靈魂,將其送進(jìn)修道院,結(jié)果自己反倒瘋狂地愛上了泰綺絲,為擺脫情欲的熬煎,他逃往沙漠,苦苦地折磨自己,但始終無法壓抑對泰綺絲的思念,終于決定放棄一切向她求歡。但是,當(dāng)他趕到修道院時(shí),泰綺絲已病入膏肓,處于彌留之際,靈魂隨即升入天國。小說深刻說明了對天性的壓制是不合理的,也是無效的。魯迅在談到《泰綺絲》時(shí)說:“我寧愿向潑辣的妓女立正,卻不愿意和死樣活氣的文人打棚。”
但事情總是辯證的,過分的入世使人耽于生理和心理上的愉悅,在遠(yuǎn)離世事的環(huán)境中,這樣的隱逸生活就成了純粹消極的茍活,消弭了創(chuàng)造性的精神探求和激情。而西方的隱修生活,在極端專注和高度緊張的精神活動中,強(qiáng)化了人的思維能力,在宗教神學(xué)的外殼下,不斷開拓著思索的空間,并提高了思辨能力,為歐洲后日的宗教改革和文藝復(fù)興創(chuàng)造了形而上學(xué)的前提。伊莎貝爾·科爾蓋特的名著《曠野上的鵜鶘:隱士,孤獨(dú)與遁世者》全面梳理了東西方古今各類隱者,認(rèn)為他們唯一共同之處就是孤獨(dú),作者認(rèn)為“孤獨(dú)是地獄,是憂郁癥和致幻的泥沼”;但是,“孤獨(dú)也是靈魂與自己相逢,是自我更新的機(jī)會,從這里會重新跳出公眾的舞蹈”。放縱情欲,任憑生理本能恣意發(fā)泄,畢竟不是人類文明的正途。要肯定人的正常欲求,但又必須用理性控制和引導(dǎo)本能欲求,使人從本我提升到自我,進(jìn)而進(jìn)達(dá)于超我。古今中外各種文明都強(qiáng)調(diào)自我修養(yǎng)和精神陶冶,在這方面,西方的隱修士文化也是一種可以借鑒的精神資源。
1976年,由胡安·埃斯特爾里奇執(zhí)導(dǎo)的電影《隱士》,曾在西方走紅,主角戈麥斯因此片獲柏林電影節(jié)金熊獎。影片描寫一位隱士作為智者的精神之旅,他隱居,在山巔靜坐、冥想、沉思,是為了在孤獨(dú)中內(nèi)省。影片的思想主題是,智能和性靈的成長只能一個(gè)人獨(dú)自完成。
這是否預(yù)示新隱士文化正在興起?
工業(yè)時(shí)代已成過去。現(xiàn)代主義的喧囂使人工具化,人的失落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世紀(jì)以來文明最大的焦慮。最早意識到工業(yè)文明對人性造成戕害的正是馬克思,他的異化理論是現(xiàn)代性批判的思想源頭。在《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中,馬克思深刻指出,在工業(yè)時(shí)代,“工人在勞動中耗費(fèi)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chuàng)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qiáng)大,他本身、他的內(nèi)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人創(chuàng)造物的活動成了痛苦的直接原因:“他在自己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fā)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受摧殘。”上世紀(jì)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工業(yè)主義批判蔚然成風(fēng),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勃興,對現(xiàn)代化弊端的反思已經(jīng)基本形成共識。在這樣的語境下,首先是從對環(huán)境的關(guān)懷出發(fā),重構(gòu)人與自然的和諧關(guān)系,建設(shè)環(huán)境友好型社會,已經(jīng)成為后現(xiàn)代文明的新理想。20世紀(jì)初,韋伯曾用附魅、祛魅、返魅來描述文明的發(fā)展趨勢。今天,厭倦了城市異化生活的當(dāng)代人,心靈深處的渴望普遍聚焦于一點(diǎn),那就是返魅即回歸自然,隱士文化重新被關(guān)注,其深層動機(jī)即在于此。其實(shí),早在現(xiàn)代化初期階段,和馬克思同時(shí)代的美國作家梭羅,已經(jīng)以隱居行為踐行向自然的回歸,宣告了對工業(yè)主義的反叛。他從1845年到1847年在康考德附近的瓦爾登湖畔度過了26個(gè)月的隱居生活,并于1854年把自己對這段生活的反思寫成了一部著作,題名《瓦爾登湖,或林中生活》。梭羅說:“我到樹林中去,為的是有目的地生活,只面對生活中的要素。”他蓋了一間簡陋的木屋,自種自食,體驗(yàn)合乎超驗(yàn)主義理想的生活方式,遠(yuǎn)離現(xiàn)代都市的喧囂,回到大自然的懷抱,成為自然的“一個(gè)組成部分”,一心聆聽自然的啟示。他譴責(zé)對財(cái)富的無饜追求,“富到流油的份兒上便不只是保持舒服的溫暖,反成了違反自然的燥熱”;他追慕古代賢者的人生態(tài)度:“古代的哲學(xué)家,不論是在中國、印度、波斯還是希臘,都是一種類型的人,外部生活比誰都貧窮,內(nèi)心生活卻比誰都富有。”梭羅是深刻的,他洞悉了現(xiàn)代社會最致命的弊端,那就是無節(jié)制的放縱生理欲望,任憑物欲支配而向動物性墮落。2005年格拉夫、瓦恩和內(nèi)勒的《流行性物欲狂》出版,標(biāo)題原文是Affluenza,作者們對這個(gè)詞的解釋是:“一種傳染性極強(qiáng)的社會病,由于人們不斷渴望占有更多物質(zhì),從而心理負(fù)擔(dān)過大、個(gè)人債務(wù)沉重,并引發(fā)強(qiáng)烈的焦慮感。”
回到開頭關(guān)于“空谷幽蘭”的敘事,問題就很清楚了,終南隱士的再現(xiàn)不過是中國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中的歷史回聲;但這種廻響多半是一種本能的回應(yīng),其精神境界無論在哲學(xué)上還是在詩學(xué)上,都遠(yuǎn)遠(yuǎn)沒有達(dá)到古代隱士的高度,更不要說對工業(yè)社會做出歷史反思了。不妨想一想,今天重拾隱士的話語,其時(shí)代意義在哪里?二戰(zhàn)后,海德格爾住在菲爾德山麓的森林小屋,過著半隱居的生活,在屋外的木凳上長坐,看山的綿延和云朵在藍(lán)天上漂浮,“他與世界的唯一聯(lián)系是一大疊書寫紙”。在孤獨(dú)中,編成了他的文集《林中路》。在現(xiàn)代化的危機(jī)面前,他反思文明的焦慮,認(rèn)為工業(yè)社會的矛盾源于人對自然的冒險(xiǎn)性干預(yù),人把自己“擺到世界前面去”:在自然不足以滿足人的表象時(shí),就訂造(bestellen)自然;在缺乏新的自然事物時(shí),就制造(machen)自然;在自然擾亂他時(shí),就改造(umstellen)自然;在自然偏離了自己意愿時(shí),就調(diào)整(verstellen)自然。所以,現(xiàn)代人的本質(zhì)就是把世界設(shè)定為可制造的對象之整體,“歸根結(jié)底,這是要把生命的本質(zhì)交付給技術(shù)制造去處理”。他詢問:“詩人何為?在世界黑夜的命運(yùn)中,詩人何所歸依?”人詩意的棲居,詩人不同于世人就在于他仍舊葆有詩情:“詩人在走向神圣之蹤跡的途中,因?yàn)樗麄兡荏w會不妙之為不妙。他們在大地上歌唱著神圣。他們歌唱贊美著存在之球的完好無損。”林中有路,但多半突然斷絕在杳無人跡處,詩人識得這些路,“他們懂得什么叫做林中路”。正是詩人在黑暗中召喚黎明,把理想的人生昭示給世人,重新燃起他們心中的希望之光。詩人才是空谷幽蘭,也只有詩人才配得上這個(gè)浪漫的美稱,他們沒有被物欲橫流的紅塵污染,而是表現(xiàn)著人性的純美。張衡的《猗蘭操》詩描述了詩人對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
猗猗秋蘭,植彼中阿。
有被其芳,有黃其葩。
雖曰幽深,厥美彌嘉。
之子云遠(yuǎn),我勞如何?
不是棄絕人寰、厭世惡生,也不是斷欲絕情、心如槁木,而是心中充滿了美好的希望,不顧幽深渺遠(yuǎn),去不辭辛勞的探尋。我們不能回到古代隱士——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的原點(diǎn)。我們要尋找的幽蘭在哪里?有一個(gè)故事說,有人全世界尋找蘭花,最后發(fā)現(xiàn)蘭花就開在自己的后園。其實(shí),幽蘭不在空谷,而在我們的心中。回歸人性,疏離物欲,是新人文主義的啟蒙。2007年,我來到瓦爾登湖邊,驚異地發(fā)現(xiàn),進(jìn)到湖水中肢體的影像就放大了,據(jù)說這是瓦爾登湖最奇妙的地方。望著瓦爾登湖湛清的湖水,我突然領(lǐng)悟到,人只有融入自然,與自然合一才會顯出自己的偉大。天人合一的理想激發(fā)著我們的詩情,我們有責(zé)任喚醒夢中的世人。
梭羅在《瓦爾登瑚》的結(jié)尾說:“只有我們醒來的那天,黎明才是黎明。黎明到來的日子會越來越多。太陽只是早晨的一顆星。”
讓我們醒來,在黎明的曙色中,去尋找美麗的幽蘭。
(作者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