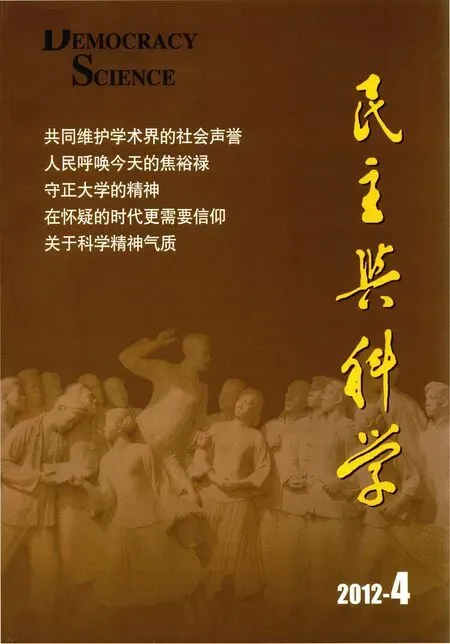說說科學伴生物
■李醒民
說說科學伴生物
■李醒民
科學伴生物是伴隨科學本身或科學概念而生的、與科學本身或科學概念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生成物。只有對科學伴生物有所了解,我們才能比較方便地把科學與之區別開來——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有意義的。我們平時所說的基礎科學(純粹科學或學術科學)、應用科學、工業化科學、技術化科學、大科學等,它們都是科學知識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由于科學的研究活動和社會建制的不同而形成的有自身特點的科學研究領域,它們能夠納入當下的科學范式,屬于相對定型的正統科學、或正式科學、或主流科學。
但是,除了正統科學或正式科學之外,還有伴隨科學一起存在的科學伴生物。科學伴生物形形色色,它包括三大類:科學派生物、科學滋生物、科學衍生物。科學派生物是由科學本身分化出來的,其中有原始科學、前沿科學、邊緣的和有爭議的科學、譏諷科學、病態科學等。它們暫時可以被粗略地劃歸科學的范疇,不過大都處于科學的外圍。它們的前途判若鴻溝:或者因其正確而被科學共同體逐漸接受,經過批判、修正和完善,最終演變為正統科學;或者因其錯誤而被拋棄和遺忘。科學滋生物是由科學概念引出的,諸如非科學、女性主義科學、反科學、偽科學等。它們不是科學,盡管其名稱帶有“科學”,這只是表明它們是相對于“科學”一詞而言的,而與科學內容本身沒有什么直接關系。處于科學派生物與科學滋生物之間的,是由科學概念和科學本身演變、產生的所謂科學衍生物,例如隱秘科學、另類科學、民間科學、超科學、似科學等。科學衍生物前途無非是:或進入科學派生物之列,或落入科學滋生物之行。
不用說,這樣的分類僅具有相對的意義:不僅科學派生物、科學滋生物、科學衍生物三大類多少有所交叉,而且同一科學伴生物項目也有可能分屬于不同的類別。加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此種交叉和重疊就更難免了。這一點從下面的分析和列舉中不難看出。
我們首先說說科學派生物——原始科學,前沿科學,邊緣的和有爭議的科學,譏諷科學,病態科學。原始科學(proto-science)又稱原始知識,也有人把它叫做前科學(pre-science),意指近代科學之前的科學的形態(古代和中世紀的科學),也意指轉變為正統科學之前的不成熟的雛形。亦有人稱原始科學為潛科學,即潛在的科學。原始科學被視為歷史上的或現實中的科學的原始形態,它最終會被改造和轉化成為正統科學——這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種事后認識。
顧名思義,前沿科學(frontlinescience)是科學家在科學探索前沿所獲取的有啟發意義的思想或假設,或具有重大潛在價值的知識或理論。它們雖然是不成熟的,不是系統而完備的理論,但卻是未來科學發展的突破口或新穎理論的萌芽。
邊緣的和有爭議的科學在研究對象、題材、問題、內容、范圍等方面,或多或少與科學有關,但是它們卻是處于科學邊緣的,常常是有爭議的,有時甚至被認為是科學滋生物,是非科學乃至偽科學。
譏諷科學(ironicscience)是具有諷刺意味的科學或令人啼笑皆非的科學,這是霍根在他的《科學的終結》一書中杜撰的名詞。霍根說,這種科學與文學批評的相似之處在于:“它所提供的思想、觀點,至多是有意義的,能夠引發進一步的爭論,但它并不趨向真理,不能提供可檢驗的新奇見解,從而也就不會促使科學家對描述實在的基本概念做出實質性的修改。”
病態科學(pathologicalscience)一詞是化學家蘭米爾在一次講演中自造的。在考察戴維斯-巴恩斯實驗、N射線和細胞分裂射線實驗的基礎上,蘭米爾發現這些科學研究具有某種共性。他提出判斷病態科學的幾條規則:觀察到的最大效果是由實驗強度極弱的稀有偶然因素產生的,結果的大小實質上與原因的強度無關;這些觀察都接近于裸眼視力或其他感官的極限,僅具有十分低的統計意義;宣稱有高度的精確性;提出與經驗相悖的異想天開的理論;批評常被一時沖動下的特殊借口反駁,被批評者總是有理由不假思索地回答;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比率有時會升到50%,然后逐漸被忘卻;批評者不能重復實驗,只有支持者能重復,最終沒有任何東西保留下來。在病態科學中,作為當事人的科學家自以為老老實實地從事科學研究,但是實際上卻由于求新和求勝心切而步入歧途。
其次,我們說說科學滋生物——非科學、女性主義科學、反科學、偽科學。非科學(non-science)完全是針對科學概念而命名的——沒有科學,也就無所謂非科學。嚴格地講,把非科學與其他科學滋生物并列在一起是不大合適的,因為非科學只是相對于科學而言的,科學之外的所有知識分支或文化活動領域都可以說是非科學。說一個學科或領域是非科學,并不意味著它們全部無意義。在某些方面,它們對社會、對人類的意義也許勝過科學。
女性主義科學(feministicscience)純粹是女性主義者的生造詞匯。女性主義者十分討厭正統科學,并視其為壞科學;他們力圖構造反映女性特點和理想的所謂好科學,以便取代存在嚴重的性別主義和男性中心主義偏見的科學。
反科學(anti-science)是反對科學的哲學思潮和社會運動。反科學即是反對科學,或對科學采取敵對態度,或與科學對立、對抗。反科學或是反對作為一個整體的科學,或是反對科學的某些要素和部分——而這恰恰是科學的最普遍、最核心的要素和最根本、最基礎的部分。
至于偽科學,一種想法或見解、信仰或活動之類的集合,本來屬于非科學,但是它們的始作俑者和追隨者卻素樸地相信其是科學,或者假借科學的名義,刻意地將其偽裝成科學,虛偽地鼓吹其是科學,以致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或惡劣后果。這樣的集合就是偽科學。
最后,我們說說科學衍生物——隱秘科學、另類科學、民間科學、超科學、似科學。隱秘科學(occult science)有時也被稱為神秘主義或東方神秘主義,其突出的特征是:隱秘科學關注的對象是自然界的一些神秘事物或超自然的隱秘事件,而且常常是私人經驗或體驗的東西。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事物、事件、經驗是虛幻的而非實在的;對它們的說明和詮釋往往是超自然的、玄之又玄的,使人不得要領。隱秘科學在迷信、信仰、幻覺、玄想、內省以及科學的邊緣游走,很難發展成為科學的一部分。
另類科學(alternativescience)之所以也被稱為大眾科學(popularscience),是因為這種科學多是大眾參與的,是熱中于通俗文化或流行時尚的人青睞的。齊曼注意到,另類科學與隱秘科學有不解之緣。多爾比揭示,另類科學與先驗的信仰和價值聯系密切,其追求者關注的是正統科學一時無法解決或根本不可能解決的問題。
民間科學(folkscience)是在民間從事研究的科學。民間科學絕大多數是由處于正式科學機構之外的科學愛好者和科學迷進行的自以為是的科學研究,當然也不排除科學家利用業余時間從事自以為有前途的民間科學研究。民間科學基本上是業余進行的,其從事者及迷戀者大都沒有雄厚而扎實的科學知識基礎和系統的研究訓練,更沒有強大而精密的實驗設備,因此要做出科學發現,是比較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即使有所發現,基本上也集中在某些天文觀察領域(比如觀察到某個小行星)或博物學領域(比如發現某個動植物物種和變種)等少數地盤。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民間科學“大顯身手”的領域往往是主流科學認為最難以攻克的領域(比如地震預報),或長期得不到解決的難題(比如哥德巴赫猜想),或根本沒有成功希望的設想(比如各類永動機)。民間科學者似乎有一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勁頭,越是困難的領域,他們越是“知難”而進;越是正統科學力不從心的問題,他們越是想“露一手”;越是主流科學認為異想天開的事情,民間科學越是要創造“奇跡”。更恰當地講,民間科學者根本不知道,它們著手的問題有多么艱難,或壓根兒就不可能成功;他們還是無所畏懼、埋頭蠻干——這真應了“無知者無畏”那句老話。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民間科學的“成果”往往不是在正規的科學期刊發表,以供科學共同體討論、審查、批判;而常常是通過大眾傳媒發表,靠上訪、網絡、非正式的宣講、散發自制印刷品傳播的,以收到聳人聽聞的新聞效果,或盡量擴大自己的受眾。不能說民間科學一無是處,也不能說民間科學一事無成,但是其積極意義不是很大的,其成功的幾率也是很小的。作為個人的一種精神追求,別人無可厚非。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尤其是具有一定聲勢的文化現象,則不宜鼓勵和提倡。因為它畢竟要無謂地消耗部分社會資源,也使民間科學者本人心力憔悴,過不了正常人的日子,乃至患上嚴重的精神偏執癥。至于有些民間科學者由于得不到科學共同體的承認,而對正統科學和主流科學家采取干擾、攻擊、漫罵等極端舉動,則是社會的不和諧音符和不安定因素,值得引起警覺和防范。
超科學(trans-science)似乎有兩個涵義。其一是所謂超自然現象的研究。這不免超出自然科學研究的范圍,其“理論”也無法納入現有的科學范式,與人們已有的知識難以相容。這種超科學肯定屬于非科學,與隱秘科學有些接近。其二是溫伯格定義的,他把“能夠詢問科學而科學卻不能做出回答”的問題稱為超科學的。不難看出,溫伯格所謂的超科學似乎與另類科學和民間科學有點相通。
似科學(para-science)也可以譯為“類科學”。由其英語詞前綴顧名思義,似科學即是乍看起來好像類似科學的意思。有人把它譯成“準科學”或“副科學”,我覺得不很準確。伊利英和卡林金斷言:“似科學是其認識論地位還未滿足科學的條件,例如似心理學。”齊曼揭示出似科學的屬性和特征:正如民間心理學認為科學家充滿“好奇心”那樣,民間認識論同樣主張科學知識充滿“神秘”和“驚奇”。似科學的獨特特征是社會和心理上的,而不是認識上的。這些信仰有時在認知上是宗教性的,但是經常是高度個人性的和異質性的,其斷言通常是如此不確定、不完整及不整齊。似科學與隱秘科學、另類科學、民間科學、超科學乃至偽科學有某些共同點。
(作者單位:中科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