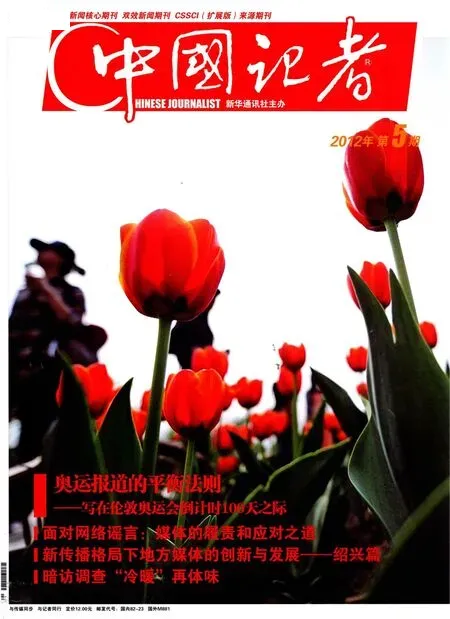一位三農研究專家眼中的“三農報道”——專訪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
□ 文/李 成
編 輯 陳 芳 chenfang@xinhua.org
與三農問題在國計民生中的基礎性和保障性地位不同,三農報道在媒體報道和社會議題中卻相對邊緣。其中有權力和資本的因素,也有媒體自身理念和方法的因素。加大三農傳播,助力三農發展,是一項系統的長期任務,需要媒體人不斷探索。本文是一篇對三農專家的專訪,旨在為媒體人增加一種思考相關報道的“改進余地”和“發揮空間”的視角。

黨國英
黨國英,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從事農業經濟學研究,主要專長是農村制度變遷問題研究,并有多篇(本)這方面的論文和著述。
新媒體背景下傳統媒體的管道作用愈發凸顯
中國記者:您如何看待媒體在解決三農問題中應扮演的角色?
黨國英:新聞媒體在三農問題的解決中一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媒體就功不可沒。在我看來,媒體不可替代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從下情上達的角度看,媒體可以將農民愿望、自發改革的行動等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央反映。在這一點上記者與現實的接觸方式、對信息的反映方式與政府不一樣,相對超脫,也相對更客觀,媒體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管道。
第二,在新媒體環境下,盡管有很多自發傳播的信息管道,但關于三農方面的反饋,負面內容比正面內容多。因為人們總是傾向于在網上發牢騷而不是“曬幸福”。這就導致自發的網絡信息是片面的,單就此評判容易給人形成農村政策效果不好的錯覺。
比如農村的農民總體是對三農政策滿意的,不滿意的有,但主要集中在城市擴張區,主要原因是土地問題。而真正的農區,涉及的利益不大,這反而給了農區空間,農民滿意度較高。但是在城市擴張區就不同了,這部分人口本來就脫離了農業,雖然反映的問題多,但和“三農”本身關系不大,多是征地補償方面的問題。
政府系統的信息管道和自發性的信息管道容易失之片面、各執一端,這種背景下,專業媒體在傳播相關信息上的戰略重要性其實更加凸顯了,更需要記者全面把握,用專業的眼光到農村搜集信息、發現新聞。
記者觀察如何避免偏差
中國記者:能否舉例說明媒體在三農報道中常見的問題以及規避措施?
黨國英:媒體報道的確是雙刃劍。報道對了,有助解決很多問題;報道錯了,也會傳播很多錯誤的做法和說法。媒體的功能主要靠記者體現,但記者觀察也會有偏差。
一、從報道方式上看,下面兩種情況容易導致報道偏差:
1.報道三農問題的時候,地方上有關部門的接待多多少少會影響記者采訪;而暗訪也很難,地方上有自己應對記者的辦法。這制約了記者對問題的深入挖掘。
2.三農報道由頭往往是農民反映的情況,多為負面,如果不多了解就容易被一時的情緒左右,形成不恰當的負面判斷。但實際上,“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十多種補貼、社會保障的完善等,農民是高興的,總體是很滿意的。
二、面對一些流行的錯誤認識和做法,如果記者自身缺乏深入調研和專業眼光,就容易盲從。這就是比較危險的報道傾向錯誤的問題了。
比如,華西村發展起來使很多人認為不搞承包經營就能富裕,而小崗村搞承包經營依然窮,這樣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形成一個“富的不搞,搞的不富”的誤解。宣傳部門如果戴紅帽子,媒體配合鼓吹,誤導性就更大了。實際上,搞承包制的農區趕不上不搞承包制的華西村,但是如果農區不搞承包制,就更不行了。承包制對農區生產力和農民福利而言有很大的提升作用。同時,華西村已經不是農業經濟,而是工業經濟,是靠高效率的工業彌補低效率的農業。所以應該探討的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如何轉移農村勞動力、建設現代農業的問題,而不是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予以否定或“創新”的問題。
再如,珠江三角洲地區搞農村股份合作制,就是土地不分到戶,而是集中起來搞魚塘、工廠等來分紅。其他地區的同志就容易誤解為:農村搞股份合作社可以富裕起來。媒體也容易跟風。而實際情況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因為沒有農業,鄉村企業搞得早,最初土地管理法規立得晚,所以工業用地不規范。后來為了彌補,就以土地面積占比來分紅。其實是一種土地物業聯合(合作)經濟,集中起來招商引資,是非農產業。而在農業經濟領域,流通和服務環節可以搞合作社,生產環節仍然必須承包制,只不過是承包制如何進一步鞏固優化的問題。媒體如果不深入剖析,就容易受誤導,尤其是受到利益相關者的誤導,比如鄉村干部是喜歡集中土地的,因為這樣他的權力就大了。
另如,有種說法認為農村現在是“386199部隊”(注:38代表婦女、61代表兒童、99代表老人)種地。但是,如果這是事實,九年多的糧食增長是怎么來的?實際情況是現在農村生產環節逐漸服務化、專業化,有提供播種收割等勞務的專門勞力。比如,“托地社”就是不放棄承包經營權的前提下將耕地“入托”,讓別人代為管理,其實是一種農業服務。
還有媒體反映的土地撂荒問題,認為是農業危機了。我認為這是天經地義啊。你看看,河北河南這樣的小麥主產區會撂荒嗎?絕不會。凡是撂荒的土地,農民撂荒一定有其道理,少數情況下是土地主人是懶漢,多數情況下是農民基于比較收益的考慮認為種地成本高,不如打工買糧食吃。再者,土地撂荒是不是就影響到中國農業了?不一定,因為糧食主產區農業現代化程度高,產量非常高。糧食兩季的主產區,一畝一年一噸糧是很普遍的。18億畝耕地,假設其中6億畝地達到一畝一年一噸的話,我們一年就有6億噸糧食,根本吃不完。所以我們多年來糧食產量都超過了口糧,目前主要是工業用糧耗費了很多糧食。所以我認為撂荒不代表農業有危機,當然我不是說農業沒有危機,但不是表現在撂荒上,比如糧食主產區產量高,但產糧成本高。這里,媒體就需要去偽存真:要找到“真問題”“真危機”,而不是炒作“偽問題”“偽危機”。
從事三農報道的記者隊伍一定要提升理論素養和專業水準,對三農歷史和政策要有深入研究,破除很多先入為主、想當然的誤判。對信息善于去偽存真,不能跟風,要體現媒體的專業性;對很多現象要深入調研,透過表面看本質,多和農村基層、農民接觸,多聽聽不同的聲音。

舉這些例子是想說明,從事三農報道的記者隊伍一定要提升理論素養和專業水準,對三農歷史和政策要有深入研究,破除很多先入為主、想當然的誤判。對信息善于去偽存真,不能跟風,要體現媒體的專業性;對很多現象要深入調研,透過表面看本質,多和農村基層、農民接觸,多聽聽不同的聲音;對“三農”專家要善于交流、學習,甚至要讓自己成為專家。
放眼整個涉農產業鏈找經濟回報
中國記者:近年來,由于受到廣告回報等方面的制約,媒體三農報道的量比較少。那么針對這種具體問題,您認為應如何解決?
黨國英:目前媒體的三農報道投入力量仍顯單薄。我認為關鍵是觀念和方法的問題。
首先是一個媒體社會責任和擔當的問題。
三農問題多年成為中央1號文件的主題,其意義不言而喻。因此媒體需要從三農問題的戰略意義入手,提升報道的力度和水平,促進三農問題的討論和解決。同時,農民很多時候不在乎吃虧,而在乎是否合乎規矩,是否合法。記者在采訪時也應該善于從這個角度入手反映農民的真實心聲。
其次,媒體應該把三農主題報道的視野放大,拓展報道的空間和角度。
比如產業報道,涉農產業鏈其實很長,經濟價值也很大,做好了不愁沒有廣告收入。中國的恩格爾系數是0.35,以25萬億消費支出總額算,僅吃的方面經濟規模就達八九萬億。可見這個領域還是很廣闊的,就看如何轉換眼光,從飯桌涉及的縱橫關系中做文章。而隨著三農政策的落實和改善,農民收入逐漸增加,農民也有買車等方面的“高級需要”,這里就蘊含著巨大低端家用車市場潛力。所以,無論就吃的方面,還是就消費市場方面,三農報道都是可以做到“有利可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