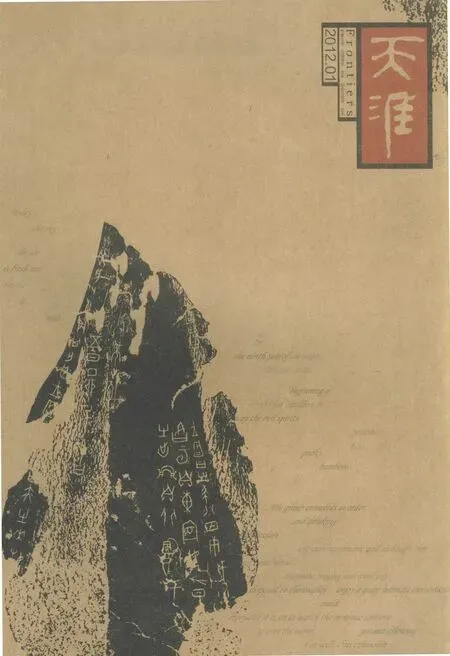“中國道路”的核心是生活方式問題
陳赟
“中國模式”論述中“中國”觀念的不充分性
“中國模式”的討論,表面上是改革開放三十年與共和國甲子反思的一部分或者是其繼續,實際上卻折射了當前關于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性憂慮。這個討論的焦點與其說是重在解釋三十年來高速經濟發展體現的“中國奇跡”,毋寧說是如何引導中國的未來。就歷史解釋而言,導致三十年經濟成就的諸多因素,在目前的狀況下,還不具備得到充分歷史化的條件,這不僅是由于相當多的因素還不能進入人們的視野,一個可靠的將三十年發展歷史化的地基(“效果歷史”意義上的回溯點)還沒有出現,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還在過程之中,其明天并不確定。在這個意義上,當前的討論其實是借著歷史解釋來達成新的未來籌劃。未來中國會以怎么樣的面貌出現?高速經濟發展會延續多久?政治與文教會有怎么樣的調整或變革?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沒有答案,卻都關涉到每一個人。這一現象本身就表明了方向感或目的感的缺位,本身就構成“中國模式”討論的深層心態背景。退一步說,就實證層面而論,對已有發展進程的經驗性總結,即便不是為了為未來提供標本,但這一經驗性解釋本身,也是影響即將展開的進程的一種力量,特別是在利益集團已經形成、階層分化明顯的情境下,以經驗科學名義出現的實證性解釋很難擺脫權力與利益的邏輯。
既然中國模式的討論說到底不得不承擔未來的中國規劃,那就應該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而不是緊緊盯著過去的三十年或眼下的這幾年。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一些學者的主張,中國模式的討論應該讓位于中國道路的討論,因為模式這個詞語本身就包含了太多的經驗性因素,其歷史基礎非常之短,似乎只有九十年、六十年甚至三十年,著眼于這樣一個短時段,毫無疑問,會缺乏遠大的歷史眼光,更重要的是它缺乏一種直面未來的指向。中國道路的問題,上可以溯至千年之前,下可及于百年之后。中國模式的討論作為中國未來的世界籌劃并不能完成使命,因為未來的五十年甚至更遠的時間內,中國籌劃的核心是文明與價值層面上的方向或目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一種管理與發展的模式或體制。迄今為止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還不足以達到呈現上述的方向或目標,唯一的途徑是在關注時代問題的前提下,顯明并提升沉淀在集體無意識與語言典籍中的文化與思想傳統,向著更長時段的歷史與更遠的未來開放我們的眼光。與三十年的經濟發展相比,這乃是一個更崇高、更嚴峻,也更困難的使命;甚至可以斷言,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不過是為這一使命提供了前提。反過來說,解決當前與今后的道路或方向問題,一定要超出三十年經濟成就,如果僅僅滿足于經濟成就,那么對道路或模式的討論就會缺乏自生型的文明母體的支撐,因而滿足于特殊性的民族國家的架構而遠離中華文明的世界性與普遍性的地基。
一旦上升到這個層次來看問題,就會發現當前的各種討論,面臨著這樣一個基本挑戰:這就是“中國”觀念的不充分性。無論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討論,還是“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的討論,“中國”都僅僅停留在自然狀態下的“所與”或現成性概念,僅僅由現成的地理的、民族的,或國家的維度規定,其內涵還不是內在于中國道路之中的目的與方向本身,換言之,“中國”還缺乏文教內涵,還是一個沒有“文—化”(“文”與“化”在這里用作動詞)能力的外鑠性概念。那種僅僅從解決“挨打”、“挨餓”之后的“挨罵”的百年歷史處境來回答中國道路的內涵的思路,至少是外在的、防御性的,遠遠沒有上升到其內在的自為性的動力機制問題,沒有上升到文明得以立身的地基,沒有上升到千年中國文明的現代更新問題。因此,我們說,中國道路中的“中國”觀念如何充實的問題,是上述方向性憂慮的核心。
中國道路的核心是生活方式問題
中國含義如何充實的問題,或者說,中國道路的方向性問題,只有在文明論層次才能得以深化。文明的最核心層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問題,而后才是圍繞著生活方式展開的政治制度、教育體制與經濟發展模式等等。生活方式關涉到每一個人的存在意義,以及如何展現人之為人的本質,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它是文明的基本方向問題。生活方式往往滲透在它的人們的視聽言動中、彌漫在人體的氣血筋脈里、貫通著意識與無意識,它提供對人性及其所居世界的根本性理解,這種理解規定著我們感受并消化身與心、性與夢、衣食住行、自我與他人、健康與疾病、時間與空間、義務與責任、工作與勞動、婚姻與家庭等等,這些生活世界基本事物的方式,而感受并消化上述事物的方式,也反過來構筑生活方式本身。一個堅實、深刻、豐裕、厚重的文明,會將自己的精神貫徹到可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與細節里,“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小大精粗,無所不運。比如坐立時端正身體的方式、日常閑居時口腔中的舌位,甚至性生活以什么方式才從生命的耗散轉化為保養,等等,中國文明都考慮得格外周詳,正是在這些不起眼的細節中,一個偉大的文明完成對人性與生活方式的從自然到文明的轉化與提升。中國文明所提供的生活方式,一言以蔽之,建立在天、地、人的相互貫通的基礎上。它對天、地、人三者的分工、邊界及其協調與平衡,都有深刻的理解,正是通過這個理解,在“天地之間”堂堂正正做人,構成了它的指向。這個指向既不會遭遇神教的世俗化轉型所帶來的困境,亦不會遭遇啟蒙運動的人道主義危機,在這個意義上,盡管我們的世界體系大體都經歷了傳統與現代的轉型,但對中國文明而言,并不是文明自身的精神性危機,并不是生活方式內在的危機,而是隨著社會結構與經濟方式的轉變,在現代世界中重新找到象征性的載體與通道。
更本質地看,經濟發展模式、政治制度與教育體制等除了解決各自承擔的區域內的問題之外,它們實際上都有自己的教化功能,都承擔著影響并塑造人性、維護某種生活方式的不易被人察覺的重任。換言之,雖然,在現代世界體系中,政治、教育、經濟、文化、體育、藝術、科學、倫理、道德等等,都被區域化的邏輯所支配。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獨立運作規則,然而在影響、風化甚至塑造人性與生活方式上,它們卻以隱黯的方式支持“場所化”的邏輯,它們都是教化體系的一個方面。在這個意義上,除了正視每一個系統的自身規則之外,便是要整體地考慮其承擔的教化功能。一談到教化的問題,便不能回避歷史形成的孔教。制度與秩序不能僅僅靠律法來維持,而是要文教來擔保。撇開孔教問題,很難想到任何一種文教體系在中國的脈絡里能夠承擔這個責任。中國的制度建設,如果脫離孔教基礎,就會失去精神或靈魂。也只有立足于孔教的根基,我們才能理解滲透在我們的衣食住行、貫通于我們的意識與無意識中的那種生活方式,才能進一步純化與提升這種生活方式,在此基礎上構造新的社會組織方式。
對于幾大軸心文明而言,對生活方式的理解往往以肉身化的形式具體地展現出來,例如基督教文明中基督化的耶穌、佛教文明中的釋迦牟尼、希臘文明中的蘇格拉底等等。中華文明所理解的生活方式,則以孔子作為其肉身化的表達,“十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概括了這一肉身化了的文化生命的歷程。雖然這一生命出生、成長在特定、具體的經驗時空中,但隨著兩千年的文明實踐的展開,這個肉身所承載的生命的“文—化”內涵不斷被充實,因而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具體、越來越鮮明,在兩千年的歷史世界中承擔了重要的“文—化”(文而化之,即文飾具體的生命并化育滋潤之)功能,其普遍性格得到了展現。中國文明的兩大主干,不管是儒家還是道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消化孔子的文化生命,即便是外來的佛教,也在消化它的過程中更新了自己。在這個意義上,孔子這個肉身所象征的文化生命,并不專屬于儒家,而是隸屬于中國文明的全體。甚至可以說,孔子的文化生命,就是中國生活方式的典型體現,它充分展現了這一生活方式所可能達到的高度與深度。
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給中國的發展提出的問題恰恰就在于,我們的“社會主義”能否最終接納并更新孔子的文化生命,使得其所展現的生活方式在當代世界延續下來并恢復活力。這個構想的另一個表述其實是,在社會組織結構、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甚至教育制度等發生了結構性變化的情況下,幾千年中國文明所建立的生活方式能否持存下來?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對中國的執政黨、對中國的士階層來說,乃是一個巨大考驗。這比經濟建設、政治改革還要艱巨。上述構想并不是要犧牲當前與今后中國的人民,讓他們來做一個具有代價的實驗,而是要在充分尊重個人生命的基礎上,立足于他們生命的當下時空,通過千年中華文明,浸潤、轉化、提升他們的生命,引導其朝向更健康、更自由、更文明、更富于教養的上升之路。
充實而有光輝的文化生命,來自寬大篤實、豁達光明的生生之氣,并不是也不能化約為任何一種抽象教義或主義話語。孔子的肉身所象征的文化生命,開放在詩、書、禮、樂、易、春秋所構成的“六藝之教”中。在普遍的層次上,詩、書、禮、樂,首先并不是作為經書或四種法典,而是作為“三科六藝”意義上的“四藝”,共屬于同一個教化空間,從而完成人性的教育與生活方式的養成。如今的基督教、猶太教、天主教等各大宗教的“教堂”顯然便是這種意義上的“詩、書、禮、樂”四者共聚的“四藝”空間。傳統中國的學校雖然是上述四藝空間的主要場所,但“四藝”本身還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進入生活世界。從生活方式的養成角度而言,四藝或六藝(詩、書、禮、樂“四藝”是一個層次,其構造的是體現了中國文明所理解的人性的人——君子,易、春秋“二藝”則是從君子向上達一路的進一步提升)作為一種教育的場域,如何構建,則是中華文明的自我更新與生活方式的持守,最為關鍵的問題。當前的讀經運動,雖然觸及到四藝或六藝中的某些層面,但其實只是集中在“四藝”中向著眼與心開放的那些東西,禮教、樂教、詩教、書教在更本質上的層面上并不能還原為讀經的問題,它是要通過人們的閱讀、傾聽、歌唱、吟誦、樂舞、執禮等活動,向著眼、耳、鼻、口、身、意諸官覺構成的整體生命的開放,是以這種方式構筑的文—化或教—化的空間。
中國道路對世界文明的可能貢獻
在理解中國道路的過程中,人們不可避免地在以西方文明作為它的參照,這無可厚非,但需要脈絡化、整體性地理解西方文明。比如,民主與憲政上,在實踐與理論上都被做了普適性的理解之后,就成了自由主義者對中國道路在政治方面上的最后方案。的確,當前中國政治蘊含著的危機,如政治權力的防御與限制問題,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但政治方案的思考,需要更為久遠的眼光。一些自由主義者試圖拿來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的時候,卻沒有反思,最終以之來捍衛什么,正因為不能考慮到這一層次,所以最后只能以普遍人性的問題,抽象地回答這一問題,最后的結果則是自由(甚至是消極自由)、民主與市場,反而成了目的本身,并將之從政治生活擴展到學校、家庭中去,從而不斷僭越自己的邊界,由此而滋生很多問題。一方面,剝離生活方式及其歷史形成的問題,最終導致了自由民主的技術化,即懸浮著的沒有歸宿與根基的自由主義;另一方面,自由民主市場等的主義化或價值化,卻又強化了與傳統形成的生活方式之間的沖突。即便以自由主義作為中國道路在政治上的回答,也既要著眼于當前時代的實質問題,又要更長遠的目光,一個政治的制度如果僅僅為當下的問題而設,那么它在未來就不可避免地面臨危機,共和國的歷史已經表明了這一點。理想的方式是轉化提升自由主義的民主與憲政,讓它的這些制度一定程度上脫離基督文明與資本主義所支持的那種生活方式,與當前的“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相結合,以中國文明的精神充實之,即讓其成為中國文明意義上的生活方式的保護者,至少在消極的意義上,不讓其抵觸、干預這種生活方式。換言之,憲政與民主的建設問題,不是一個移植的問題,而是一個“在地”轉化的問題,應該在中國文明復興的整體結構中加以考慮。
事實上,自由民主的觀念,在其原產地乃是根植于神學政治的論述的脈絡之中的,經過了啟蒙運動,自由主義雖然經歷了去基督教的過程,但它的去宗教化過程本身卻是以新的宗教的建立而完成,即以人道主義的人的價值之宗教替代基督宗教中的上帝的神教,人所設置的價值或者對價值的設定本身成了崇拜的對象。自由主義對人的理解,著眼于人與人之間的維度,人是萬物的尺度,人是世界的主人的觀念,它構造了自由主義生活方式的基礎。這種生活方式雖然有其《圣經》神教的根子,但卻是啟蒙運動中的“棄神”思想使之最終得以完成。人的自由、人的權利等諸多問題,雖然也曾歷史地促進了人類的獨立與解放,但在其被“價值化”(被價值化,意味著以主體方式出現的人基于特定視角觀察所得的觀點對存在進行某種主觀性的設置與構造)以后,除了同樣作為個人的他者,不再有任何人以外的限制,這種“天上地下,唯人(我)獨尊”的人道主義邏輯,構造了諸多現代性的后果。而且,只要是遵循啟蒙思想關于人的價值的宗教,就不可避免地觸及到諸種被神化了的“價值”之間永不停息的爭斗,人的整體的秩序與和諧必然遭遇到來自這一“諸神之爭”的危機。對自由主義的運用本身必然以對之的“在地”轉化與提升相關聯,所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仍然具有指南的意義。
在人道主義“自由教”普世化的今天,已經沒有什么東西可以限制作為人的最高價值的“自由”,特別是這種啟蒙意義上的“人的自由”已經下行到作為第一人稱主體的“我的自由”,這是現代世界中生活方式問題最成問題的根源之一。飯前一杯冰水,打倒人的腸胃對是否饑餓的感知能力,而后便可多多進餐。店主人賺了錢,客人也長成大胖子。這種資本主義的邏輯通過市場這種機制得以進入生活方式的深層。為了生產被消費的產品而首先要生產需要消費這種產品的個人。甚至連政治、宗教與教育的制度本身,都沾染這種邏輯,這不能不說是現代的人性與生活方式的危機。但正是這種生活方式在全球迅速地蔓延,甚至不可遏制。如果從權力關系來看,共同體內部的平等背后的支撐是共同體與其外部的巨大的不平等、內部的自由之后的支撐是外部的巨大不自由,這種在共同體外部爭先恐后進入共同體內部,而共同體內部又拒絕外部的生存樣態,甚至以生活方式的“美夢”的方式被構造出來,這無疑是毀滅地球與人類的一種威脅。對于身陷金融危機中的歐洲人們來說,他們不會將危機追溯為政治體制的問題,也不會將之視為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問題,這多半是因為在自由民主之外,他們實在無法想象還有其他的政治可能性,而在他們的生活方式之外,他們也喪失了新的可能性的想象。基督文明的末世論賦予了西方文明一種歷史終結的意識,這種意識深埋在他們對政治與生活的理解中。就此而言,也只有中國的思想,才提供了一個真正的他者,可以為當今的世界提供“歷史終結”之后新的可能性。從這個狀況出發,中國道路在生活方式的層面擔負的不是復制上述的“美夢”,而是立身于自己豐厚的文明傳統,為生民拯救被終結了的歷史,為生活提供新的可能性。中國道路對世界如果有最大的貢獻,那么它應該首先在這里。
當前中國的思想分化,集中在中國道路的理解上。但按照我的理解,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與宋明人如下概括所體現的問題意識相近:“莫勘三教異同,先辨人禽兩路。”人心與人性及其所引發的問題,在今天到了讓人觸目驚心的程度。不是寬大優裕從容之氣,而是暴戾怨忿、麻木不仁之氣,正在侵蝕著人性。當然,這并不是某個或某些具體個人或群體的道德與精神問題,而是關乎民族生存的世道風教問題,而世道風教雖然與政治難以分割地糾結在一起,但并不是單靠政治能夠解決的。自由主義、新左派與保守主義這“三教”,在“先辨人禽兩路”這個問題上應該有共同的自覺。不管如何思考政治制度、教育體制與經濟發展模式,人性及生活方式的問題應該被首要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