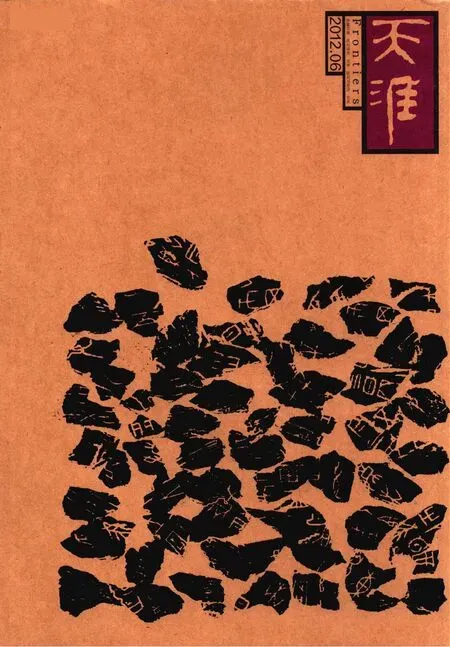勢治秩序:轉型鄉村社會一種新的形態
陳占江
六十多年前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指出,人類社會存在兩種秩序:一種是鄉土社會中的禮治秩序,一種是工業社會中的法治秩序。在費先生看來,任何維系社會秩序的力量或紐帶必須與其社會性質相符合。在鄉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相熟,較少發生流動,在這個熟人社會里維系秩序的主要是禮。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不像法律那樣依靠國家權力強制推行,而是通過傳統和教化來濡化和規訓一代代人并使其成為有效的自我約束力量。鄉土社會中的民間糾紛也不靠法律解決,而是通過“禮”的化身——紳士或長老以說服、教育、勸誡等方式進行調解。禮治之所以能夠在鄉土社會中實現乃是由于禮治滿足了當時社會的需要。“禮治的可能必須以傳統可以有效地應付生活問題為前提。鄉土社會滿足了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禮來維持。在一個變遷很快的社會,傳統的效力是無法保證的。……所應付的問題如果要由團體合作的時候,就得大家接受個同意的辦法,要保證大家在規定的辦法下應付共同問題,就得有個力量來控制各個人了。這其實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謂‘法治’。”(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自晚清以來,中國被迫納入西方主宰的發展邏輯中,工業文明不斷擴張而農業文明日趨式微,禮治逐漸失去了其原有的社會基礎。在這一過程中,工業文明的法治邏輯通過至上而下的方式強行侵入有著悠久農業文明的鄉土社會。那么,法律在轉型社會中所起到的功能如何呢?費先生對此有一段頗富警示意義的話:“現行的司法制度在鄉間發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制定若干法律條文和設立若干法庭,重要的還得看人民怎樣去應用這些設備。更進一步,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單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鄉,結果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先發生了。”(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作為功能主義者,費先生認為在從鄉土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法律所表現出來的更多是負功能,送法下鄉的弊端早已在實踐中暴露出來。承費先生的余緒,電影《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爺》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新時期對于法律在鄉村社會中的遭遇和后果所作出的深刻的反思,我國法學界以蘇力為代表的“本土資源派”亦持如是觀。
鄉土社會被費先生視為無訟社會。在鄉土社會中,無訟與禮治是互為表里、并行不悖的。訟師的地位很低并在現實生活中被不斷地污名化,無訟的理想也被儒家思想一再地強化。然而,無訟或禮治之所以能夠在鄉土社會中實現,其原因不僅僅是儒家思想和熟人社會性質的影響,與傳統中國的政治體制亦有內在的關聯。費先生曾對傳統中國的政治體制進行過深刻的闡釋。在傳統中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并未將整個社會吸納到皇權之中,反而由于地理、技術等原因導致“皇權不下縣”的局面,縣域以下的社會基本上不受皇權的直接干預,紳權成了連接中央與地方的中介和橋梁,紳士在二者之間扮演著既代表皇權又在一定程度上約束皇權的力量。所以費先生將鄉土中國的政治視為皇權與紳權并行的“雙軌政治”。在這種社會中,法律扮演的功能更多的是維護皇權的穩固而非調節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所以在傳統中國,無為政治既是歷代統治者追求的理想也是現實的無奈選擇。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通過一系列政治手段和技術手段徹底結束了幾千年來“皇權不下縣”的“雙軌政治”。國家的權力延伸到每一個社會角落,像毛細血管一樣漫布于整個社會肌體,無時無處不有國家的影子。如果說帝制時代的國家權力受到了一定的約束,那么新中國以來呈現的則是強國家弱社會的局面,甚至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行政幾乎完全將社會吸納其中。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果是國家權力因沒有有效的約束和制衡導致國家權力過度膨脹,而依靠國家力量予以保障實施的法律常常成了“政治的晚禮服”(馮象語)。在司法實踐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衡和有力的監督,法律有些時候淪為了強者實現其意志或利益的工具。
按照費先生的理路,討論在鄉村社會能否推行法治的前提是鄉村的社會結構和農民的價值觀念是否為法治提供了相應的社會基礎。易言之,法治與鄉村社會之間是否存在“位育”的關系。當下的鄉村已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從內向型村莊向外向型村莊過渡,時空秩序和日常生活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社會發生了頻繁的流動,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社會結構已然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結構混亂的景象,新興職業或階層不斷涌現,貧富分化日趨嚴重。以國家為推手的送法下鄉、宣傳下鄉、電視下鄉等運動不斷瓦解著農民的傳統觀念并試圖重新植入一種以現代性為內核的價值取向和社會理念。從農民的生態秩序和心態秩序看,費先生所言的鄉土中國已漸行漸遠,甚至留給我們的只是一個日漸模糊的歷史剪影。僅以農民的法律意識而言,除特別封閉落后的鄉村外,大部分地區的農民的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已有大幅度提高,至少不像某些有識之士所認為的那樣淡薄。當下的鄉村社會似乎已為法治秩序基本提供了相應的前提和基礎。那么今天的鄉村社會是否實現法治了呢?
筆者近幾年在安徽、湖南、浙江、河南、內蒙等地農村的生活經驗和社會調查發現,法治之于鄉村社會有如空中樓閣、海市蜃樓,法律在鄉村社會中依然處于尷尬的地位。農民在遇到利益糾紛時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法律,“打官司”、“告狀”等幾乎成了當下的第一反應,然而究竟有多少人采取了法律手段解決糾紛則值得深究。在筆者看來,糾紛解決中在多大程度上運用法律是法治程度的一個重要判準。調查發現,農民在現實生活中運用法律的情況并沒有隨著法律意識的提高而增加,反而出現了新的“無訟”現象。新無訟現象的存在顯然不是因為鄉村社會中的利益摩擦和各種糾紛減少甚至不存在了,事實恰恰相反。農民之所以不愿通過訴訟解決糾紛,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人情、面子的影響,但更多的是因為一則訴訟成本高,二則農民失去了對法律或司法的基本信任。訴訟成本較高一直成為阻礙農民訴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帝國時期如此,當今亦然。楊聯陞先生在《中華帝國的作息時間表》中指出了這一點:訴訟的昂貴在中華帝國是盡人皆知的,對于容易成為官樣文章和腐敗之犧牲品的農民來說,尤其如此。訴訟案嚴重干擾了農民的時間表,對于土里刨食的農民不啻為一個沉重的負擔。在我們的調查中,這種情況于今依然沒有多大改變。當真正拿起法律武器維權的時候,農民的日常生活即被打亂,而這種日常生活更多的被打工或務農所占據,打工或務農恰是農民的衣食之源。顯然,僅時間的消耗對無閑暇余裕的農民而言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農民遇到糾紛往往經過一番理性考量后沒有選擇訴訟,而是選擇了私了、妥協或隱忍。當我們問及為什么不通過法律的途徑解決時,大多數答案集中在訴訟成本上,一則延請律師花費不菲,二則漫長的法律程序影響了農民的收入。故此,一般而言,農民在遇到侵權時并不會選擇法律而是尋求其他途徑以求解決。導致無訟的另一個原因在于司法的公正性由于權力、金錢甚至黑惡勢力的介入而遭到嚴重削弱、侵蝕,從而導致農民并不相信法律。調查發現,當下農民的“冤屈”大多來自于強者的欺凌,而強者與司法機關通過利益結盟從而形成一個致密的權力網絡,使得法律成了保護強者的工具而非弱者權利救濟的最后稻草。調查中一個中年農民說道:現在最守法的是老百姓,最不守法的是那些當官兒的和有錢的,最可怕的是當官的和有錢的勾結在一起!一位常年在外打工的青年農民甚至認為普法運動的結果是制造了順民,縱容了蠻官。
當下鄉村社會的無訟,和費先生所言的因禮治和熟人社會而導致的無訟相比有著根本的區別。如果說鄉土中國中的無訟是因為鄉村是封閉自足的社區,自身有一套糾紛解決機制從而無需向外借助于國家法律,那么當下鄉村社會的無訟,則因為法律雖已進入鄉村,但在異化的法律運作中弱者處于更為不利的境地從而不愿求助于法律。有些鄉村懼訟現象比較普遍,足見一斑。在內蒙的鄉村調查發現,多數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具有較高的法律意識卻有著較低的法律期待,也即受訪者雖然懂法卻不愿用法,原因在于他們認為法律是富人和閑人的游戲,窮人只有在極端的情況,如出了命案或把事情捅大才有可能得到法律的眷顧。調查中遇到一村民告村支部書記的事情。該村民因受到村書記的不公正對待要將其貪污的罪行告上法庭,該書記叫囂道:有本事你去告,你用自己的錢打官司,我用公家的錢陪你打,耗死你!結果,該村民知難而退。最近湖南的調查也遇到類似的個案。一位劉姓村民已經收集到村里組長的貪污證據,告了三年至今未果。該組長公開承認貪污事實但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在此期間他又到鄉、區和市各級部門上訪均被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深感絕望。幾十年前,訴訟也許在農民看來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現在反倒成了一種能力和地位的象征。若能將某人送上法庭在鄉村無疑是一件相當“長臉”的事。如果說,法律從來都是各方利益群體博弈的結果,那么在當下中國鄉村社會中法律實踐則是一種失衡的博弈。在司法實踐中,法律能不能得到公正執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事人之間的博弈。如果力量均平,或許法律會以調解或公平執行的形式出現;如果力量失衡,法律的公正執行很可能變得不現實。對此,一個老年婦女憤怒地說道:現在打官司哪里有公平,打的都是關系和錢。你有錢有人法律就保護你,無錢無人就是你完全有理,法律也不會保護你。在調查中,受訪者講了許多身邊法律不公平的事情,或許他們對于法律存在一定的誤解,或許有夸大、歪曲的成分,但各種版本的“腐敗”故事使農民失去了對于法律曾經抱有的信任和期望。
從上述討論看,當下的中國鄉村正處于轉型期,禮已失去了原有的約束力而法的“故事”正以各種形式流傳,法律在鄉間并未產生普遍的有效性。如果說禮治失去了原有的社會基礎,而法治的社會基礎尚未形成,那么禮崩樂壞法未行的鄉村社會為何并未出現顯性的秩序危機呢?當下鄉村社會既非禮治秩序也非法治秩序,究竟屬于何種秩序型態呢?一言以蔽之:勢治秩序!在筆者看來,勢治秩序已成為轉型鄉村社會一種新的型態。作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語言,勢不僅與姿勢、形勢有關,更多的是指勢力、權力、力量等。在傳統社會中,禮治的實現盡管與紳士或長老所具有的勢密不可分,但這種勢在很大程度上黏附在道德、等級、權威、面子之上。在糾紛調解中,更多的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而非以勢壓人。當下的鄉村社會,新舊道德正處于替嬗之間,道德空間為各種形式、各種性質的倫理道德所充斥,且彼此之間存在較大的沖突,而法律則存在文本與實踐、事實與規范之間的背離。鄉村社會可謂是一個多元權威并存而又相互沖突抵牾的場域。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市場以及形形色色的社會力量進入鄉村,使得當下鄉村社會出現紅色、灰色以及黑色三色勢力并存的格局,進一步加劇了大多數農民的弱勢地位。在鄉村糾紛中,禮和法幾乎完全被勢所取代,利益愈大的糾紛其解決愈依賴勢的運作。當制度化的渠道不能為弱者提供權利救濟時,弱者要么選擇私力救濟要么選擇妥協和隱忍,而在現實中更多的選擇了后者。富有隱忍精神和慣習的中國農民則為勢治秩序提供了心理基礎。由此可以發現,當下鄉村社會表面的穩定是以弱者犧牲個人權益為代價的,而這種犧牲一旦超出個人所能承受的極限則可能發生悲劇性結果。勢治秩序的存在折射出我國社會運行過程中潛伏的深層危機,為政者可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