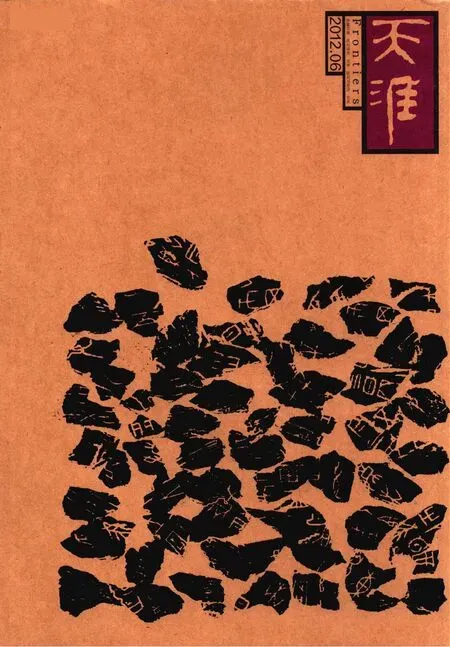如何建立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平衡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連清川在FT中文網發表文章,指出,自由與平等之間,充滿了極大的矛盾,而整個歐美的國家政策重點,幾乎就是在這二者之間尋找平衡道路的過程。連清川試圖通過已故美國紐約大學教授朱特的論述來尋找答案。
連清川稱朱特為“偉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在2010年的遺著《沉疴遍地》中,朱特幾乎都流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輝煌里。在凱恩斯主義與羅斯福新政的光環下,“信任、合作、累進稅和干預主義的國家在1945年后的幾十年里給西方社會留下了什么?簡單的回答是:不同程度的安全、繁榮、社會服務和更加平等”。的確,在新世紀光臨之前的五十年時間里,西方,尤其是歐洲,建立了一系列福利國家的模版,通過高額的累進稅,強制性地在社會中制造了相對的平等,卻并沒有損害民主國家的本質。那是歐洲的黃金時代。
但是,今天的歐洲,以及美國,顯然已經沉淪在新一輪的不平等的狀態之中。在經過幾十年的繁榮之后,福利國家幾乎必然所帶來的經濟活力的喪失,導致了歐洲普遍的社會改革。而開啟那個時代的是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里根總統。他們的主要手段就是對國家所強制管制的許多政策松綁,允許企業進行自由競爭,并且,在許多領域中,將國家福利的包袱甩給了私營企業,進行了私有化。在英國的布萊爾和美國的克林頓時期,這種政策登峰造極,的確帶來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空前繁榮,創造力極大激發,全球化狂飆突進。但是,這個時期同樣帶來兩個嚴重的后果:其一是社會的貧富分化再次加劇;其二是政府的角色退化,公共功能減弱。朱特寫道,凱恩斯相信“如果資本主義的運作被縮小到僅僅是為富人提供變得更富的手段,那么,資本主義就不能生存下去”。
當然,朱特的能力并不僅僅止于懷舊的感嘆和憤怒的指控,他要充當的是滅法時代的救世巫師。他的藥方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作為公共福利的承擔者,必須提供多數的公共服務,例如郵政和鐵路;而經濟計劃,在民主的前提下不必擔心被指控獨裁,應該擔任更大的作用;福利國家的前提是正確的,只是必須在自由的前提下進行。
如果簡單地歸結朱特的理論就是:保證競爭性市場的自由;政府承擔多數的公共服務功能;增加計劃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以福利國家的再分配制度實現相對平等。
連清川說,中國現在面臨的局勢是二戰前和冷戰后歐洲問題的總和,面臨著自由赤字和平等赤字的雙重困境。
今天中國的國家制度控制著從政治制度到經濟制度的幾乎所有領域。它包辦了所有的公共事務和大多數的經濟事務。中國從來沒有像歐洲那樣把公共服務交由私營企業來經營,而是自始至終由國家來承擔。在1978年之后看似有些公共服務交由企業來經營了,實際上仍然是由國家控制的國營企業來運行。
國民在這種情況下對于公共服務根本無從置喙,更無從談到什么選擇了。而公共服務提供的質量是否能夠得到提高,關鍵在于公眾是否有機會能夠參與到整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監督之中。顯然,對于所有的公共事務,公眾沒有任何途徑得以參與。
在缺乏自由的前提之下,談公共服務應該由誰來提供的問題,無異于天方夜譚。朱特在其藥方中提到鐵路經營權的問題,他認為鐵路應該由國家提供服務,因為私營企業罔顧了許多未能獲得利益的少數人的需求。但這個案例恰恰說明了在中國這個藥方是多么地令人恐懼:我們的鐵路服務本來就是由政府提供的,但是它帶給了我們7·23,帶給我們奢侈動車,帶給我們劉志軍。
而我們的平等赤字同樣地令人恐懼。朱特所描述的西方社會倫理衰退,自然是合理的。由于解禁政策的普遍施行,拜物成為了世界通行的宗教。所有世界的英雄人物都只蒼白地剩下了一群靈魂空洞的企業家,無論他們發家的過程多么地暴力與無恥。但是那個社會里至少還有法律與公民社會進行平衡,而福利國家的百足之蟲,依然庇佑著天下的寒士。
但是如今中國這個社會已經變成了十七、十八世紀的資本主義了。一方面我們是“英雄不問出處”,在幾乎所有的企業都帶著原罪的情況下,國家放任殘酷的叢林法則肆意橫行,唐駿、禹晉永之流不受懲罰地成為致富的典型,以非理性的財富追逐刺激整個民族的金錢游戲,從而破壞市場的基本準則;另一方面自由匱乏下的權力與資本的瘋狂結合,無休止地吞噬中下層民眾的生活資源,持續推動少數人不斷上行和多數人不斷下行。在資源分配的本身已經天然不合理的情況之下,再分配的機制并不是提供福利,而是提供少數人的優先占有權,平等形態自然日益惡化了。
巫師朱特在書中寫道:極端不平等的社會也是不穩定的社會。不平等會引起內部分裂,而且,遲早會引起內部斗爭,其結果往往是不民主的。
最后,連清川說,對于中國的前途,許多人有各種各樣的幻想,卻唯一沒有這樣的預言。崩塌社會的摧毀力是無方向的、隨意的和狂躁的,它并不區分人群和階層。所有人都是所有人的敵人。無人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