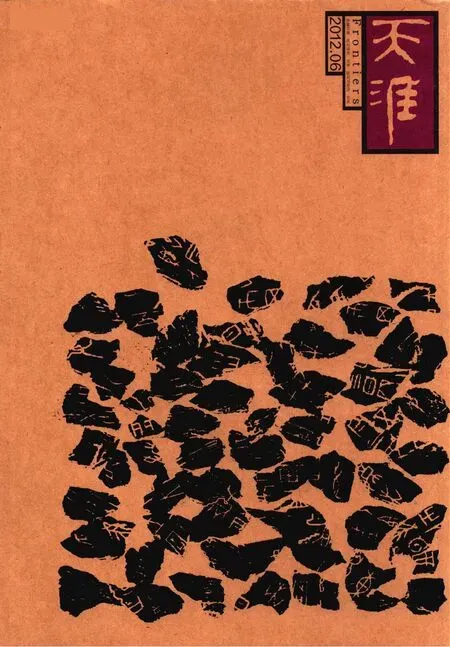重構農民與政治之間的關系
趙曉峰
農民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是近現代政治學關注的重要理論命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中國共產黨通過階級分析法的輸入,打破了廣大農村原有的社會結構,充分動員了中下層農民的革命積極性,有效解決了革命的動力源問題,最終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選擇,獲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新中國建立以后,以土地革命為肇端,黨和政府延續了革命時期的農村政策,確立了以階級劃分為基本依據的分類治理原則,建立了農民對國家的高度政治認同,充分地將農民整合進國家政治發展需要的軌道上,為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初步工業化進程奠定了牢固的鄉村基礎。
人民公社解體以后,鄉村社會逐步確立起“鄉政村治”的政治體制架構,國家試圖以民主政治替代階級政治,通過村民自治制度的推進來重建農民與國家的關系。然而,有農村調查經驗的人很快就發現,農民對選票政治并沒有表現出令人期待的熱情,參與民主投票的積極性普遍比較差,村民選舉往往成為鄉鎮干部和村莊農民精英自娛自樂的事情,普通農民的政治冷漠傾向非常明顯。農民認為選誰不選誰,對自己的日常生活沒有什么太大的影響,選舉不過是要換個村干部來管自己罷了,一樣地要催糧派款,老百姓的日子還不得照常過。也有農民認為選舉沒有什么實質意義,選來選去就那幾個人,自己的選票也發揮不了什么作用。所以,取消農業稅以前的村莊,被一些學者稱為“無政治的村莊”。
村莊是“無政治”的,但是農民身上仍然流露著較強的政治性。即便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農民負擔居高不下的時代,農民也依然普遍認為“皇糧國稅,天經地義”。雖然稅費的負擔幾乎已經要超出農民能夠承受的限度,但是農民提出質疑的往往不是農業稅的征收額度問題,而是鄉統籌和村提留為什么會漲得那么快升得那么高的問題。一些農民一時交不起農業稅費,也依然認可村干部將拖欠的稅費“掛”著,記在賬上,留待有錢的時候再交。農民會為交糧納稅的行為跟基層干部扯皮,將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混淆起來給村干部出難題,提出“不解決問題就不交錢”的訴求,卻不會質疑村干部催糧派款行為的合法性。因此,取消農業稅費以前,村民自治制度的實施沒有能夠真正將農民拖進基層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當中,但是農民的政治性并沒有完全消失,他們依然講國家政策,講法律法規,講原則,講“大道理”,農民在村莊選舉中的政治行動能力比較差,可在日常的治理實踐中還保有較強的政治性。
取消農業稅費以后,農民身上僅存的政治性也在迅速流失。稅費改革不僅是取消農業稅費那樣簡單,而且還伴隨著一系列農村配套政策的調整,深刻地影響著農民的行為變遷邏輯。以農村債權債務鎖定政策為例,基本上所有的省市在配套政策的制定中,都嚴格規定,基層干部不能強制性向“尾欠戶”催繳稅費,以致稅費尾欠的交與不交成了當事人自己的事情,其結果就是幾乎所有的尾欠戶都拒絕繳納先前“掛”在賬上的款項。由此引發的政策實踐效應是連鎖性的,尾欠戶得意洋洋,“我就是不交,誰能拿我怎么辦呢?國家政策都說了,交不起可以不交嗎?”而那些足額繳納稅費的農戶也產生了發自內心的不公平感,“我又不是窩囊廢,憑什么別人可以不交,偏要我交;想要再向我收錢,門都沒有!”如此一來,農民都開始傾向于講自己的“小道理”,而不再講國家及村莊的“大道理”,導致后稅費時代的“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等政策失去了實施的村莊基礎。即便是對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如灌溉水渠的維護、村莊道路的維修等公益事業,農民也既不愿意出勞,更不愿意出資,鄉村社會陷入到了新的治理困境當中。
農民政治性的流失,既與國家政策的不連續性有關,又與消費主義導向的市場經濟過度的膨脹式發展有關。改革開放以來,村莊社區逐漸被打造成了市場社會、經濟社會,農民生活的關注重心轉移到發家致富上來,財富倫理進行了重組,既然一切要看個體的致富能力和家庭的經濟實力,那么只要我能掙到錢就是有本事,“財富不論出處”,可以“笑貧”卻可以“不笑娼”。市場稀釋了村莊,瓦解了農民的集體意識和村落共同體意識,型塑了農民“只講個體權利,不講個體義務”的日常政治生活品性,“只要不觸及我的個體利益,不讓我出錢,你想怎么搞都行!”農民個體主義意識快速的殘缺式發展,使農民不僅沒有能夠成為現代公民,難以自覺遵守國家涉農法律法規及執行國家涉農政策,而且也丟棄了地方性文化規范,政治性被嚴重摧毀,不講“公”只講“私”,不講國家政策和地方“大道理”只講個體“小道理”的現象逐步擴散化,逐漸侵蝕到了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改變了鄉村社會的性質。
喪失政治性的農民,處處與基層干部過不去,“你不是要修路嗎,我就是不出錢,看你怎么辦?”“要我出錢也可以,先把別人的稅費尾欠收上來再說!”“修水渠,又不是我一家的事情,你有本事,把別人家的都收起來,我再考慮交不交。”遇到類似情形,基層干部往往表現的是束手無策,“與其自己作難,不如啥都不管”,基層組織成了鄉村里的“維持會”,“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過且過得了,何必要去瞎操心還不落好呢?
然而,村干部的普遍不作為肯定是不能長久的現象,鄉鎮政權不可能置之不理。置身于壓力型體制,受控于目標管理責任制,鄉鎮政權必須竭盡全力推進地方上的新農村建設工程,最起碼也要樹立起幾個典型村、樣板村,以緩解“迎檢”的壓力。由此,村莊里的富人群體開始進入鄉鎮干部的視野,成為“香餑餑”。在鄉鎮領導的竭力邀請和大力支持下,農民經濟精英越來越多地走上村莊政治舞臺,構建了新的村級權力結構。富人治村,不需要從農民手中收取一分錢,也不需要同農民協商,而主要依靠富人掌控的經濟資源和社會關系資源,通過自墊資金或是爭資跑項等手段,就能較好地解決村莊里的公共品供給問題。實際上,不僅是富人群體,“混混”也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以為農民提供公共品的辦法,成為“好混混”,獲得鄉鎮領導的青睞,進而把持村莊權力,使農民生活在暴力與屈辱之下。而且,混混治村的現象和富人治村的現象一樣,都有快速發展的勢頭。
富人治村也好,混混治村也罷,類似現象的大量出現,都與農民政治性的流失有極大的關系。只要不讓自己出錢出力,又能享受到公共品供給的好處,管你是誰當村干部都行。當然,如果是拳頭硬、心又比較狠的混混當村干部,“人往你面前一站,讓你交錢修路,你也不能不交吧!”“混混有手段,不像那些老好人干部,一遇到點阻力,就退縮了,啥事也不敢做。他們敢干,軟的不行,就來硬的。只要能辦成事,大家也就無話可說了。”農民是非觀的混亂,政治性、原則性的流失,使他們失去了對村莊權力的影響能力,也失去了參與村莊政治和村級治理的機會。為此,普通農民不得不開始承受不講政治性的代價,主動地,抑或被動地被拋出了基層民主政治發展的軌道,成為“落單的農民”。
除此以外,“無政治性的農民”的大量涌現還與農民上訪問題的日益嚴重有著緊密的關聯。傳統的觀點認為農民是為了維護公民權利和受侵犯的利益而去抗爭,去維權,去上訪的,但是從基層實踐的情況來看,此種類型的上訪僅在農民上訪總量中占很少一部分。在農民上訪問題中,有一種新的正在快速增長的上訪類型,即是農民的牟利性上訪,他們可以提出種種理由,甚至可以憑空捏造一個借口,就去找地方政府上訪,并要求解決反映的問題。問題自然是無法解決的,但是上訪農民卻可以憑此獲得各種好處,比如獲得特批的低保指標等,在“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的辦法來擺平”的地方維穩邏輯下,“會哭的孩子總會有奶吃的”。而政治性流失之后,農民就可以不講原則、不講正氣,找個理由就可以去找政府上訪,從而加重了國家信訪制度的負載,也使農民正當的利益表達受到了負面的影響,不利于基層社會的穩定和國家合法性形象的營造。
農民的政治性是鄉村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石,也是塑造農民的現代公民素質和公民政治品格的基礎。因此,在當前國家極力推崇社會建設的背景下,應該擴大農民的民主權利,探索參與式民主的實踐機制,讓農民不僅能夠參與投票選舉,而且還能夠參與到日常的村莊政治決策與村級治理實踐當中,重構農民與政治之間的關系,通過以社區為中介的社會建設,逐步重建農民的政治性,落實和保障農民的公民權利,推進鄉村社會的民主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