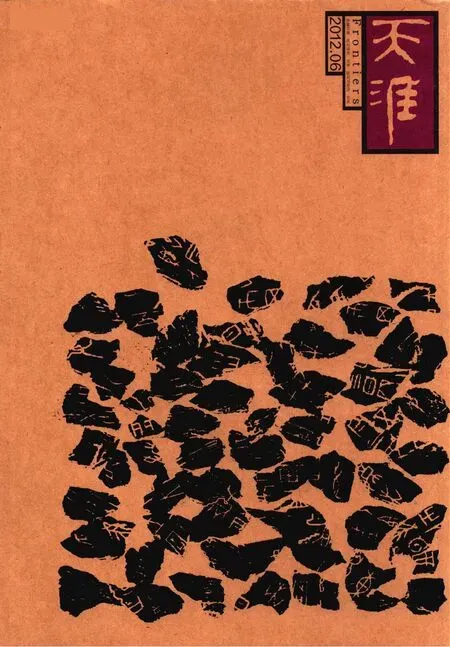良宵
張楚
一
她剛搬到麻灣時,村人并未覺得有何異樣。或許在他們看來,這只是位干凈的老太太,衣著素樸,臉上一水褶子,梳了低低的發髻,站在櫻桃樹下,束手束腳,竟有幾分與年歲不相稱的羞怯。隔壁的婦人偶來瞅了幾眼,閑聊幾句,這才曉得是村里王靜生的遠房姨媽,怎么想起要到鄉下住上段時日,這才勞煩她外甥在村西租了三間瓦房。行李也不甚多,幾床被褥,一只泛黃的皮箱。隨行的還有一只白鵝。白鵝也老了,翼羽暗淡,喙上的肉瘤失了色澤,在屋檐下懨懨臥著。若是人來,她就從包裹里掏栗子、榛子類的堅果,笑著塞進人家掌心,慢聲慢語地催促道,吃吧,吃吧。她的牙齒大抵是假牙,白如玉米,笑時幾乎不見牙齦。
翌日,雞沒叫上三遍就早早爬起,繞村子轉了半圈。四月初,清冷了一冬的村子,難免透些活潑。櫻桃就不消說了,頂一樹雪,招了細腰蜂。單說荒地里大片的紫云英,于風中凝斂成水晶,流出光和蜜來。后來她走累了,坐上塊青石歇腳。有村人牽著黃牛、騾子從她身旁攆過,難免都瞥上兩眼。她呢,但凡有人瞅她,都要笑一笑,嘴唇被暖陽打成瓣薔薇。
也不喜歡串門。村子里的婦女,如果不是農忙季節,屁股底下是安了陀螺的。尤其是此處的女人,舌頭都要比別村的長兩寸。就有那好事的,借串門的名義來,吃幾枚老太太的堅果,喝幾盞老太太泡的茉莉花茶,再打聽些該問不該問的話,想傳與旁人聽。可這老太太,安靜得像一只貓,村婦們在炕沿上東拉西扯,她也不插嘴。問她退休前是干哪行的?她說,當教師。問她兒女幾個?她說,兩兒一女。問她多大年歲?她說,忘了。問她老伴是否健在?她說,去世二十多年了。人家問她話時,大眼珠子瞪得溜圓,而她呢,只瞇眼盯著墻旮旯,有一搭沒一搭地應著。有時那只老鵝搖擺著肥碩的屁股踱進屋,她就順手抓了脖子拎上炕,箍在懷里,榆樹皮手細細摩挲著。那鵝也不吭聲,閉了眼,仿佛在她懷里死去一般。
閑婦們就漸漸沒了興致,不如何來往。只有一個諢號“劉三姐”的,時不時跑上一趟,倒比王靜生還勤些。蒸了野菜餡的餃子趁熱端一碗來,燉了排骨趁熱送幾塊來,親閨女似的。老太太推辭幾句,就接了,也不見有言謝的套話。“劉三姐”似乎也不在乎。在村人眼里,她本來就是個有點缺心眼的“女光棍”。所謂“女光棍”,是周莊、夏莊、馬莊、麻灣一帶獨有的叫法,專指那些性情如男人的女人。哪個村不出一兩個“女光棍”?譬如夏莊,最有名的女光棍是周素英,專跟男人賭錢鬧鬼;譬如馬莊,最有名的女光棍是劉美蘭,蹬著大頭皮靴,領了幫嗩吶手跑紅喜白喪之事;麻灣呢,若說有女光棍,大抵就是“劉三姐”了。“劉三姐”其實長得還算英俏,只是脾性躁,嗓門粗,腸子直,有事沒事喜歡扯著鐵嗓子唱兩句。
二
老太太過了五六日,將麻灣村周遭咂摸透了。這個叫麻灣的村莊,地處冀東平原,西行百里是燕山,東行百里是渤海,怪的卻是靠山不吃山,靠海不吃海,反倒以植棉聞名。據說老輩子,宮里用的棉花全由此處沿京東北運河載去。不過現下卻是荒了手藝,年輕的跑到城里做泥瓦匠,只有老農人種幾畝棉花。麻灣呢,除了村西有塊方圓百米的土崗,全然是平地。若是站荒田里環四周,便是由地平線草草勾勒的渾圓。現下清明才過,麥子返青不久,作物都還歸倉,除了野花草,只有柳樹頂了綠苞芽,飛著些醬色的七星瓢蟲。
那天她從村西的土崗下過。雖走得慢,還是呼哧帶喘,就順勢找了干凈的一塊地角坐下。屁股還沒涼,便聽到不遠處傳來孩子們的叫罵聲。手搭了涼棚去瞅,卻是一個孩子在前邊跑,一幫孩子在后身瘋追。那孩子蹽得比野兔子還快,轉眼就從她身邊旋風般刮過,直刮到那黃土崗上。那幫孩子呢,也就不再窮追,只在崗下唧唧歪歪罵個不休。這麻灣的方言倒也有點意思,平心靜氣說起來時,三拐五拐的猶如唱評戲,罵起人來時則脆生利落,簡直京戲里的念白一般。那幫崽子兀自咒罵一通,這才怏怏散去。
老太太瞥了瞥他們的背影,又去斜眼瞅那土崗。不會兒,土崗上便隱約探出個圓頭,小心逡巡著崗下。大概看是孩子們走了,這才約略著直起身抖抖索索矗在那兒。孩子套件過了膝的破夾克,晃蕩晃蕩的,雞胸脯裹件漏眼的長袖海魂衫。見老太太望他,竟俯身撿起塊土坷垃扔過來,不偏不倚沖她額頭上。老太太倒是吭也沒吭一聲,只順手摸了摸額頭,又朝那崗上望去。孩子就不見了。
晚上,老太太蒸了鍋饅頭,干嚼了半個,就披了羽絨服拎了馬扎坐院子里。夜晚的村莊靜得早,偶有耗子鉆垛草雞鬧窩。墻頭似有野貓出沒。老太太定睛瞅了瞅,拎了馬扎進屋,打開戲曲頻道,正演白玉霜的《木蘭從軍》,忍不住把睡著的老鵝抱上炕,攬在懷里,摸它溫熱的羽,摸它冰涼的喙,再閉了眼細細聽戲。須臾,過堂屋傳來輕微的腳步聲,側耳聽,倏爾沒了,過了會兒,腳步聲重隱約響起,老太太就問:“誰啊?”話音未落已是一派沉寂。心想這雙耳朵,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晨起時,發現鍋里的饅頭少了幾個。心想不會是被野貓叼走了吧?出了院子,又想不起到哪里溜達,就念起了昨日那個野孩子,這么想著,吆喝了老鵝,慢慢悠悠朝土崗走去。她這院子靠村西邊,離崗最近,不過三四百米,可若真一步一步量起來又無比漫長。想當年,她能一連串翻百十個筋斗云。
土崗矗眼前時,她叉著腰大口大口地喘息起來。崗也不高,只不過人太矮了,崗也不長,只不過人的胸腹太窄了。土崗四周除了雜生的幾株野榆錢,便是蒲公英,蒲公英密密麻麻洇成一片,遠看仿若一塊安靜的黃金,近看則是朵朵小向日葵。鼻子里澀香之氣漸發濃烈,她從兜里掏出枚榛子,嘎嘣嘎嘣嚼起來。人老了,牙掉了,饞蟲還活著,吃了一輩子的堅果看來是戒不掉了。后來她想,何不去崗上看看?就繞到那條斜坡前仔細端詳,這一看先就心虛。斜坡雖不是很長,卻陡峭得很,別說是她,就是十五六的愣小子也會發憷。斷了念想,捶著腰眼慢慢悠悠回了家。
這一晚,老太太做的炸醬面。飯后照例躺炕上看電視。說是看電視,不如說是聽電視。眼皮子磕磕絆絆時睜時閉,只耳朵支棱著聽胡琴聲咿咿呀呀。待聽到過堂屋傳來“吸溜吸溜”的聲響,這才驟然醒來,輕咳兩聲,聲響就淹沒在無涯的黑暗中了。她把電視聲音調大些,輕手輕腳穿了鞋子下炕,猛一挑門簾,就見一團矮小黑影躥到院子里。那晚夜空無月,她只瞅到影子晃蕩著爬上矮墻,倏地下就不見。轉身將過堂屋的燈打開,卻見剩下的炸醬面沒了,只碗邊粘了硬邦邦幾根。似乎就明白了。如果沒有猜錯,這偷食的人,除了崗上那野孩子,也不會再有旁人了。心里難免嘀咕起來,這孩子是如何的一回事?為何吃不上飯?爹娘去做什么了?村里就沒旁的親戚了?便尋思有機會了,定要問問那“劉三姐”。
這“劉三姐”倒是好幾日沒來。聽村子里的喇叭,好像麻灣村家家要簽什么合同。自己這房子是租來的,倒也沒往心里去。炕上坐了會兒,便又愣愣想起那野孩子的小眉眼,心格外綿軟,竟隱隱盼起夜晚的降臨了。翌日,未及晌午,老太太就盤算著晚上煮何飯菜。這幾天不是干饅頭就是稀面條,那偷食的孩子估計也吃不飽。思來想去,便要做“菠蘿醬鯽魚”。
小賣部里倒是有鯽魚,可卻沒有菠蘿,老太太就買了幾根芹菜。芹菜味沖,又有股異香,雖不及菠蘿,想必也不會差到哪里。回了家就刮魚鱗剖魚腹,將腸子肚子喂給老鵝。又將空魚肚塞上姜片、蔥段和豆瓣醬,才用鐵鍋小火燉起來。這是個岑寂的午后,同往常一樣,只聽得細春風拂過老屋檐,只聽得嫩葉拱出蒼樹皮,只聽得鄰居豬圈的約克豬懶懶呻吟……這樣閑坐了很久,這才把火關了。光一寸一寸縮,夜一寸一寸脹,她草草喝了碗稀飯,將過頭屋的燈打開,早早貓進被窩,照例看電視。
孩子又來了,先是鍋蓋碰鍋沿的清脆聲,然后是電飯鍋被揭開的茲啦聲,再是不當心被熱氣熏了手又不得不強忍著的“哎呀”聲,飯菜入嗓猛然吞咽的咕咚聲……最后,是窸窸窣窣的衣褲和門簾摩擦聲。不過五六分鐘,聲音就消散在夜里,又是漫漫的靜。她披上衣裳躡手躡腳踱到庭院。月亮大而黃,孩子正在翻墻,不曉得是如何了,這回翻了幾次都沒翻上去。后來,他從豬圈旁搬了塊石頭,探著身子踮著腳才夠住墻頭。怪的是他沒立馬跳過去,而是騎矮墻上,雙腿耷拉著呆坐了良久。后來,老太太看到孩子的肩胛骨在月光下一顫一顫地抖索起來。
老太太沒敢驚擾他,默然看了片刻回房,靠著門閂愣神。
三
翌日清晨便早早出門。老鵝在她身后搖搖擺擺尾隨著。她知道村里有家小賣店,專賣冷鮮肉。那天,小賣部人倒不少,有人在扯成匹的帳子布,看來是村里有人過世了。老太太戴上花鏡,觀瞧半天,這才吩咐店主從豬背腿上割了一斤,而后帶著老鵝回了家。中午時,忍不住一個人跑到黃土崗下坐了個把時辰。風比昨日暖些,吹得骨頭酥癢,荒田里的紫云英被陽光照成一團紫霧。可孩子卻沒出現,她愣愣地盯了會兒野榆錢樹,這才走了。及至下午,老太太切姜剝蒜,又配了紅椒、桂圓、八角、茴香和十三香,用高壓鍋將肉悶了,肉香不久彌漫開來。
期間倒是有幾個閑婦過來串門。她們有陣子沒來了,進了屋先聳動著鼻子問“咋這香呢?”見是老太太燉肉,又夸她廚藝高超,接著喟嘆起如今的兒子媳婦們,全是金貴命,雖然都是土里刨食的,卻連餃子也包不好,年三十煮破了一鍋,簡直成了餛飩片湯。老太太只縮在炕腳聽,一句話也不插。又聽她們說,縣政府的人來了七八次,看樣子村子搬遷是避免不了的。老太太這才問了句:村子搬到哪兒啊?干嘛要搬啊?她們的興致就被勾起來了,哄嚷著說,麻灣和附近的周莊、夏莊,據科學家們檢測,地下埋著大量鐵礦。大量是啥概念呢?就是儲存量位居全國第三。全國第三哪,可不是鬧著玩的!這些人四五年前就來勘探,折騰了幾年,據說明年就要動工采礦了,這不,鎮上天天逼著簽拆遷合同。用不了多久,麻灣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巨大的地下采礦場。老太太“咦”了聲問道,你們搬到哪兒啊?沒了田地,日子怎么過?她們就揚著眉角嬉笑說,我們巴不得搬到縣城,當城里人呢。錢嘛,不是有賠償款嗎?這世道,有了錢,啥都不用怕……
可算是走了。老太太捶了捶腰,不禁去看鍋里的肉。其實本想跟她們問問那孩子的事,可話到嘴邊又咽了下去。這幫長舌婦,定會好奇她為何問詢。何況,又何必非要知曉孩子的事?她跟他,只打了個照面,閑話也沒說上過一席。他要是餓了,就來這里吃兩口,填飽肚子;他若是有了下家,不再來偷食,自當沒有過這回事。老太太瞇眼在炕上打起盹來。等睜開眼,天已大黑,蹣跚著去過堂屋看看燉的肉,明顯是吃剩的。孩子吃了不少,看來很對他胃口呢。老太太竟有些隱隱的得意,方沉沉睡去。
次日早早就起來,栽了兩壟韭菜。韭菜根是王靜生送的,順便捎了一糞箕子豬糞。這個遠房外甥,跟她并不親近,反倒有些罅隙。老太太也并不介懷,送了他一雙自己繡的棉拖鞋。王靜生接了,又悶悶地抽了一袋煙,這才趿拉著鞋轉身離去。等外甥走了,老太太就坐到屋檐下曬太陽,曬著曬著有些惡心,想必是這幾天受了風寒,隨口吞了幾粒藥片,倒頭睡起來。中間醒來幾次,只覺得骨頭酸軟喉嚨脹痛,喝了口熱水又漸漸迷糊過去。其間聞得老鵝嘎嘎亂叫,想必是餓了來討食,卻沒氣力爬起來喂它。醒來時太陽已爬上屋檐,就拌了糠菜去喂,卻發現老鵝沒了。
這老鵝,跟了她十三年,是她從小區門口撿的。肯定是誰家的孩子從寵物市場買來,養得不耐煩隨手扔掉了。城里的孩子,就是沒耐性。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揣兜里帶回家。當初也只是小小一團鵝黃,睜了驚恐的眼動也不敢動,誰成想竟長成偌大一只呢?兒女們是極少來的,通常只有她和它,晨起去中山公園散步,中午吧唧吧唧嚼著青菜,聽收音機里唱著老戲,傍晚呢,窩在沙發里打盹,半夜醒來時方將電視關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想說話了就和它嘮叨兩句,生氣了就踹它兩腳,它不記仇,依舊影子似的隨著她,貼著她,膩著她。
老太太難免心慌起來,顛著老寒腿在院子四周搜尋一番,仍沒得蹤跡。猛然想起那孩子,心就咯噔了一下。該不會夜晚來時不見吃的,索性將它逮走燉了吧?
那晚,灶冷燈滅,她早早在過堂屋候了,大氣也不敢喘一口。果不其然孩子仍是來了。當他在灶臺上翻尋時,她冷不丁一把就攥了他胳膊。他胳膊如此干枯,掙了兩掙竟沒有脫開。老太太隨手開了燈,這才不緊不慢地問道:“我的鵝呢?”
這倒是她與他頭一次如此近地說話。他比前些日子似乎更細瘦了,有那么片刻,她竟懷疑他會不會被過堂風給吹走。他的眼也是紅腫的,嘴角生了水泡。老太太又問道:“是不是你把鵝偷走了?”孩子點點頭。她想也沒想就從他后腦勺扇了一巴掌,“是不是把鵝給吃了?”她顫抖著聲音問。孩子又是點點頭。老太太“哎呀”一聲,順勢從鍋臺拎了把刷鍋的炊具,捋起他衣袖就抽打起來。抽著抽著便瞧得他胳膊上全是銀元大小的紅斑,一圈連一圈,看得心里麻麻幽幽,索性撒了他,一屁股坐在灶臺上,默默盯了他半晌,這才擺擺手說:“你走吧,走吧。以后不要再來了。”孩子一愣,卻并沒有動。老太太聽他嘟囔道:“我奶奶死了……我殺了它祭祀……”老太太不再搭理他,轉身回了屋子,和衣躺下。
這一躺就是兩天。中間清醒時老太太想,該不會是大限已到吧?然而轉念想想,死在這個叫麻灣的村里也沒什么不好。這個村子,地上有棉花,地下有鐵礦,也算是寶地了。迷迷瞪瞪間又覺得自己化了妝緩步走上那戲臺,不成想環顧四周,琴師未來,臺下一個人也無,竟悵然起來,旋爾又自嘲,都這把老骨頭了,竟還怕沒人來聽自己唱戲……
等再次睜開眼,屋里的燈怎么就亮了。側身朝門外望,先看到炕沿上擺著副碗筷,碗里尚冒著熱氣。老太太爬起來張看,卻是碗疙瘩湯,香油花浮著,白雞蛋臥著,雞蛋旁是幾粒剝好的新蒜。老太太心里熱了下,小口小口著吸溜起來。大抵是餓得塌鍋了,雖然缺鹽少醋,竟覺得格外香甜。就想,會有誰來呢,若是靜生或“劉三姐”,斷不會悄沒聲地來了又走,看來,也只有那孩子了。定是他過來找食,見她臥床生病,這才煮了疙瘩湯。看她睡得香,又不忍叫醒,才將疙瘩湯放在炕沿上,睜眼就能看到。小小年歲,心眼倒是不少呢。雖然他將老鵝殺了,心里百般怨恨,可誰沒辦過蠢事呢?何況一個細腳伶仃、饑腸轆轆的孩子?她突然萌生起拜訪他的念頭。來了半月有余,她還沒正式拜訪過誰呢。老太太就拿了手電筒出了院子。
夜晚的村莊,和白日的村莊,氣味是不一樣的。白日的村莊是屬于動物的:屬于槽子邊的黃牛,屬于圈里的約克豬,屬于柵欄里的奴羊,屬于籬笆里的鳳頭雞,屬于墻頭的野貓,屬于麥秸垛的刺猬,屬于草叢里的春蛇……那氣味摻在灶坑里,摻在孩子的鼻涕里,摻在男人的尿液里,是重的、沖的、濃的、腥的、煙火氣的;而夜晚的村莊則屬于植物:屬于韭菜,屬于櫻桃,屬于桃花,屬于榆錢,屬于一切靜默生長著的神靈,所以那味道是甜的,是淡的,是凜的,是澈的,是悄然入心入肺的……老太太走在夜里,骨頭似乎也輕靈起來,平時十來分鐘的路,只走了七八分鐘。到了黃土崗才想起,那條斜坡太陡了,以她生銹的腿腳,白天攀爬上去已是不易,何況繁星漫天的夜晚?怏怏地在崗下站了會兒,蒲公英的甜澀又隱約著撲進鼻孔。
還好,病又隔了一夜就痊愈。上午,就接到了大兒子的電話。她沒想到兒子會給她打電話。他說話向來簡潔。他在電話里說,媽呀,你生日快到了,還記得吧?有個香港大公司的老板,做了你一輩子的戲迷,專門從香港飛過來,要給你隆重的慶祝一下,光贊助費就掏二十萬。你過幾天拾掇拾掇,趕快回省城吧。
大兒子五十多歲了。他秉承了他父親的一切:暴躁、酗酒、打老婆。他早把她盤剝的只剩一具衰老的身體。每到發工資的日子,都會帶兄弟來分錢,此后一月不見蹤影。說她手頭沒攢下錢誰信呢?去年跌了一跤,路也走不了,孩子們誰都不吭聲,也沒帶她到醫院看治,如果不是幾個戲曲學院的弟子出了手術費,她剩下的日子怕也只是癱爛在床上。如今她好不容易偷偷跑到鄉下,不成想還是被他找到。她輕聲輕語地告訴他,她是不會回去的,她喜歡這個叫麻灣的村子,她要在這里老死。
“那你就死那兒吧!永遠別回來!”兒子在電話里咆哮起來,“反正這輩子你的命比草還賤!有福也不會享!”
命比草賤……命比草賤……她的眼眶就濕了……
“老太太啊,發啥愣呢?”
她抬頭,卻是“劉三姐”推門進來。“劉三姐”手里捧著碗懶豆腐。
“我用黃菜葉跟豆腐渣熬的,聞聞,聞聞,比豬肉都香!”“劉三姐”邊說邊咂摸著嘴,“趁熱吃了吧,世界上最好吃的懶豆腐,就是我‘劉三姐’做的。”
四
那天晚上,老太太燉的清水排骨湯。喝完了湯,天方擦黑。她覺得有點熱,就脫了棉衣在院里給韭菜澆水。澆著澆著,耳畔便傳來誰家的收音機聲。有人正在唱《春閨夢》,是張氏與丈夫王恢互訴衷腸那一場。聽聲音不是王缺月就是趙恒秋。畢竟是晚輩,功夫還是有些稚嫩。聽著聽著,她不禁將水桶緩緩放下,輕聲輕語唱將起來:
去時陌上花如錦,今日樓頭柳又青。
可憐儂在深閨等,海棠開日我想到如今。
門環偶響疑投信,市語微華慮變生。
因何一去無音信,不管我家中這腸斷的人。
她恍惚又站在偌大舞臺之上,金絲絨帷幕拉開,司鼓開始打倒板頭,倒板頭打完,胡琴聲一響,滿場肅靜無嘩。一瞬間,她仿佛就成了張氏,對著夫君埋怨。雖是埋怨,卻是嬌憨的、驚喜的、委婉的、意猶未盡的。她竊笑、她頷首、她掩面、她蓮步生滅……當她最后佯裝拂袖時,她仿佛聽到戲臺下傳來驚雷般的叫好聲……
唯有墻邊傳來“咕咚”一聲悶響,她才猛然夢醒,身子打個激靈,木木地朝墻邊看去。
這一看竟忍不住笑出聲來。卻是那孩子從墻頭跌了下來。看來沒什么大礙,他慌里慌張地拍拍身上的灰塵,這才怯生生凝望著她。
“你怎么又來了?”老太太沉著臉道,“你偷吃了我的鵝,這回又想偷什么?”
“我……我……”男孩諾諾道,“我只是來瞧瞧,你的病好了沒有。那天晚上,你的頭比開水還熱……”
老太太瞇眼看他。他就支吾著說:“我剛才在墻頭聽你唱戲……一不留神掉下來了……”
老太太這才走過去,摸了摸他的頭,說:“以后不用爬墻頭了,奶奶給你開著門。”
就領男孩進屋,給他熱了排骨和米飯,盛得鼓尖才遞給他。孩子大口大口扒拉著,她就問:“你爸媽呢?”“全死了。”“怎么回事?”“病死的……”“爺爺奶奶呢?”“爺爺早死了,奶奶……奶奶……”男孩哽咽著說,“奶奶前幾天心肺病犯了……你那只鵝,我殺了做供品的……”“還有親人嗎?”“有個大伯……是個瘸子……”
男孩將碗筷放下,呆呆凝望著房梁。老太太說:“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先把排骨都吃了。”男孩快速地瞥了她一眼,又埋頭悶悶吃起來。他飯量委實很好。他總共吃了三碗米飯,排骨也啃得精光。
“以后跟誰過呢?”她仿佛問自己,又仿佛問孩子,“這么小,比火旗高不多少……”
男孩就放下碗筷,徑直往外走。老太太伸手拽他,他沒動。老太太說:“你喜歡吃糖嗎?柜子上的鐵盒里有。有大白兔的,還有金絲猴的。”
男孩說:“我從來不吃零食。”
老太太撇撇嘴說:“哪里有孩子不貪零食的?”
男孩黯然道:“我爸媽活著的時候,也沒給我買過零食。”
老太太嘆息著說:“以后奶奶給你買……”
男孩瞥她一眼,嘟著嘴轉身走了。不會兒,老太太聽到屋外關門的聲響。這次,他不是翻墻出去的。
隨后幾日,男孩都過來共進晚餐。家里好像還沒如此喧鬧過。老太太特意讓王靜生打集市買了張八仙桌。桌上通常是一涼一熱。熱的呢,是老北京菜,什么番茄腰柳啊,炸灌腸啊,砂鍋獅子頭啊,櫻桃肉啊,都是最拿手的;涼的呢,無非是蘿卜櫻子、香蔥、新韭,抑或小嫩菠菜,用海天醬油和酸醬細細拌了。兩個人,就在炕上面對面坐了吃。孩子呢,通常只悶了頭扒飯,很少動筷子夾菜。吃一陣偶然抬頭,老太太便往他碗里夾一箸菜,嘴上嘮叨著:“十來歲的小子,吃窮老子。多吃,多吃。”孩子也夾了肉丁或臘腸,猶猶豫豫著往老太太碗里塞。老太太就笑。如果兩人都不言語,屋內便只聽得牙齒咀嚼食物的聲響,不過聲響又不同:老太太是細嚼慢咽,老牛反芻般半晌才動下嘴;孩子呢,則像豬崽搶槽子般呼嚕呼嚕,眨眼間一晚米飯就下了肚。老太太說:“你慢些吃,吃得太快,胃哪能受得了呢?可要當心,年輕的時候是人找病,老了啊,就是病找人了。”孩子仍是大口大口地吞咽,仿佛沒長耳朵般。那一日,孩子忽然放下手中的碗筷,鄭重地對老太太說:
“我……我想求你個事……”
老太太故意說:“那可不行,你給我什么好處呢?”
孩子眼神就黯淡下去,老太太這才說:“好吧,我不要好處了,只要你拜我為師,學一出《紅拂夜奔》就成。”
孩子仍垂著頭,半晌才說:“我估計活不過明年了。要是我死了,你把我跟我爸媽埋一塊吧。”
這話從一個孩子的口里出來,老太太一時就找不出合適的話來應答。孩子又慢慢說道:“墳就在崗上。我喜歡吃肉,到時候你給我墳頭……放一塊豬頭肉就行了……紙錢呢,多燒些,我好給我爸媽買新衣裳……”說完了又繼續埋頭吃起來。老太太就強笑著說:“你個兔崽子,小小年歲,竟想些不著邊的事兒,就是死,我肯定也在你前頭。”
老太太面上掛著笑,心下卻不時犯愁。孩子為何要說這番話?不像是睜著眼說假話,難道是得了什么絕癥?又想,一個父母雙亡的孤兒,如何安頓為好?雖說有伯父,看來也是薄情寡義的人,不然怎會讓孩子孤身獨住?只是個十來歲的孩子啊,按常理,晚上還賴在娘被窩里暖腳的。便尋思著去找村里的干部,好歹找個人家寄養才安妥吧?實在不行送福利院,也比夜里孤零零守著土崗強,也比被孩子們整日欺負強,起碼不至于嚇破膽,只到晚上才敢出來。
那天,男孩夜間又來,老太太燉了半只蘆花雞。剛把雞大腿撕下放孩子碗里,“劉三姐”夾著團棉花就來了。“劉三姐”臉上本來堆著笑,愣眼瞅到男孩,突然一聲尖叫,嚇得男孩兀自撒腿就跑。男孩跑了,“劉三姐”還撫胸長嘆,竟是副失魂落魄樣。老太太乜斜著她,冷冷問道:“抽羊角風了嗎?”
“劉三姐”說:“我的天親啊,你咋敢讓這孩子跑你屋里頭?”
老太太說:“他又不是十惡不赦的人,我干嘛不敢讓他來?”
“劉三姐”垂頭頓足地嚷嚷道:“他可是個瘟神哪!你不知道,他爹媽出去打工,被人騙去賣血,得了艾滋病,去年全死了!艾滋病啊!你老人家可知道這是啥病?你還敢跟他一塊吃飯!不想活了你!”
老太太茫然地瞅著“劉三姐”,說:“他爹他媽有病,跟孩子有什么關系?”
“劉三姐”急赤白臉地說:“咋沒關系?!他媽懷孕的時候就得病了!這孩子生下就有艾滋病!”
老太太不再聽她絮叨,開始收拾碗筷。“劉三姐”一把將碗筷奪過,順勢扔進垃圾桶,又匆忙提了垃圾桶快步出屋。顯然,這個麻灣唯一的“女光棍”是被徹底嚇著了。當然,麻灣唯一的“女光棍”被徹底嚇著了,也就說明整個麻灣村被徹底嚇著了。
五
老太太翌日起得晚。如若不是敲門聲愈發大起來,定會再睡個回籠覺。等她將門打開,倒不禁愣住。房北圍站著七八個女人,有相識的,有不相識的,還有半生不熟的。見她邁門檻出來,都不約而同向后退了幾步。老太太用手壓了壓發髻,她們又是碎步挪騰。很顯然,她們都知道孩子的事了。看來“劉三姐”的舌頭,也并不比她們的短多少。
那個清晨,這幫子婦女圍圈住老太太,七嘴八舌問個沒完。譬如,他何時開始到她這里蹭飯的;譬如,他吃過之后的碗筷,她是否用開水燙過?譬如,他有沒有跟她討要錢物;譬如,她以后是否還會叫他來吃飯?顯然,他們最關心的還是末一個問題。
老太太目光漠然地越過她們,掃到了房前一棵梨樹。梨樹也是素白,不過卻比櫻桃多了分瑩潤。女人們仍喋喋不休,仿佛她們若不是如此這般盤問她,倒真是對她不起。她后來實在有些厭煩,就說,我筋骨有些受風,要去屋里好生靜養一番,你們還是各自忙各自的去吧!
女人們怔怔地盯了她看。她連個招呼也沒打就關門回屋。站在過頭屋里,耳邊還響動著她們嘈雜的議論聲。
待到日懸中天,老太太又去了黃土崗。空中飛著亂柳絮和蒲公英,老太太不停打著噴嚏。這樣行到崗下,又歇息片刻,這才一點一點向上爬。爬了沒幾步就腰酸腿疼,尋思尋思又徑自下坡,仰頭朝崗上望去。
男孩就站在崗上俯視著她。他只穿了那件漏眼的海魂衫,細瘦胳膊支棱著。他看她一眼,她看他一眼,誰都沒有說話。老太太“哎”了聲再去瞅他,他仍站在那兒,猶如剛從泥土里鉆出的豌豆苗。他的瞳孔與眼白,倒如晝與夜般涇渭分明。
“你下來,”老太太朝男孩擺擺手,“以后別住這兒了,搬到奶奶那兒。”
男孩猛地搖搖頭。
“別怕。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想小鬼至。我都這把年紀了,還有什么怕的?我都不怕,你還有什么怕的?”
男孩仍是搖搖頭。
“你晚上想吃什么呀?奶奶給做砂鍋白肉吧?”
男孩轉身就跑了。崗上又空曠起來。
看來,這孩子是怕連累她,沒準這是最后一次見到他了。老太太蔫頭蔫腦回了家,捂了棉被靜躺。晌午剛過,王靜生就來拜訪了。王靜生來了后并未言語,先是在炕沿上默默卷了支旱煙,咳嗽著抽完才去瞧他姨媽。他姨媽這才從被窩里鉆出來,盤腿坐在炕席上。王靜生說,關于她跟孩子的事,他聽別人說了。別人呢,也沒啥惡意。以前他跟父母住崗上,跟村人不怎么來往。去年他父母病死,剩他一個,都是她奶奶送糧送水。前些天他奶奶死了,還有個伯父。可這伯父是他奶奶的養子,打自初就跟他父親不和,又是個瘸子,看來指望不上。孩子的病不是好病,別人才不敢跟他往來,怨不得別人。老太太就別瞎摻和了,省得別人戳著脊梁骨說閑話。“姨啊,你這輩子,”王靜生頓了頓說,“聽到的閑話還少嗎?”
這倒是老太太搬到麻灣村以來,頭一次聽王靜生講這么多話。王靜生說完,又卷了支旱煙抽起來。老太太這才轉過身說:“回去吧靜生,我有分寸的。”
王靜生就趿拉著鞋走了。
那晚,老太太做好了飯菜,孩子卻沒來。老太太看著桌子上的鹵煮和油條,一口都吃不下。八仙桌就在炕上擺了一宿。半夜老太太睜開眼,盼著那飯菜已被孩子吞咽得精光,不過,油條仍硬邦邦躺在笸籮里,盛鹵煮的碗已凝了一層油。嘆息一聲,卻是怎么都睡不著了。
村長是頭午來的。這是個有點駝背的中年人,面目紅腫,穿雙皺巴巴的皮鞋,一說話嘴里就噴薄出酒氣。他先自報家門,而后一屁股坐到炕上。他說,他本來早該拜訪拜訪老太太,可他實在太忙了。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的村長了。這不是他能干,而是他必須能干:誰讓他們村地底下有鐵礦呢?這個村子不起眼,卻埋藏著大把大把的金錢。縣里讓他們年底前全部搬遷,可要讓這幫莊稼人離開住了半輩子的窩,倒真是費力不討好的事。他忙呀,比奧巴馬還忙,這才沒顧忌上那孩子。再說了,孩子有毒,人還是少接觸為好。“他的事你就別操心了,”最后村長打著哈欠說,“我跟書記會解決好他的事。如果有問題,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老太太“哦”了聲。村長似乎很滿意,又說:“你要是有啥困難,盡管跟我說!我雖然不是騎馬的駕鷹的,可畢竟還是一村之長嘛。”
老太太笑了笑。
村長前腳走,老太太后腳就出了門。她手里端著個鋁盆,盆里是五六個大饅頭。出了院門,村長赫然就堵在門外。他皺著眉頭瞥她一眼,又瞥了瞥饅頭,鐵青著臉說:“真是個老古董。你沒長耳朵嗎?嗯?拿我說話當放屁嗎?嗯?”
老太太沒吭聲,徑自朝前走。村長一愣,隨即吼道:“站住!你給我站住!”老太太仍是走自己的。村長三步并作兩步過來,一把扯住她衣襟:“你給我回去!回去!不是說了嗎?沒你的事!”
老太太站在那里,一聲都沒吭,只默然眺望著遠處的土崗。
六
兒子是第二天上午到的麻灣。
他是坐夜車來的。省城離麻灣不過一千四百里,可除了火車還要倒三次長途汽車。他腋下夾個皮包,走起路猶如身后有惡鬼追趕一般。他連問帶打聽地找到王靜生家,讓王靜生帶他去找老太太。王靜生讓他連弟喝口水,也被斷然拒絕了。看來他真是有十萬火急的事。王靜生領了他穿街過巷,到了老太太住處。鐵門四敞著,院里栽著韭菜、菠菜和蘿卜秧子,一群花腰小蜂在陽光下嗡嚶著飛。還有幾棵櫻桃樹,花期已過,葳蕤枝葉上頂著幾枚枯花蒂。他們悄悄進了屋。老太太正在炕上收拾皮箱,見了兒子,只是茫然地點了下頭,然后繼續把衣裳一件一件折疊好,再放進散發著樟腦味的箱子里。
兒子似乎就放了心,擦了擦額頭的汗水說:“哎,我真是白著急了,原來你已經準備回去了啊?”
老太太看他一眼,將皮箱拉鏈拉好。兒子埋怨道:“你的手機也不開。不開你拿它干什么呀?我昨天找了你一天,都是關機。”又瞅一眼王靜生說:“你們家也是,好歹安裝個電話啊,有個大事小情的多不方便。是不是?”王靜生就陪著笑臉點頭稱是,又說姨媽住這里的日子,自己照顧得不是很周全,還望見諒。兩人又閑聊幾句,兒子才對老太太說:“你最近還好吧?這個禮拜日就是你壽日,香港的李老板星期六就飛過來,飯店呢,就定在凱撒大酒店。畢竟是李先生面子大,省電視臺的還要全程錄像呢。快回去吧,窩在這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干嘛?”
老太太將皮箱從炕上往下拎。拎了幾次都沒拎動,王靜生趕忙伸手接過來。兒子繼續嘮叨道:“破鞋爛衣裳的還要它干嘛?給靜生老婆好了。人家伺前伺后也不容易。”王靜生連忙說,她老婆是個胖子,比母熊還肥,姨媽的衣裳肯定不合身。兒子說:“算了算了,我們快走吧。出租車司機還在村頭等著呢。我們直接打車去市里,好歹還能趕上下午的火車。”
三人就往門外走。王靜生幫老太太提著皮箱。等出了大門,老太太把皮箱從他手里接過,抽出拉桿,拍了拍他的肩,就朝土崗那廂走去。王靜生“咦”了聲,忙扭頭看他連弟。他連弟已然將他們拉開五六米,又狐疑地去看老太太,嘴里喊道:“姨媽!姨媽!走錯了!”老太太沒應答,王靜生只得又朝他連弟喊:“彥春!彥春!彥春!”
兒子這才扭頭,蹙著眉朝老太太喊:“媽!你糊涂了啊,出租車在村東呢!”見老太太不語,聲音就又挑高些。他嗓門本來就粗大,這下倒真像是用喇叭喊話了:“回來!往這邊走!回來!往這邊走!”老太太大抵聾了,只顧彎著脊背邁著碎步拉著棕色皮箱一步一步朝前走。兒子大概在王靜生跟前有點上火,他小跑著過去,一手按捺住皮箱,另一只手死死拽住她衣角,晃著她身體喊道:“媽!你傻了啊!這是去哪兒啊?!怎么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老太太這才回身默默注視著兒子。兒子虛胖的臉上全是汗水。兒子身后是王靜生,王靜生身后則是些街坊鄰居,“劉三姐”也伸著脖子縮在人群里,幾度想踏上前來,又都猶豫著退回去。他們若即若離地環在左右,仿佛是專門來看熱鬧的。老太太一把甩開兒子的手,繼續拉著皮箱西行。兒子倒也不敢再造次,只得跟在母親身后邊走邊絮叨:“人家可是給了贊助費的!不瞞你說,說是二十萬,其實給了五十萬!圖個啥?不就圖見你一面,聽你唱兩句《春閨夢》和《鎖麟囊》?人家拿你當寶,你可不能把自己當寶,傲氣值幾個錢呢?”
如果有人從土崗上俯瞰,便會看到一行人以一種奇怪的姿勢迤邐前行:最前面是位拖著皮箱、滿臉皺紋的老太太,后面是兩個神態疲憊焦慮的中年人,再后則是稀稀拉拉、端著胳膊嗑著瓜子的閑人。老太太走了好一陣才到崗下。她再次轉過身看著兒子,看了會兒,方才嘆息道:“回去吧,你。聽話啊。”兒子哭喪著嗓子喊道:“那你呢?你這是去哪兒啊?”老太太伸手擦了擦他額頭的汗,扔下皮箱徑直朝坡上走去。
這條坡不長,但是陡,爬滿了蒲公英和矢車菊。老太太曾在黃土崗下徘徊多次,卻從未真正上去過一回。她深吸了口氣,這才徐徐彎下腰身,晃晃悠悠往上爬,爬了沒幾步就有些氣喘,冷不丁一個趔趄,險些就栽滾下來。眾人在坡下不禁一陣尖叫,她聽到兒子劈著嗓子喊道:“媽!下來!快下來!這是唱的哪出戲啊?”她裝作沒有聽見,只是將腰俯得更低,胸腹幾乎就要貼上地面,手里抓住花草莖葉,身如脫水的彎狗蝦般一拱一拱朝坡上蹭。當眼前驀然出現一只瘦骨嶙峋的小手時,她不禁抬起脖子瞅了瞅。男孩就站在她上邊。他還穿著那件海魂衫,小臉大抵有幾天沒洗了,灰頭灰腦的。她就慢吞吞地說:“沒事兒,別管我!”嘴上這么說著,手還是顫顫巍巍伸過去。當孩子冰涼的小手緊攥住她榆樹皮似的掌心時,老太太身上忽就有了氣力,手腳在瞬息都熱了起來。有那么片刻,老太太確信雙腿其實就踏在棉花般潔凈干燥的云朵里,每向上微微跨一小步,就離天空和星辰更近了半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