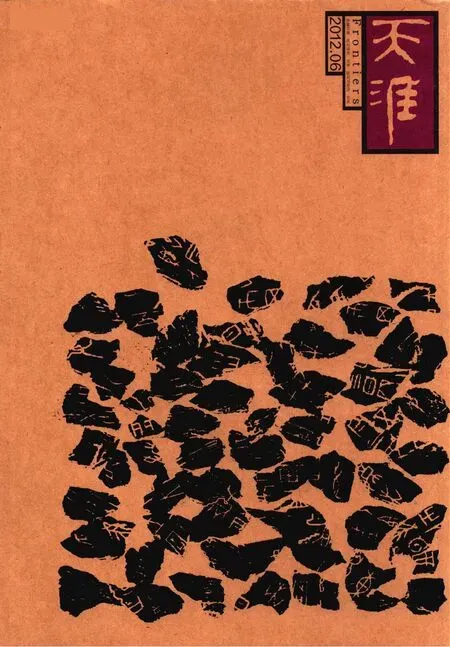民國的征地與拆遷
李開周
日本兵在中國沒干過什么好事兒,南京大屠殺是他們干的,旅順大屠殺是他們干的,這些罪惡滔天的暴行在歷史教科書上一再提起,現在已經人所共知。還有一些暴行,在教科書上很不小心地略過去了,通俗歷史著作也鮮見回顧,它們埋藏在古舊報紙以及抗戰小冊子的字里行間,埋藏在大難不死并仍然健在的某些長壽老人的回憶里,偶爾也能在民國漫畫的內頁里見到它們,就像一兩張不引人注意的帶血標本。
我說的暴行,指的是低價征地和暴力拆遷。
日軍在中國怎樣征地
1937年7月,日軍攻占北京,在今天的豐臺區造甲村(位于北京西站西南)修建機場,征用了一批土地。征地需要付給補償,當時日軍付多少補償,或者有沒有付給補償,史料上沒記載,我們只知道農民不答應(也許是出于愛國精神,也許是因為補償太低),不愿意在協議書上簽字。日軍就采取強制手段,用刺刀逼著農民簽字。最后他們得逞了,成功征地近二百畝。
我猜想,日軍用刺刀威逼農民的時候,決不只是恐嚇那么簡單,被征地一方免不了要流點兒血,說不定還死了人。不過史料上沒寫,我不敢妄言。
下面這起征地事件就真的是流血滿地了。1937年8月,日軍攻占上海,在今日上海浦東新區的黃沙村和顧家宅村修建機場,也要征用農民土地。這回日軍吸取“教訓”,干脆不給任何補償,也不跟農民談任何條件,直接殺人奪地。黃沙村縱橫七八十里,定居三四百人,不分男女老幼,被狗日的鬼子全部屠殺,無一幸免。顧家宅村倒沒遭受滅村之禍,但日軍為了殺人立威,一刀下去,把一個剛滿四歲的孤兒劈成了兩截。人都死了,自然不會再有什么釘子戶,自然不需要再給什么補償。
汪偽在廣州怎樣征地
日軍在中國征地的過程充滿了血腥,被日軍扶持起來的日偽政府也一樣血腥。
1943年2月,汪偽政府擴建廣州白云機場,在三元里一帶征收了農民土地兩百多畝。古往今來,不管是為了公益,還是為了私利,征收土地都是必須補償的,而補償的數額,至少在理論上,不能比被征土地的市場價值低。換句話說,不管政府出于什么目的征地,都不應該讓農民吃虧。汪偽政府給的補償是多少呢?每畝778元。這當中,包括土地補償金、青苗補償費、遷墳費,以及重修水利設施的補助等等。總之,所有應該補償的項目都列了進去。
每畝補償778元,不是大洋,不是毫洋,更不是人民幣,而是汪偽政府在統治區內強制發行并普遍流通的一種紙幣,名叫“中儲券”。中儲券跟法幣一樣,剛發行時還很堅挺,越到后來貶值得越快,最后拿出幾百萬元也只能買根火柴,大堆鈔票形同廢紙。在1943年2月,中儲券已經貶值,但貶值的程度還不是很厲害,當時廣州市面上,一擔“齊眉”牌大米賣到628元(中儲券,下同),一擔中級面粉賣到748元,一擔黃豆賣到1078元,一擔花生賣到3773元,一擔豬肉賣到4431元,一擔冰糖賣到1393元。
“擔”是重量單位,在民國,一擔等于80公斤。那么在1943年2月,花中儲券7.85元能買一公斤大米,花中儲券9.35元能買一公斤面粉;如果買黃豆、花生、豬肉、冰糖各一公斤,則分別需要中儲券13元、47元、55元、17元。拿這組物價跟現在的物價相比,您可以估算出當時中儲券的購買力:大概每兩元中儲券才能兌換一塊錢人民幣。汪偽政府征收三元里一帶農民土地,每畝給予補償778元,折成人民幣還不到400元,簡直就是白撿。
當然,那時候三元里還不繁華,地價還不是很高,尤其農民的土地更加便宜。但再便宜也有個價格,早在1933年,廣州還沒有淪陷的時候,這兒的一畝地就能賣到毫洋幾千元,按購買力折成人民幣,至少上萬元一畝。市價上萬,只給幾百,汪偽政府對廣州農民可算是狠到了姥姥家。
偽滿在東北怎樣征地
比起汪偽政府在廣州的廉價征地來,偽滿政府在東北的圈地運動更加可怕。
我們都知道,日本關東軍曾經攻占東北,成立偽滿洲國,扶植滿清末代皇帝溥儀做了偽滿洲國的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君主,然后他們就把整個東北變成了日本人的殖民地。殖民地當然離不了“殖民”,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日本政府陸續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日本農民和日本浪人來到東北,在白山黑水之地定居下來。定居需要建房,建房需要地皮,為了給新遷來的日本人提供地皮,關東軍授意偽滿政府在長春、沈陽、哈爾濱等城市大肆征地。
1939年4月,在鐵嶺來了個日本籍的新縣長(當時鐵嶺還是縣級行政轄區)古田傳一,這個新來的縣長親自主持征地工作。當時一個叫作新臺子村的村莊被征走845畝耕地,領到的補償連一年的口糧都不夠,村民們到政府大門口靜坐示威。古田傳一很煽情地對前來抗議的失地農民說:“收買移民地是國策!”意思是你們要愛國,要顧大局,不能光打自己的小算盤。他這種無恥論調,有點兒像后來江西宜黃某官員宣揚的“沒有強拆就沒有城市化,沒有城市化就沒有新中國”,讓人忍不住懷疑是不是那個日籍縣長又穿越時空來到了現在,或者那位官員穿越時空回到了偽滿洲國。
早在1932年10月(偽滿洲國剛剛成立半年),日本關東軍指使黑龍江阿城縣政府在阿什河沿岸征收14500坰(面積單位,一坰一般指15畝)耕地,補償標準是:已經耕種過的熟地每坰30元到70元,還沒耕種過的生地每坰只給15元。而市場價要比補償高得多,地勢平坦、區位優良的優等耕地每坰能賣200元,最差的耕地每坰也能賣130元。事實上,農民們連理論上規定的補償標準也拿不到,縣政府派出的評估員故意壓低土地等級,本來是熟地,他們給登記成生地,本來是優等地,他們給登記成劣等地,這樣農民所能領到的補償就更低了。最變態的是,補償款不是直接發到農民手里,而是讓失地農民去找一個叫作“東亞勸業會社”的企業設在哈爾濱的辦事處去領。從村里到哈爾濱,上百里的路程,當時交通不便,土匪橫行,辛辛苦苦領到的補償款很可能被土匪搶走。另外這個東亞勸業會社效率極低,失地農民背著行李在辦事處門口排起長長的隊伍,發放補償款的工作人員還在不緊不慢地閑磕牙,還刁難農民,不是說手續不夠,就是說公章不在,逼得農民來回幾十趟,為了把補償領到手,甚至要跟他們磨嘰一兩個月,來回的路費、餐費、住店費再加上誤工費用,可能比補償還要多些,與其去領錢,還不如不領。偽官僚和關東軍等的就是這個,你不領正好,給他們省了。
1934年3月,關東軍特務部在《吉林省東北部移民地收買實施綱領》中規定,征用農民耕地的補償標準最高不能超過每坰20元。同年6月,日本拓務省提出,要按“比現在普通市價顯著低廉”的標準,“在關東軍的支持下收買土地”。偽滿政府作為關東軍和日本拓務省的傀儡,征地的時候自然只給極低的補償。從常識推測,經手征地的偽滿官員還極可能貪污一部分征地款,使失地農民得到的補償更少。
補償顯著低于市價,征地的時候肯定會有阻力。現在解決阻力的辦法多種多樣,包括連坐(父母不在征地協議書上簽字,兒女可能丟掉工作)和動武(譬如雇黑社會充當打手,把釘子戶打傷打殘)。偽滿政府喜歡動武,它也不必雇黑社會當打手,有關東軍幫它殺人,如果你在征地過程中不配合,就得跟日本兵的刺刀比劃比劃。所以偽滿在東北征地,經常伴隨著流血事件,不是釘子戶被日軍滅門,就是整個村子被日軍屠殺。
末代皇帝溥儀在回憶錄里提了幾個數據:“東北農民在糧食被強征的同時,耕地也不斷地被侵占著。根據《日滿拓植條約》,日本計劃于二十年內從日本移民五百萬人到東北來,這個計劃沒有全部實現,日本就垮臺了,但是在最后兩年內移入的三十九萬人,就經過偽滿政權從東北農民手中奪去了土地三千六百五十萬公頃。”也就是說,單是在1944年和1945年兩年里,偽滿政府就強制征地3650萬公頃。而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2010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2010年全國征地總面積不到40萬公頃,偽滿一年的征地規模,相當于現代中國幾十年的征地規模。我覺得,偽滿之所以能夠如此大規模地征收土地,一是因為補償很低,不需要花多少錢;二是因為阻力很小——殺人可以減少阻力。
降低了誰的發展成本
站在汪偽政府和偽滿政府的角度來看,征地補償當然是越低越好,因為征地補償越低,建機場、搞移民以及搞房地產開發的成本就越低,花同樣的錢,能辦更多的事,套句官話講,這樣可以降低發展成本,加快發展速度。
但問題是,降低了誰的發展成本?在日本刺刀的輔助下,偽政府可以低價征地甚至無償征地,建設成本當然是下降了,貪污機會當然是增加了,甚至也降低了時間成本:只要一紙公告貼到墻上,老百姓就得主動交出土地和房子,無需談判,無需公證,無需上法庭打官司,效率高得驚人。
可那些農民,不但沒有降低成本,反而增加了成本,他們的生存成本在上升,抗爭成本也在上升。當申訴無門時,要么沖向刺刀,要么選擇自焚,要么忍下這團怒火,讓它在心底熊熊燃燒,直到某一天突然像火山一樣爆發。
常識是這樣的:一個政府,不應為了降低自身的統治成本而存在,而應為了降低國民的生存成本而存在,倘若做不到這一點,就不是一個合格的政府。
常識也是這樣的:從長遠來看,任何一起強制拆遷和低價征地都在無形中增加著統治成本,因為喪失了公平感和安全感的國民是最難統治的一群。當年汪偽政府和偽滿洲國在大陸的統治之所以都很短命,主要倒并不是因為炎黃子孫不愿充當亡國奴,而是實在忍受不了那種極端變態的剝削方式。
這些常識,跟偽政府是講不清的,擱到現在說,卻為時不晚。
孫中山的征地思想
無論是汪偽政府,還是偽滿政府,征地時都有一個共同點:付給農民的補償遠遠低于市場價。這種做法很不合理,跟孫中山先生的征地思想背道而馳。
孫中山先生在征地方面持什么思想呢?四個字可以概括:照價收買。
眾所周知,孫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義,三民主義里有一條民生主義,民生主義要求平均地權,平均地權又包含兩個要點:一、漲價歸公;二、照價收買。
譬如您炒一塊地,買的時候一千萬,現在漲到了兩千萬,您轉手賣掉,能掙一千萬,按照孫中山先生的理論,您至少得交給政府八百萬,然后政府把這八百萬投入到教育、鐵路、市政或者國防上去。換言之,土地溢價不能讓一個人獨吞,應該拿出一部分讓全民分享,這就叫“漲價歸公”。
再譬如您住著一套房,市值一百萬,現在政府搞拆遷,讓您搬出去,那么它得給您一套一模一樣的房子,或者按照一百萬或者更多(加上安置費)的標準對您進行補償。也就是說,政府在拆遷或者征用私人產業的時候,必須公平合理,必須像一個地位對等的買家,必須走市場路線,“不讓人民吃虧”(川系軍閥劉湘的名言),這就叫“照價收買”。
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講三民主義,平均地權是肯定要講到的,但是要點往往講錯,以為平均地權就是讓農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就是要搞土改。其實平均地權不光是在農村平均,也是在城里平均,不光是平均土地分配,還要平均住房供應。怎么平均?還是那兩個要點:漲價歸公,照價收買。
只要漲價歸公,用不著打擊,開發商就不會再捂地了,投機者就不會再炒房了,房價地價絕對不會上漲得那么快,快得像最近十幾年這樣,讓絕大多數購房者措手不及。而只要照價收買,用不著做思想工作,用不著搞連坐以及放火燒屋,大多數拆遷戶都會主動搬遷,根本不可能涌現那么多釘子戶,群體事件會銷聲匿跡,大規模上訪會減少九成,“維穩”和“截訪”之類有中國特色的詞兒會在不遠的將來變成古漢語。所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雖然陳舊,里面仍有符合時代需要的部分,像“漲價歸公”和“照價收買”這兩條,如果能在今天實施,對咱們老百姓應該很有利,對構建和諧社會應該很有用。
法律是法律,現實是現實
即使在民國,三民主義也沒有能夠真正貫徹下去,漲價歸公和照價收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留在紙面上的空想。
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以前,南北分裂,各自為政,來不及實施這一主張。后來北伐勝利,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當局制定《中華民國土地法》(1928年6月30日頒布),只寫了照價收買,沒提漲價歸公。再后來“土地投機風行于各大都市”(民國學者陳岳麟1936年調查報告),經濟學家呼吁征收地價稅和增價稅,除了上海和青島等少數城市響應,不見其他城市跟進。緊接著日本侵華,八年抗戰,完了又忙著打內戰,一直到1949年,漲價歸公也沒能變成現實。
再說照價收買。南京國民政府1930年修訂《土地法》,以及后來制定《土地法施行法》,還有召開“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土地征收,都要強調一回“征收土地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以及“須照價收買”這兩大原則。可是咱們看看那時候征收民地給多少補償,就知道法律上規定的只是一些空話了。
1928年,南京市拓寬中山路,在長達12公里的狹長地帶征收土地700畝。南京市政府草擬了補償標準,交給一個臨時設立的仲裁機關“土地征收審查委員會”審定。理論上說,這個土地征收審查委員會可以對市政府的征地行為進行制衡,可是該委員會只有五個人,委員長就是南京市土地局的局長,另外四名委員當中有三名是財政局長、公安局長之流,只有一名是商會代表,而且還是土地局長的親戚。像這樣的機構,完全是個擺設,市政府草擬的補償標準再低,在土地征收審查委員會那里也會全票通過。
該委員會通過了這樣的補償標準:征收土地以平方丈(60平方丈為1畝,每平方丈折合11平米多一點)為單位,按照區位的優劣,每平方丈最高補償22元(銀元,下同),最低補償6元。事實上,那時候中山路兩旁的土地每平方丈最低也賣到50元,要說這就叫照價收買,等于瞪眼說瞎話。不過南京市政府有自己的一套理由:我們的確是照價收買,只不過照的是1926年的市價,不是1928年的市價。
您知道,1926年的南京還沒有變成首都,中山路一帶人口稀少,滿目荒涼,土地價格很低。可是到了1928年,遷都工作已經完成,一年當中南京人口從30萬暴增到70萬,房價大漲,房租大漲,地價也跟著翻番,市政府按遷都前的老行情征地,簡直坑人到了極點。
當時主持征地的主管領導是南京市長,名叫劉紀文(此人是宋美齡的前男友),心狠手辣,很有“魄力”。被征地的老百姓群情激昂,去內政部訴愿(現在叫上訪),劉紀文堅持按照土地征收審查委員會通過的那套補償方案強征土地。中山路兩旁有一些臨時搭建的簡易房,有的是商鋪,有的是難民窩棚,全被劉紀文當成違章建筑給拆了,不給一分錢補償。失去土地的百姓和失去房屋的難民串聯起來,兩三萬人聚集到南京下關廣場,先是靜坐示威,然后進城游行,媒體也來助威,一些報紙把民眾抗議的新聞印成號外免費發送。劉紀文派軍警鎮壓,逮捕了幾個人。第二天,南京農協會、南京商民協會、安徽同鄉會(中山路兩旁居住的主要是安徽人)和碼頭總工會等社會團體聯合公告,宣布罷工罷市,以此抗議市政府的野蠻行為。劉紀文不得已提高了補償標準,事態才平息下來。可是拆完房子征完土地之后,南京市政府翻臉不認賬,一是減半發放,二是拖欠補償,直到1933年,才把經過七折八扣所剩無幾的補償金發放下去,而這時候中山路兩旁的土地已經漲到每平方丈300元了。劉紀文在中山路拓寬工程中低價征地,強拆房屋,派軍警毆打集會民眾,干了些壞事。但從官方角度看,他雷厲風行,不怕挨罵,其鐵腕手段使南京面貌煥然一新,是建設南京的大功臣。
南京是首都,是官方嘴里的“首善之區”,官員理應守法,政府理應愛民。《土地法》剛剛頒布下去,照價收買的紅頭文件剛剛頒布下去,堂堂市政府就采取欺詐手段和武力鎮壓的方式低價征地并無償拆遷,而且主管官員毫發無損,并沒受到懲處,法律和現實怎么就差得那么遠呢?
從保路運動到毀路運動
1936年春天,為了建設一條從成都到重慶的便捷通道,南京國民政府的鐵道部成立了“成渝鐵路工程局”,準備修筑“成渝鐵路”。修這條路,要經過簡陽、資中、內江、隆昌、永川等縣市,全長500公里,需要征用土地55000畝,其中大部分是耕地,小部分是沿線農民的宅基。成渝鐵路工程局制定的土地補償標準是這樣的:水田每畝補償20元(法幣,下同),旱田每畝補償10元,剛開墾的半荒地每畝補償5元,宅基則按區位優劣估價后補償,每畝最高不能超過30元。鑒于這時候農作物已經接近成熟,還要給農民一些青苗補償,成渝鐵路工程局制定的青苗補償標準是:煙葉和甘蔗每畝補償10元,小麥和水稻每畝補償6元。工程路線和補償標準確定以后,成渝鐵路工程局把整個工程委托給了川黔鐵路公司,要求在1939年夏天之前完工。
民國時期的農業技術并不比新中國成立后的前十年落后,農作物的產量則比大鍋飯時期還要高得多。在民國二十年代,四川的軍閥混戰已經基本結束,農民可以安心耕作,肥沃地區小麥單產能達到兩石(80公斤)左右,而西川麥價是每石5元到8元,換句話說,種一季小麥的毛利潤是10元到16元(扣除種植成本、收獲成本和各種租稅之后就很少了)。至于水稻,種植成本高,產量和售價也高,毛利潤比小麥還要可觀一些。而成渝鐵路工程局不分水田還是旱田,不分小麥還是水稻,每畝青苗只給6元,明顯不夠彌補農民的損失。
青苗補償不合理,土地補償也不合理,成渝鐵路工程局對水田按照20元一畝補償,對旱田按照10元一畝補償,而沿線耕地的市場價又是什么水平呢?截止1936年春,簡陽地價最低25元一畝,最高170元一畝;資陽地價最低12元一畝,最高200元一畝;資中地價最低40元一畝,最高70元一畝;內江地價最低40元一畝,最高84元一畝。很明顯,成渝鐵路工程局制定的土地補償標準要比市價低得多。
跟1928年拓寬中山路時低價征地的南京市政府一樣,成渝鐵路工程局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理由——它確實是按照《土地法》上規定的“照價收買”政策走的,只不過依照的不是1936年的市場價,而是1932年到1936年這五年的平均市場價。因為這五年當中大部分地區的土地價格都在陸續上漲,所以平均市場價當然要低于1936年的市場價,所以成渝鐵路工程局等于是鉆了法律的一個空子。
四川的老百姓并不像鐵道部想象的那么容易對付,他們不讓鐵路工程局鉆空子,對后者制定的補償標準搖頭說不,同時四川省政府也提出抗議,要求鐵路工程局增加補償,不然不配合征地。鐵道部妥協了,妥協的結果是:讓四川省政府成立“成渝鐵路征地委員會”,并在各縣設立征地辦事處,由四川官方而不是鐵道部的人來制定補償辦法和發放征地款,但是征地款的總額不能超過鐵道部規定的上限——200萬元。
200萬元征地款,計劃征收55000畝地,平均每畝能給36元補償,這個平均數比成渝鐵路工程局原定的最高補償標準(宅基地補償每畝最高30元)還要高,但是跟1936年的市場價比,仍顯偏低。當時四川省的一把手是軍閥劉湘(大地主劉文彩的侄子),他本著“不讓人民吃虧”的原則,又讓省政府拿出200多萬元來,作為征地的“協助款”發給失地農民。這樣一來,等于把補償提高了一倍,農民很高興。
劉湘這么做是有原因的:一、成渝鐵路倘若修成,受益最大的就是四川,多花點兒錢給老百姓,減少一些征地阻力,使鐵路早日完工,對他這個長期執政四川的軍閥來說是很劃算的;二、他執政下的四川一直處于半獨立狀態,對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一直陽奉陰違,四川其實是他劉湘的小王國,如果農民拿到的補償太低,失人心的是他,而不會是蔣介石;三、他是四川人,不想讓老鄉吃虧,所以先是逼鐵道部多出血,發現鐵道部出血不多,就自己掏腰包。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以及什么目的,劉湘把成渝鐵路沿線土地的補償標準抬高了,這對農民是好事兒。
問題是,劉湘治下的四川官場跟中國其他地方一樣腐敗,劉湘不可能親自丈量土地,不可能親手給農民發錢,鐵道部支付的200萬征地資金以及四川省政府追加的200多萬協助款,都要經過層層劃轉,從部里劃到省里,從省里劃到縣里,等劃到各縣“征地辦事處”賬上的時候,已經被各級官僚截留過。各縣征地辦事處為了地方的財政和私人的腰包著想,少不了也會想盡種種辦法貪污征地款,在被征土地的面積和等級上做手腳:本來一畝,測量成八分;本是水田,登記成旱地。這樣老百姓實際上能領到的補償就變得很少了。
失地農民拿不到應得的補償,組成請愿團去省里上訪。而上訪的效果并不明顯,就有人采取非法手段——挖毀剛剛鋪設好的路基,把枕木和鐵軌偷走賣錢。由于農民的抗議和破壞,以及抗日戰爭的爆發,成渝鐵路在民國時期始終沒有能夠修成。
早在清朝末年,四川人民曾經掀起過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抗議清政府把民辦鐵路收歸國有的強盜政策,那時候大家所保的鐵路就包括這條成渝鐵路。進入民國,由于政府征地時做得不合理,保路運動反倒變成了“毀路運動”,真是情何以堪。
也許有的朋友會認為那些毀路的農民太小氣,太自私,就為了一點兒補償款,竟然阻止和破壞鐵路建設,這是典型的不顧大局。我認同這個觀點,但我覺得最自私最不顧大局的不是農民,而是貪污征地款的官僚,歸根結底是這些貪官在破壞鐵路建設。用孔老夫子的話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他們領導天天刮著不正之風,還想呼吁草民學雷鋒,天底下有這個道理嗎?
劉湘這個一把手在征地事件中刮的風還是比較正的,但在老百姓不實際掌握選票的民國四川,沒有哪個機構和群體能幫他監督官場,他老兄一個人得長多少只眼,才能看得住底下的官員呢?在那個環境下,官員們貪污征地款是必然,不貪污才是奇跡。進而言之,低價征地是必然,照價收買才是奇跡。
全國的情形
跳出四川,放眼全國,低價征地早已是普遍現象。據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統計結果,1936年上半年全國共征收土地367宗,征地總面積1233187公畝(折合8萬多畝),經官方支付的補償款、青苗款和遷移費總計為532592元(法幣),平均一畝地才給6元,而且這只是賬面顯示的數據,沒有考慮基層官吏的截留和貪污。
同樣按照內政部的統計結果,早在1934年,全國已利用土地當中最便宜的山林地平均市價已經高達8元以上,水田和旱地的平均市價則分別是37元和21元。一般來說,被征收的土地都是區位優良、地勢平坦、交通便利的地塊,價格會比平均數還要高一些,每畝地平均只給6元補償,肯定是遠遠低于市價的。
現代中國土地公有,農村土地禁止直接入市交易,所以是不存在市價的。但政府在對農村土地進行征收以后,往往拿到一級市場上掛牌出讓,其成交價仍然可以視為是農村土地的市場價格。中國農業大學土地資源管理系的沈飛和朱道林教授曾經對全國35個地區的農地征收和土地出讓進行過調查分析,他們發現平均市場價(出讓價)是平均補償價的17倍以上,也就是說,如果政府從農民手里征收一塊地,每畝付給10萬元補償,那么轉手賣給開發商的時候,出讓價不會低于170萬元。從我個人了解的情況看,這個比例似乎還顯得過于保守,實際上,政府賣地和征地之間的差額更大,利潤更驚人。
由此可見,現代中國的土地征收跟民國時期有著的明顯相似之處,那就是都沒有做到照價收買,政府征收土地時付給農民的補償款跟同一地塊的市場價(或者出讓價)相差太遠,政府占了很大便宜,農民吃了很多虧。
昆明的拆遷
征地補償低于市價,拆遷補償也不會合理。咱們以昆明為例,看看民國時代的拆遷。
抗日戰爭爆發以后,昆明成了大后方,戰區的高校、機關以及公私企業源源不斷地遷來,昆明城中人滿為患,房價房租天天上漲。為了解決住宅短缺和市區擁堵的問題,云南省政府規劃了一個新住宅區。這個住宅區位于金碧路西段,東到老城墻,西到環城路,南到雞鳴橋,北到大觀路。規劃線以內本來住著幾百戶人家,省政府讓他們搬走,把房子拆了重建,以節約土地,以安置更多的居民。
云南省政府的政策是這樣的:宅基按市價補償,房子則按種類補償,磚瓦房每平米補償折合成法幣是0.8元;墻體為土坯、屋頂用瓦的房子,每平米補償0.4元;墻體是土坯,屋頂用茅草的房子,每平米補償0.3元。1941年,西南聯大的教師在校外租房,每平米月租平均為4.67元(法幣)。朋友們,每平米房子一個月的租金都在4元以上,政府付給業主每平米的補償竟然還不到1元,換句話說,業主房子被拆了以后,得到的拆遷補償只夠出去租幾天房子,這不開玩笑嗎?!
當然,民國拆遷補償跟現在的拆遷補償不一個概念,現在的拆遷補償包含地價補償,民國的拆遷補償只相當于建筑遷移費,地價補償是另外計算的,劃到征地一塊。但是這建筑遷移費給的也太低了,每平米幾毛錢,夠干什么用?最多夠雇人搬家具而已。再說房子能遷移嗎?只能拆掉,把碎磚爛瓦破木料運走,而這些建筑廢料是不值錢的,拆遷戶想重建家園,還必須花錢購買一批建材,另外還得雇人建造,而建材費和雇工費找誰要去?必須自己掏腰包,因為云南省政府已經給了宅基補償和建筑遷移費,所謂的拆遷補償全在里面了,領導們對老百姓已經“仁至義盡”了。
現在政府拆遷民宅,有一項基本原則:不能讓業主被拆遷之后的生活水平低于拆遷之前。還有一項更重要的原則政府沒有提,即使提了,地方官也做不到,那就是必須在被拆遷戶完全自愿或者法院判決該拆遷合法的情況下進行,絕對不能強拆。鑒于缺了一項原則,所以現代政府倡導的“文明拆遷”其實只是“半文明拆遷”。不過“半文明拆遷”也比抗戰時期云南省政府在昆明金碧路西段所進行的“不文明拆遷”要進步一些,那時候連業主的生活水平都保證不了,建筑補償給得那么少,只要一拆遷,準讓你生活水平下降。
野蠻拆遷是一項光榮傳統
古代政府搞拆遷也是如此。宋人筆記《清波雜志》記載:“蔡京罷政,賜鄰地以為西園,毀民屋數百間。”意思就是說蔡京退休以后,皇帝賜給他一片宅基,讓他修建花園,他嫌宅基不夠,又拆遷了幾百間民房。蔡京拆遷民房有沒有給人補償呢?也許有,不過史書上說:“西園人民起離,淚下如雨。”可見即使給了補償,那補償也很低,要不然待遷戶決不會“淚下如雨”。所以蔡京拆遷是強迫性的,不是出于待遷戶自愿。
皇帝親自主持的拆遷也未必能做到合理補償,拙著《千年樓市:穿越時空去古代置業》敘述過宋太宗趙光義的一項“仁政”:他幾次想擴建宮城,一見圖紙就憋住了,說“內城偏隘,誠合開展,拆動居人,朕又不忍”。意思是說他很仁愛,盡管內城很小,早該擴建了,他卻一直不擴建,因為他不忍心看著老百姓搬家。其實假如補償足夠多,拆遷戶高興還來不及呢,也犯不著讓他“不忍”。
在專制時代的統治者看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征你一塊地,拆你幾套房子,那叫“恩典”,再說了,地是你們小民的嗎?那是“王”的,連你們小民都屬于“王”,你不讓“王”征,你就有不臣之心,什么低價征地,什么野蠻拆遷,都是不臣之言。
民國算不算專制時代?我覺得算,因為民國的參議會和國民大會往往淪為執政者的應聲蟲,至少得算半專制時代。半專制時代的征地和拆遷,自然也要繼承專制時代的“光榮傳統”。
國民黨縱火燒屋
雍正年間,廣東省某府某縣,有一戶姓梁的人家跟一戶姓凌的人家比鄰而居。梁家人少,院子大;凌家人多,院子小。凌家人跟梁家人商量:你們能不能搬走,把宅基騰給我們蓋房啊?梁家人當即拒絕。凌家人說:又不讓你們白搬,我們給錢。梁家人搖頭:這院子是我們祖祖輩輩一直住的,給多少錢也不搬。凌家人惱了:你們不搬,有辦法讓你們搬!
雍正九年農歷九月初三深夜,梁家人睡得正沉,一把火從前院燒起來了,等到家人被大梁噼噼啪啪的燃燒聲驚醒時,大火已經躥到了房頂上。四鄰和地保拎著水桶來救也無濟于事,梁家八口人沒一個能夠逃生,全被活活燒死。
誰放的火呢?凌家。原來凌家人一貫作惡,在鄉里霸道慣了,見梁家不愿搬遷,就想放把火嚇唬嚇唬,把梁家人嚇走。哪知這把火放得猛了,燒死了人家滿門。案子告破之后,凌家自然逃不脫法律的懲罰,該殺的殺,該關的關了。
以今人的眼光看,滅門的凌家就像是開發商,遭滅門的梁家就像是釘子戶,開發商要釘子戶搬走,釘子戶不搬,開發商就去釘子戶家里放把火,這種事兒并不新鮮。只是凌家人沒經驗,本來想把人嚇走,結果卻滅人滿門。我覺得他們應該向現在的開發商學習,放火逼遷的時候帶上幾只滅火器,適當控制一下火勢,別把人燒死,至少別一下子燒死那么多。像幾年前上海那宗轟動全國的放火逼遷案,就只燒死了兩個人,顯得相當“人性化”。
不過凌家人也許會反駁:光放火不死人,還能把人嚇走嗎?
這個擔心是有必要的。遙想當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對平涼路、榆林路、昆明路、西湖路、舟山路、龍江路等地段的貧民窟開展大規模拆遷,遭到釘子戶抵制,工部局派人到昆明路貧民窟放火逼遷,試圖殺只小雞給猴看,哪知火苗子剛起來就被撲滅了,釘子戶登高一呼,窮苦人應者云集,兩千多人把放火者圍了起來。工部局加派人手前去爭援,隨即遇到更大的麻煩,公共租界貧民窟的住戶幾乎都走出家門上街抗議。次日《申報》登載了這一事件,說婦女用馬桶壘成圍墻,小孩扛著掃帚,男人拿著鐵鎬,成功保住了自家僅有的草棚、木屋、鉛皮房……試問公共租界的拆遷工作為什么不能順利進行?從拆遷方的角度看,一是釘子戶太多了,二是主持拆遷的人還不夠狠,放的火太小。不過工部局只在小小的租界里說了算,它不敢真的放火燒死很多人,不然很容易陷入國際輿論和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只有國民黨政府敢于放大火。由于貧民窟“妨礙公共衛生”、“妨礙公共安全”、“窩藏盜賊歹徒”,國民黨市政當局要把上海閘北區長安路一帶的貧民窟全部拆除,在警告多次而釘子戶仍不搬遷的情況下,1928年3月7號夜里,公然命警察縱火燒屋,燒毀草棚一千多間,死傷居民幾十人,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領導們順順當當把那兒的貧民窟給拆了。
您知道,敢于燒死釘子戶的猛火并不是誰都能放的,剛才說的雍正年間凌家那樣的個體拆遷者放了肯定倒霉,后臺不硬的開發商放了也會倒霉,有資格放這種火并且放過之后好像什么事兒也沒有發生的,只有武器在手勇于鎮壓不怕民變也不懼輿論的官僚,或者有官僚做后盾的特權開發商。
租界當局也很無恥
話說民國有個鄭伯昭,是孫中山先生的老鄉,靠給英美兩國的煙草公司做推銷起家,后來自己成立公司,自己開設煙廠,迅速攢下億萬資產。發財之后,鄭伯昭開始多元化經營,既做煙草生意,又從事房地產開發。這種經營之道在舊上海商界毫不稀奇,早在滿清時期,天地會反清復明,占領上海華界,建立“大明國”,把上海富人嚇得逃進租界,使得租界的房地產市場在一夜之間火了起來,當時就有大批鴉片販子做起開發商。商人嘛,圖的就是賺錢,只要房產開發的利潤超過煙草和鴉片的利潤,傻子才不干房地產。
鄭伯昭把賣煙賺的錢投在上海公共租界附近的四川北路,開發了一個名叫“宜樂里”的小區,然后就把房子租了出去。蓋了房子只租不賣,這也是民國開發商的一大特色。且說鄭伯昭收了一段時間房租,發覺自己的開發方式不太科學——房子都蓋成了石庫門樣式,每幢都是兩三層樓帶小院子,臨街還沒有開發商鋪,跟高層公寓比起來,太浪費地皮了。所以他想把房客攆出去,拆了重建,臨街部分則用高價賣給迫切需要擴展地盤的公共租界工部局。
在宜樂里租房的房客大多簽了長期合同,租期沒到,房東就攆人,屬于毀約,得給大伙一些安置費或者搬家費,多交的租金也得退給人家。鄭伯昭是鐵公雞,不給房客補償,也不退租金。房客當然不同意,拒絕撤離,兩下里就擰上了。房客們人多,鄭伯昭錢多,他買通駐軍在上海的軍閥何豐林,又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行賄,領了拆遷許可證,帶人去宜樂里拆房。房客集體阻攔,跟拆房的工人打了起來,租界當局趁機派出巡捕,荷槍實彈驅趕房客。房客再次反抗,巡捕悍然開槍,結果一個房客被打穿了腦袋,另一個房客被打成殘廢,其余房客被迫搬走。
在這次強拆事件中,租界當局表現得很無恥。無恥之一,宜樂里位于華界,輪不到工部局管,它卻越權派出巡捕。無恥之二,為了逼房客搬遷,竟然開槍殺人,完全不顧人性和法律。無恥之三,殺人之后又動用宣傳機器《字林西報》誣蔑釘子戶,說他們的反抗舉動是“暴動”,是被“無知煽惑者之不負責任的宣傳運動所造成”。最最無恥的是,堂堂工部局還采用黑社會手段,派四五個人把“宜樂里房客聯合會”的會長、滬北公學的校長馮明權騙出校門,然后綁架到巡捕房,然后又在報紙上造謠,說該會長其實是個詐騙犯,大家不要上他的當。
本來租界當局是以文明和民主自居的,它也暴力逼遷,也造謠誣蔑,也用黑社會手段,說明無恥是不分種族和國籍的。我有個不一定正確的結論:只要法律不能真正實施,人權不被真正重視,任何地區的任何機構都敢于無恥起來。
拆到了死人頭上
上海的拆遷如火如荼,天津的拆遷也在“有序進行”。
早先沒有租界的時候,天津是很冷清的,一進入民國,前清遺老到天津置業,下野軍閥去天津避難,很多老外像德國人、法國人、日本人也蜂擁而至,天津迅速繁榮起來,地價也跟著迅速飆升。從光緒十二年到民國十五年,短短四十年間,天津的地價竟然上漲了幾百倍。
地價飆升,房價自然也飆升,咱們中國的購房者又總是買漲不買跌,價格越高,房地產越火暴。民國十五年前后,天津城內原有的空地上都蓋滿了樓房,過去的平房也很快地被拆掉重建。前清遺老和一些實業派人士眼見有利可圖,紛紛涉足房地產開發,一時間建筑材料供不應求,自建房的家庭想買磚,必須提前一年預約才能買到。
天津城內和近郊的空地開發得差不多了,有些開發商又打起了義地的主意。所謂“義地”,就是具有慈善性質的公共墓地,里面埋葬的都是些無人認領的死尸。
按照常理,你開發義地,得把墳墓挖開,把棺材抬出來,運到遠郊去安葬,用現在的話說,這叫“異地安置”。可是為了節省成本和加快進度,開發商直接就把墳頭平掉,瞧見哪座棺材出露地面,就抬出來劈開,把死尸燒了,棺材當柴禾賣。當時《民風報》刊登記者評論,有這么幾句很有意思的話:“義地變賣,舊棺遷徙,經理其事者傷天害理,將未盡腐爛之尸截開,……碎棺賣做柴,住戶購柴時須仔細辨認。”
記者罵拆遷者“傷天害理”,其實有點兒過了,因為人家拆遷的不是活人,活人有欲望,會反抗,很容易跟拆遷者產生沖突,個別情緒激動的家伙還會鬧自焚,會給領導和打手們造成很大壓力。而拆遷墳地則不然,不用宣傳,不用勸導,不用斷水斷電斷交通,不用雇黑社會上門毆打,甚至連補償款都不用付,被拆遷者根本沒意見,完全配合工作,這期間沒有釘子戶,沒有上訪,拆遷工作有序進行,眾多死者情緒穩定。
并不是所有的釘子戶都吃虧
死人做不了釘子戶,活人可以做。前面的敘述里,釘子戶都是由于征地補償或者拆遷補償不合理而逼上梁山,但也有些釘子戶是在非法取利。
抗戰初期,國民黨政府為了戰備需要,修筑敘昆鐵路和滇緬鐵路,昆明火車站附近的地皮本來分屬很多農民所有,忽然被幾個有后臺的投機者(包括官員)高價購買。等到政府征收的時候,這些投機者搖身一變成了釘子戶,拒不簽字,直到他們把自己購買的地皮“變成”千金難買的優質地塊,拿到遠遠超過市價的超額補償為止。1937年11月,云南省政府在昆明聚奎樓以西開辟商業區,消息還沒傳出,“內部人士”已經獲悉,“一般權貴者即大量收買,迨省政府征收建筑之時,遂數倍買價而沽。”(聶聞鐸《川滇鐵路宣昆段地價及土地征收之研究》)賺了個盆滿缽滿。
也就是說,同樣的地塊和房屋,因為業主身份的不同,所得的征地補償和拆遷補償有可能天差地遠。如果業主只是無權無勢也沒有談判能力的平頭百姓,官方就可以蠻不講理一下,用低于市價的補償獲取優質的地皮;如果業主是官僚或者官僚的親戚,那就得老老實實的“照價收買”,甚至還可能給出比市價高得多的補償(反正都是“公家”的錢)。當然也有這種情況:平頭百姓團結起來跟官府對抗,不爭取到高額補償決不罷休,但是這樣做的風險畢竟太大,碰上“有魄力”的官員,搞不好會雞飛蛋打,像1928年3月上海閘北貧民窟拆遷事件中的釘子戶那樣,被警察縱火燒個干凈。
現代中國的政策是“同命不同價”:同樣是撞死一個人,賠償有天壤之別,撞死外國人要比撞死中國人賠得多,撞死城里人要比撞死農村人賠得多。民國時代的政策大約是“同拆不同價”,同樣是拆遷一幢房子,因為業主身份的不同,所付的補償也有很大區別,要么低得不合理,要么高得不合理。而無論是哪種不合理,對官員自身的利益都有益無損(低補償能給政府省錢,高補償能讓自己或者自己的親戚多賺錢),吃虧的永遠是老百姓(低補償使被拆遷一方財產縮水,高補償則最終由用地單位或者購房者買單)。所以補償太低固然不對,太高了也于人民不利,理想的狀態還是“照價收買”。這話說說容易,實現起來太難,因為人民沒辦法監督權力,我偏不照價收買,你能奈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