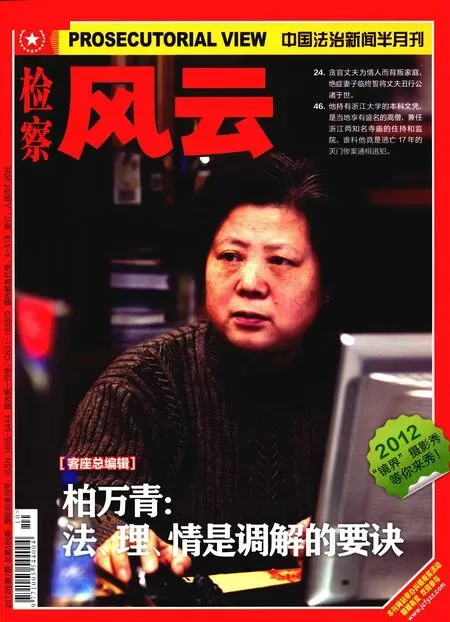刑訴法修改:權力與權利博弈
文/南方
刑訴法修改:權力與權利博弈
文/南方
刑訴法的規定關乎公權力配置與私權利保障,因此關注刑訴法修改,就是關注公民自身。事實證明確實如此。2011年9月,刑訴法修正案草案向全社會征求意見,引發了社會大討論。除了網站的意見外,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法律界寄送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的意見也很多。一個月后,全國人大法律草案征求意見系統共征集到7.8萬條建議,反響強烈。
法律因時而立,因時而改。在這15年間,發生了一些引起廣泛關注的案件,暴露出刑訴法存在的問題,如云南杜培武案、河南趙作海案、湖北佘祥林案。雖然只是個案,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存有缺陷,有必要進一步予以完善。這些案件的出現最終推動了刑訴法的再次修改,在懲治犯罪的同時,關注人權保障,是國家人權事業在刑事司法中的巨大進步,意義重大深遠。在這一總基調下,很多具體制度設計價值凸顯了出來,比如刑事訴訟法第一次把非法證據排除寫入草案。當這些作為一項制度固定下來以后,則要求有一系列的程序加以保障,所以這次在刑事訴訟法中對非法證據排除,既強調了公檢法各機關的義務,同時也專門規定了在審判階段具體的程序。而不僅僅滿足于一句口號,或者一個原則性的規定。毫無疑問,司法改革的成果需要通過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本次修法在強化司法機關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非法證據的排除、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的封存、刑事和解制度等很多方面,正體現了近年來這些成果。
刑訴法修訂,它的立法博弈主要應在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展開。刑事訴訟法首先應是一部配置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法。但長期以來,我們的立法工作存在一些不足,公民參與立法的熱情有待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這次修法體現了民眾對于立法的建議權,以及立法機關對于民意的重視。去年刑訴法公開征集意見時,曾有條文引起廣泛爭議。比如,“無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等情形,完全可能成為適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導致偵查機關可以隨心所欲決定是否通知家屬,變成“秘密拘捕”。這次提交三審的修正案草案刪去了逮捕后有礙偵查不通知家屬的例外情形,明確規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逮捕或者執行監視居住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家屬。同時,將拘留后因有礙偵查不通知家屬的情形,僅限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
正確處理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是刑事訴訟領域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既要及時準確地打擊犯罪,不放縱犯罪分子,又要切實尊重保障人權,不冤枉一個好人。無疑,我們正在朝這個方向切實邁進。
新聞背景
刑事訴訟法與賦予和規制刑事訴訟中的公權權力、追訴犯罪、保障公民權利密切相關,素有“小憲法”之稱。刑訴法1979年制定,時隔32年,2011年第二次大修正式啟動,并于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