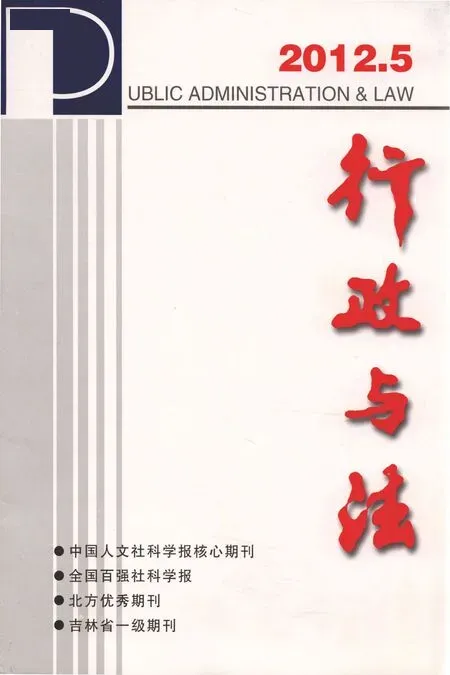合理政府規模理念及其對我國行政組織改革的啟示
□ 童秀梅,楊發坤
(⒈重慶師范大學,重慶 400030;⒉復旦大學,上海 200433)
合理政府規模理念及其對我國行政組織改革的啟示
□ 童秀梅1,楊發坤2
(⒈重慶師范大學,重慶 400030;⒉復旦大學,上海 200433)
政府規模的合理選擇不能簡單地以 “大政府”、 “小政府”來定位,而應根據不同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狀況,以提高政府能力的有效性,滿足廣大公眾的需求為標準來確定。我國政府組織改革應突破 “小政府、大社會”理念框架的限制,以合理政府規模理念為基礎,尋求一種適合我國國情、符合我國市場經濟運行以及社會發展的、適度規模的合理、高效政府。
合理政府規模; “小政府、大社會”;行政組織改革
“政府對一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這種發展能否持續下去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追求集體目標上,政府對變革的影響、推動和調節方面的潛力是無可比擬的”。[1]政府作為人類社會的最大政治組織,其規模與一個國家的行政效率、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密切相關。選擇何種政府規模理念作為行政組織改革的理論指導,是政治學和行政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一個國家的政府規模究竟應當控制在什么樣的水平,如何確定其適度規模,一直是各國學界共同關注的問題,并對此進行著長期不懈的探討,但始終沒有定論。一方面,由于各國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不同,政府職能也不盡相同,因此政府的規模也不同;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一個國家內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展階段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對政府的規模也有不同的要求。政府規模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呈現出動態性和發展性,并且不是一個簡單的“大政府”或“小政府”的選擇問題。
一、政府規模的界定及內容
作為國家表現形式的政府,是從社會中產生并代表全社會的機關,是國家進行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的工具。廣義的政府是指行使國家權力的所有機關,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機關;狹義的政府是指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即國家行政機關。本文將從廣義政府的角度分析政府規模。政府規模是指一切國家機關的構成規模,既指政府職能與權力范圍,又指政府機構與人員多少。它包括內在規模與外在規模兩個方面:內在規模表現為政府職能規模和權力規模,外在規模表現為政府機構和人員規模。[2]
內在規模表現為政府職能和權力的范圍、結構,即職能規模和權力規模。政府職能是指政府在一定時期內對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所承擔的職責和所負有的功能,它是國家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政治職能、經濟職能、文化職能和社會職能四項基本職能。政府職能規模的大小取決于政府對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范圍、數量及這些事務的復雜程度,表現為政府四項基本職能的數量、復雜程度以及結構上的集中或分散。行政權力是國家公共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立法機關授予行政機關行使的管理國家政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權力,是實現行政職能的依托。政府權力規模指行政權力在整個公共權力體系中所占的比例和份量,從理論上講,它的大小取決于國家政治體制對公共權力在行政體系中的配置。
政府外在規模一般從三個方面考察,包括政府機構設置、人員配備的數量以及行政經費支配與消耗的數量,即行政機構規模、行政人員規模、行政費用規模。行政機構規模是指政府為實現國家政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而設置的各類政府機構的數量和結構,縱向表現為在全國范圍內,從最高層到最基層的層級數量和機構內部的上下層次;橫向表現為一級政府的管理幅度和設置的工作部門的數量。行政人員規模指政府機構內工作人員的總數,它是政府規模的重要內容,主要從崗位數、領導職數、行政人員總數三個方面去衡量。行政費用規模表示政府為實現行政職能所占有和耗費的經費數量,其直接反映行政成本和行政效率的高低,通常以政府財政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特別是行政費用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來衡量。
在對政府規模的研究中,通常使用三個基本數量指標:一是政府支出和消費占GDP的比重;二是行政機構數量;三是政府公務人員與總人口或就業人數之比。政府支出和消費占GDP比重是分析政府規模中經常使用的基本指標,一般情況下公共消費占GDP比例越高,政府規模就越大。政府機構數量也是判斷一個政府規模大小的常用標準,機構規模包括橫向管理幅度和縱向層級厚度兩種結構型規模。政府橫向管理幅度越寬,所屬政府個數、工作部門數量及其內設機構相對較多,則政府規模越大。而政府縱向層級越多,上下機構的設置多,則政府規模也越大。政府公務人員數量與政府規模呈明顯的正相關性,人數越多,政府規模從量上看就越大,反之則越小。[3]
二、政府規模的幾種類型
有關政府規模的爭論,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西方傳統政府規模理論的分析是建立在 “政府—市場”二元格局基礎上的。因此,傳統政府規模理論對政府規模的探討通常是以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為核心與標準對政府規模進行的論述,認為正確界定了二者的關系,也就界定了政府規模。
(一)守夜型政府——小政府論
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守夜型政府——小政府理論的核心是政府不干預經濟。20世紀30年代之前,西方處于完全自由市場經濟階段,市場的規模狹小而分散,市場的完全競爭狀態能有效地配置各種社會資源,并引導微觀經濟主體朝著有利于社會的方向發展,這樣,政府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因此,政府采取一種消極放任的態度,盡量避免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其核心主張是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其主要職責是扮演“守夜人”角色,讓市場處于一種完全自由競爭的狀態。這一理論反映到政府規模定位上就是“守夜型”政府論。此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在其古典經濟學中,他認為,市場是調節經濟活動的最佳方式,只要給予經濟活動完全的自由,經濟活動就會由一只“看不見的手”來自動調節和支配,促進社會財富的增加。政府職能的基本價值標準就在于成為一個好的“守夜人”,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斯密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支配了歐美國家100多年,直至20世紀30年代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為止。西方古典自由主義則更是強調“功能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這種理論的特點是過分貶低政府的作用、夸大市場機制的功能。
(二)干預型政府——大政府論
大政府理論強調政府對社會經濟生活和公民事務的全面干預與管理。20世紀30至70年代,市場這個無形的指揮棒已無法有效調整社會經濟生活的諸多矛盾與問題,市場機制本身的局限性由此暴露出來,市場失靈開始顯現,人們不再相信市場的力量,轉而投向政府。“凱恩斯主義”在這個背景下應運而生,此時干預型政府理論作為一種新的政府規模理論登上歷史的舞臺。干預型政府理論認為,政府是一種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在社會中占有主導地位,應充分發揮其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干預作用。此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凱恩斯。凱恩斯提出要全面增強國家的作用,通過有意識的國家財政政策、稅收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指導社會消費傾向,提高社會的有效需求和社會總就業水平,實現國家對公共經濟活動的宏觀指導并推動其健康發展。在這段時期,干預型政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把西方各國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因此也得到了西方各國的普遍認同。但是,過分強調政府的作用,無限擴大政府規模和權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官僚機構的龐大和低效以及社會成本的不斷增加。
(三)協調型政府——合理政府論
合理政府論就是要在政府和市場之間找到一個新的合適的度,既能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也能全面有效地發揮政府的職能。20世紀70年代,在石油危機的沖擊下,長期執行國家干預政策的西方國家陷入了“滯脹”,西方國家出現了“政府失靈”的現象,如無法解釋的高通貨、高失業并存的所謂的“滯脹”問題等,凱恩斯主義陷入兩難選擇,因此出現了所謂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艾哈德是德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并不贊成完全不受約束的“自由放任”,同時也部分否定凱恩斯主義的全面干預思想,力圖在自由放任與政府干預之間尋求“第三條道路”。在他看來,政府應創造條件使市場和價格制度發揮最大功能,而對于市場機制的不足,則積極贊同政府干預。20世紀80年代以后,發展經濟學借鑒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和分析方法,形成了新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對政府與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有了更成熟的認識,糾正了只強調政府力量或市場力量作用的片面性,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對兩者有正確的定位和合理的搭配。政府不再干預微觀的經濟活動,而應發揮宏觀調控、緩解經濟波動的作用;在微觀經濟領域里則應充分發揮市場的功能,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尋求新的互補與組合。
三、合理政府規模的理性分析
政府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組織,是公眾利益和公共權力的代表,無論是從自身發展的軌跡還是從社會發展的要素來看,政府規模都是在不斷增長的。因此,合理政府規模的選擇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如果政府規模太小,則不能履行其應當承擔的政府職能,而社會公眾的要求和期望得不到滿足,就會讓公眾對政府失去信任;反之,如果政府規模過大,造成公共支出的增長,加重了社會負擔,也會造成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4]因此,如何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尋找平衡點就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即如何在政府和市場之間找到一個新的合適的度。經濟學上的市場經濟論不僅對適度規模的政府進行了價值和理性的論證,還提供了技術合理性的保證,這也為我國政府規模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式。
正如企業存在著規模經濟問題一樣,政府也存在著內在經濟和不經濟而導致的規模經濟問題。政府內在經濟是指政府在規模擴大時由自身內部所引起的成本降低,收益增加。如當原有政府規模太小,必需的政府職能不能履行或履行不好,導致無效率或低效率時,通過人力、資金等資本投入的增加,組織機構的完善,內容分工的合理,能夠相對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但是,政府規模不是越大越好,和企業一樣,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政府職能過多,組織機構龐大,人滿為患,就會導致政府內在不經濟,使政府自身成本上升,收益下降。其主要表現在政府規模擴大后:第一,有可能造成內部管理不善,政府行政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第二,政府內部組織機構增加,使政府內部管理費用增加,從而使成本上升;第三,人員增加,使人際關系變得復雜,協調難度加大,很可能會產生派系爭斗,這些均會導致內耗,降低效率;第四,管理層級增多,使信息傳遞、反饋的速度和質量受影響,從而影響政府行政管理的有效性。當政府規模變動時,內在經濟和內在不經濟是同時發生的,如果內在經濟大于內在不經濟,則表現為規模經濟。這時擴大政府規模仍可使平均成本降低,有利于政府提高效率。反之,則表現為規模不經濟,這時擴大規模,只會導致平均成本上升,有損政府效率。因此,我們既要充分利用政府規模經濟的益處,又要抑制規模不經濟因素的滋生,力求讓政府規模收益遞增,使政府規模的擴張保持在使平均成本達到最低點的程度。
我們可以借鑒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來思考合理政府規模。這里對科斯理論略作調整,將其中的企業看作政府,市場交易看作政府職能社會化,諸如許多公共部門提供的服務就可交給市場或第三部門。那么科斯理論可表述為,政府“內化”市場交易雖能節約行政成本,但隨著政府規模的擴張,政府的管理費用會越來越高,因而政府規模不能無限擴張。政府的合理規模取決于市場交易費用與政府行政成本的比例關系,當政府規模擴張到政府再“內化”一項新政府職能所引起的管理成本等于由市場來履行該項職能的費用,即邊際政府成本交易=邊際市場交易成本時,均衡就實現了,此時的資源配置達到最優。這時政府規模就是適度的,也是合理的。當然,政府在確定適度規模時,除考慮成本、效率等經濟因素外,還要綜合考慮政治、社會以及政府行政特點等諸多因素以達到最優規模。
綜上所述,關于政府規模的合理選擇,不能簡單地以“大政府”、“小政府”來定位,而應根據不同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狀況,以提高政府能力的有效性,滿足廣大公眾的需求為標準來確定。政府規模要在與行政環境的良性互動中不斷進行動態調整,趨向動態的平衡。因此,重新界定政府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克服政府規模的無限增長,有必要對我國現有的政府規模進行理性思考。
四、合理政府規模理念對我國行政組織改革的啟示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規模進行了多次改革和調整,如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的政府機構改革以及后來的轉變政府職能,從整體上看,這些機構改革最基本的表現形式是調整機構和精簡人員,目的就在于抑制政府機構規模的過快膨脹,但是結果卻總是不盡人意。政府規模日益膨脹的負面效應也是顯而易見的,如財政赤字、行政權力腐敗、政府機構臃腫、行政效率低下等等。透過歷次機構改革中關于如何限制政府規模這一問題而做出的一系列制度設計和安排,可以看出“小政府、大社會”理念如今已經成為支持我國行政組織改革的主流理念。“小政府”理論所要表達的僅僅是一種對過度膨脹的政府規模理念的抵抗,現實中的“小政府”未必是能夠有效滿足不斷增長的社會需要的政府。正是這種理念誤區使得我們在如何選擇適度的政府規模這一問題上出現了偏差,由此而做出的制度設計和安排也未能有效化解政府規模膨脹問題,這乃是我國政府機構改革屢次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惡性循環的一個基本原因。[5]
我國現有的政府規模實際情況不是政府總規模太大,而是政府職能分布不合理,我國政府規模標準如何確定,也不是一個“大政府”、“小政府”的簡單選擇問題,而是一種結構性不合理問題。這種結構性的不合理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公務人員的分布結構不合理:一是公務人員部門分布不合理,很大一部分人員仍分布在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政府部門中;二是公務人員層次分布不合理,地方政府人員比例過大,中央政府人員比例過小,造成無法滿足社會宏觀調控的需要;三是公務人員部門內部分布不合理,后勤服務人員比例過大,決策執行人員過少。第二,政府支出結構不合理:一是建設性投資數量有限,使用效率低,表現為重復建設和無效投資;二是消費性支出的效率低下,表現為行政管理機構的膨脹和公款消費等控制不力,導致行政管理費急劇增長。據有關數據顯示,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我國財政收入實現了大幅增長,而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卻增長了87倍,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在2003年就已上升到19.03%,近年來它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更高。行政管理費的過快增長占用了有限的財政資金,影響了其他事業的發展。
合理政府規模理念告訴我們,政府規模一方面不能過大,另一方面又不能太小,而是要合理適度。合理適度的政府規模應當以政府與市場的結合度、政府對資源的支配度、政府支出的約束度、公共產品的供給度、社會公眾的滿足度等標準作為評價政府規模是否合理適度的科學依據。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考慮:
首先,轉變政府行政理念,建設服務型政府。政府行政理念是政府行政的價值觀念及趨向,決定并影響著政府內部的機構設置,如公務人員匹配的標準、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據、職能范圍的邊界等。控制政府規模,構建合理適度政府,關鍵是要真正轉變政府行政理念,因為,因為有什么樣的政府理念就會有什么樣的政府行為。政府行政理念先后經歷了統治型政府行政理念、管制型行政理念和服務型政府行政理念的過程。服務型政府理念,就是堅持以公民為本位、以社會為本位、以服務為本位,擴大社會自治范圍,注重政府自身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的提高,為各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和平等條件。
其次,規范政府權力,明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數量限度及質量要求。政府掌握的公共權力賦予了政府可以實現自我規模的不斷擴張的權利,因此,要從源頭上防止政府規模擴張,就必須對政府的權力進行規范。對權力的規范,就要對權力內容進行合理的規定;就要保證權力行使公平適當,將政府權力限定在一個有理、有限的法定范圍之內。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包括公共服務)是政府最重要的職能,必須界定公共物品及其范圍,并制定公共產品最有效供給的標準,在更大程度上、更大范圍內滿足社會公眾的需要。只有明確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數量限度及質量要求,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服務質量才會提高,社會公眾監督政府工作才有依據和標準。
再次,優化政府職能結構,科學界定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優化政府職能,合理設置政府結構,核定政府人員編制,是建設合理適度政府規模的重要路徑。我國以往的政府機構改革都多次提到政府職能的轉變問題,但效果都不能令人滿意。從國內外行政改革的實踐來看,在限制政府規模這個問題上,它們共有一條基本的經驗就是轉變政府職能,因為只有職能轉變了,政府才能夠放棄那些不應該管的事務,縮減相應的機構和人員,其規模才能夠得到有效控制。我們的政府機構改革之所以屢次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力度不夠。在沒有徹底轉變政府職能的情況下,那些被裁減掉的機構、部門和工作人員的數量很快就會得到恢復,政府規模還要膨脹。同時,要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大力培植和扶持第三部門,完善社會自治組織結構,充分發揮第三部門在處理社會公共事務中的作用,建立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關系。
最后,規范政府財政支出,注重政府成本管理。政府的財政支出是衡量政府規模的重要指標,支出規模的擴大反映了政府規模的擴大。我國目前存在著行政成本過高、政府支出不合理的現象,所以,要通過學習完善政府預算制度,主動壓縮政府成本,減少政府不必要的開支來限制政府規模的擴張,使政府支出規模控制在經濟適度的范圍之內。政府要注重成本管理,按照政府成本適度、績效最高原則,合理確定政府各種成本;通過公開、透明的政府采購制度、財政支出制度降低行政成本;優化支出結構,提高政府資金使用效益,科學劃分政府投資與轉移支付的比例。
[1]世界銀行.變革世界中的政府[R].1997年度報告.
[2]盧向國.關于政府規模適度化的理性思考[J].學習論壇,2001,(10):17.
[3]張雅林.適度政府規模與我國行政機構改革選擇[J].改革論壇,2001,(03):100.
[4]張康之.限制政府規模的理論[J].人文雜志,2001,(03).
[5]史記.政府規模理念與我國政府機構改革[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1,(03).
(責任編輯:牟春野)
Concept of Reasonable Government Scale and Enlightenment on China's Administration Reform
Tong Xiumei,Yang Fakun
Government scale can not be simply to “big size government”,“small size government” to locate,bu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ocial,economic,political developmen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overnment's ability,satisfy the public demand for the criteria to determine.Our country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reform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small size government,big size society"concept frame to limit,to the reasonable government scale concept as the basis,to seek a kind of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accord with our country market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appropriate scale of reasonable,efficient government.
reasonable government scale;“small size government,big size society”;administrative reform
D631.13
A
1007-8207(2012)05-0009-04
2012-03-10
童秀梅(1985—),女,湖北恩施人,重慶師范大學政治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行政管理;楊發坤(1980—),男,湖北恩施人,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社會管理與社會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