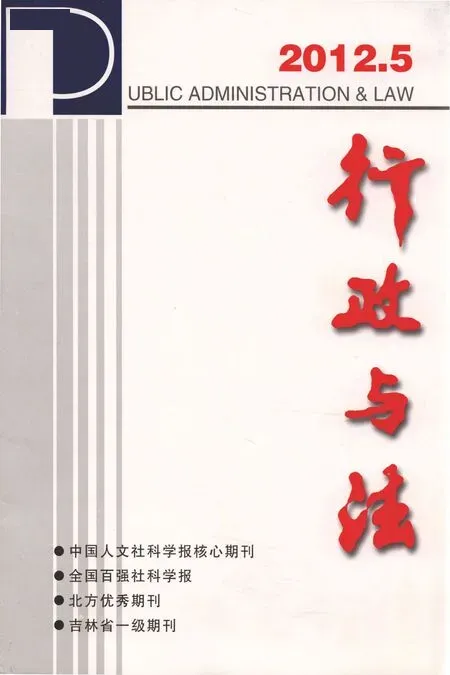風險社會理論給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帶來的挑戰與啟示
□ 張恩典,何志輝
(⒈淮南市工商局謝家集區分局,安徽 淮南 232052;⒉中共江西安義縣紀委,江西 南昌 330500)
風險社會理論給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帶來的挑戰與啟示
□ 張恩典1,何志輝2
(⒈淮南市工商局謝家集區分局,安徽 淮南 232052;⒉中共江西安義縣紀委,江西 南昌 330500)
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向世人宣告了風險社會的到來。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認為,現代社會的風險是文明的產物,不同于傳統社會的風險。風險社會理論在給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監管方式等帶來了挑戰的同時,也給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帶來了啟示:理性對待食品安全風險認知差異,建立食品安全風險規制體系,探索食品安全風險的復合治理方式。
風險社會;風險分析;不確定性;復合治理
在現代社會,風險充斥著社會的每個角落,影響著每個社會個體,我們已經置身于“除了冒險別無選擇的風險社會”之中。1986年,德國社會學家馬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邁向一種新的現代性》一書中最早使用“風險社會”這一概念,用來描述西方后工業社會所遭遇的核危機、生態危機等新型風險。同時,他指出,現代社會正處在“從財富分配的社會到風險分配的社會”的轉型之中,并以此為基礎系統地創立了風險社會理論。本文以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為視角,在分析風險 (社會)的定義及特征的基礎上,探討風險社會理論給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帶來的挑戰與啟示。
一、風險社會理論概述
風險這一概念是風險社會理論的核心范疇,包括貝克在內的風險社會理論研究者多是以風險概念為研究起點,在批判性地描述、分析后工業社會的風險形態、特征及成因的基礎上,建構各自的風險社會理論(以馬爾里希·貝克、安東尼·吉登斯為代表)和風險文化理論(以拉什為代表)。風險社會理論學說眾多,限于本文的論述主題及風險概念在風險社會理論中的核心地位,筆者選取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從風險概念入手,重點分析風險的定義與特征,力求以此把握風險社會理論之內涵。
(一)風險的定義
貝克認為,風險是文明的產物,與危險有著本質的區別。“風險概念是一個很現代的概念,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換句話說,只有在自然和傳統失去他們的無限效力并依賴于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1](p119)“風險概念創造了一種文明, 以便使自己的決定將會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后果具備了可預見性,從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過有意采取的預防性行動以及相應的制度化措施戰勝種種副作用。[2](p121)而我們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現代工業社會在為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創造舒適安逸的生存環境的同時,也帶來了核危機、生態危機等足以毀滅全人類的巨大風險。這些新型的風險不同于前工業社會時期人類所遭遇的各種自然災害,它源自于人類所做出的決策,源自于技術本身。為深入分析風險的本質,貝克還將風險概念與現代化理論聯系起來,他指出:“風險的概念直接與反思性現代化的概念相關。風險可以被界定為系統地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風險與早期的危險相對,是與現代化的威脅力量以及現代化引致的懷疑的全球化相關的一些后果。”[3](p19)在對風險社會深入剖析之后,貝克深化了其對風險概念的理解,并從正反兩個方面對其進行進一步廓清,將風險的含義歸結為以下八個方面:[4]⑴既不是毀滅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實的虛擬;⑵是有威脅的未來,(始終)與事實相反,成為影響當前行為的一個參數;⑶既是對事實也是對評價的陳述,它在“數字化的道德”中結合了起來;⑷控制或缺乏控制,就像在“人為的不穩定”中表現出的那樣;⑸在認識(再認識)沖突中表現出來的知識或不知;⑹由于風險的“全球性”而使全球與本土重組;⑺知識、潛在沖突和癥候之間的差別;⑻一個人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與文化之間的二元性。
(二)風險的特征
與工業社會相比,在風險社會中,人類所面臨的風險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其特點表現在:
⒈不確定性。不同于危險的客觀實在性,現代化風險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現代化風險并非源自于人類的無知與魯莽,而是源自于理性的規定、判斷與分析,是人類理性運用的結果。現代風險的不確定性與人類過度依賴科學與技術有著密切的關系。科學知識具有不確定性,具體表現為科學知識的爭論性、嚴格假設或方法論差異、不可預測性。[5]而且科學的不確定性是內在于科學的,是科學文化的重要特質,也是科學家工作中所熟悉的,并且不是都可以通過進一步的研究消除的。[6]這意味著,在利用科學和技術逃避危險、控制風險的過程中將產生新的風險,科學雖然能給我們提供新的知識,但是新的知識又會產生更多的不確定性,從而加劇了現代社會風險的不確定性。
⒉難以認知性。因為現代風險源自于科學技術,人們往往無法直接以感官來體驗,而科學知識的抽象性與技術的復雜性意味著現代風險需要借助專業知識、技術手段及精密儀器才能被認知,這無疑增加了普通民眾對風險認知的難度。同時,這也意味著普通民眾與專家在風險認知上存在很大差異。
⒊平等性。在現代社會中,風險分配與傳統社會財富分配方式不同,風險的分配超越了階級、身份及財富多寡的限制,普遍地影響到現代社會的每個個體。貝克將風險的這種“平等”稱之為“飛去來器效應”,“風險在它的擴散中展示了社會性的‘飛去來器效應’,即使是富裕和有權勢的人也不會逃脫它們”,“它不僅對單個的資源反戈一擊,而且以一種整體的、平等的方式損害著每一個人”。[7](p39-41)當然,風險的平等性也不是絕對的,在現實的具體情境中,風險的分配仍具有不平等性。
⒋自反性。貝克并不是孤立地分析風險社會的,而是將風險置于現代社會的宏觀考察之中,風險社會與現代性密切相關。根據貝克的現代化理論,現代化分為簡單現代化和自反性現代化。自反性現代化意味著“對由另一種現代性對工業社會形態首先進行抽離、接著重新嵌合”。[8](p5)由此可見,自反性現代化是現代化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社會中的危險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工業社會正在向風險社會過渡。在風險社會中,社會具有(狹義上的)自反性,這表明“不確定性”重新回歸到社會中,也就是說,工業社會在規避風險的同時,不斷制造新的風險,并促使社會向風險社會過渡。[9](p1-18)而且在風險社會中,風險“被界定為系統地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因此,風險的自反性特征意味著風險社會將變成一個技術批判的社會。這種批判并不是要徹底否定科學技術,雖然“科學技術和現代社會的發展強化或深化了不確定性,但重建新的不確定性還需要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我們不可能通過退回到過去解決問題”。[10]
必須指出的是,以貝克和吉登斯為代表的風險社會理論雖然極具批判性,但這并不表明他們對風險社會的未來持悲觀的態度。恰恰相反,他們對風險社會的未來持樂觀的態度,并且將風險分為積極風險和消極風險,當然這種樂觀是建立在反思基礎之上的。例如:在如何規避和應對風險這一問題上,“貝克和吉登斯的風險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制度主義傾向,即要在其風險社會理論中把制度性和規范性的東西突出出來并給予恰當的定位。他們的理想是能夠在制度失范的風險社會建立起一套有序的制度和規范,既能增加對風險的預警機制又能對社會風險進行有效的控制。”[11]
二、風險社會背景下我國食品安全監管所面臨的挑戰
風險社會理論作為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理論,對處于后工業社會的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相對而言,對中國的影響則要復雜得多。正如著名學者鄧正來教授所言,“當下的世界結構實際上對中國的發展構成了一種‘雙重強制’,因為它在自然時間向度上為中國的發展引入了兩個外部性的未來”:第一現代與第二現代。轉型中國具有第一現代和第二現代的共時性,使得中國的風險問題展現出比西方更大的復雜性。“風險沖突的矛盾性在于:在中國,風險既可以推動理性化和制度轉型,也消解了工業化和第一現代的基礎”。[12]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科學技術越來越多地被應用到食品生產、加工等各個環節之中,但伴隨著技術的大量應用,食品安全風險也隨之而來。風險社會之下,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監管主體及監管方式等都面臨著巨大挑戰。
在監管體制方面,根據我國2009年施行的《食品安全法》的規定,我國現行食品安全監管采取的是分段監管為主,品種監管為輔的體制。這種體制因為監管部門眾多,多頭監管,容易導致食品安全監管的“碎片化”,使執法資源分散,造成食品安全風險規制動力不足。[13]而且當發生食品安全事故時,食品安全監管部門之間往往互相推諉,容易導致貝克所說的風險社會下“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困局。
在監管主體方面,一直以來,我國強調政府監管在食品安全中的主導作用,并多采用政府的經濟性規制措施。但是,在風險社會下,食品問題中的風險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和難以認知性,政府在應對諸如食品添加劑等現代食品生產技術所產生的食品安全風險時往往會陷入捉襟見肘的尷尬境地,傳統的強調以國家監管為中心的食品安全監管模式常常是失效的。
在監管方式方面,與食品安全監管的國家主導模式相適應,我國在食品安全監管方式上采取發證(即市場準入)監管方式和事后監管方式。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發證監管的目的是“通過設立準入機制來控制市場參與者的數量和質量”,發證監管方式“符合中國歷來追求‘有序競爭’的主觀偏好。”[14]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容易產生以下兩個問題:一是發證往往淪為部門尋租設租,進行權錢交易的手段;二是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將“查無”作為食品安全監管的重要手段,運動式的圍堵“無證”耗費了大量的精力,致使對那些已經獲得審批的食品經營廠商疏于監管。事后監管是我國食品安全監管的另一重要方式。一直以來,我國食品安全監管中存在重事故處理、輕事故預防的現象,而且在具體的食品安全事故處理中,一方面,多采取短時間的運動式執法,運動式的整治往往依靠簡單的人海戰術,使得監管人員疲于奔命;[15]另一方面,依靠正式的行政處罰甚至是刑事處罰,試圖以“重罰和重刑”所產生的威懾力在短時間內解決食品安全問題。事實上,這種事后監管方式根本無法應對現代社會中因技術原因導致的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擴散性的食品安全風險。
三、風險社會理論給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帶來的啟示
風險社會理論在給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帶來挑戰的同時,也給我們重新審視我國食品安全風險,從而進一步完善食品安全風險規制策略與機制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
(一)正確對待食品安全風險認知差異
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頻繁發生,使公眾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恐懼,這種社會恐懼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的嚴重性,也暴露出公眾與專家對我國食品安全風險所存在的認知差異。公眾更多依憑直覺來認知風險,而且容易受輿論媒體的影響。“公眾對于感同身受、被媒體廣泛報道、有可能切實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風險,會有很強的認知。”[16]美國法學家凱斯·孫斯坦認為:“在許多情況下,人們認為某種風險是十分有害的判斷并不是充分的定性評估,而是由于受到情感的綜合的影響,部分地源于關于可能事實的不可靠的直覺”。[17](p12)專家對風險的認知則是建立在科學分析判斷的理性基礎之上,并運用大量的現代技術和規則進行數據分析,從而得出風險程度和概率的評估的。較之于脫離現實的空想或者邏輯上混亂的觀念,科學更具有確定性,更具有說服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科學和專家對食品安全風險的認知就是確定無疑的。科學的確定性是相對的,而不確定性是固有的。同時,專家也有其源于又不完全等同于科學局限的不可靠性。[18]在現代風險社會,公眾與專家在風險認知上存在差異是必然的,因此,首先,我們需要正視兩者的認知差異,加強風險溝通,在公眾與專家之間建立信任的橋梁。其次,在食品安全風險的規制措施制定中不能以直覺和恐懼為依據,而應當建立在對后果評估的基礎上。[19](p12)但是,這并不是說公眾的風險認知在食品安全風險規制活動中就不重要,實際上,在風險社會中,公眾對行政機關的食品安全風險規制活動具有更多的實質合理性期待。[20]
(二)構建以風險分析為基礎的食品安全風險規制體系
風險分析原則作為現代食品安全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已成為國際公認的食品安全管理理念。它指的是對食品安全中可能存在的風險進行評估,進而根據風險程度來采取相應的風險管理措施以控制或者降低風險,并且在風險評估和管理的全過程中保證風險相關各方保持良好的風險狀態。風險分析由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和風險交流三個部分組成。
風險評估是指對人體接觸食源性危害而產生的已知或潛在的對健康不良的影響的科學評估,是一種以系統的組織科學技術信息及其不確定性信息來回答關于健康風險的具體問題的評估方法。[21]風險評估是風險分析和風險規制的關鍵環節,是風險管理、風險交流的前提和基礎。在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工作中,包括危害因素的識別、危害因素的描述、暴露劑量的評估、風險特征的描述,主要是一個事實分析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需要借助專家在理性知識上的優勢,利用現代技術獲取相關數據,并運用技術與規則進行數據分析。因此,專家知識在風險評估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但是,風險評估并不全然與價值無涉,而是密切相關。例如:“在風險評估議程和優先次序的設置上,科學、專家的作用則趨弱,價值偏好的因素加強,就更需要通過來自多元化公眾的風險監測信息與風險評估建議,以避免某種價值偏好的過分影響。”[22]
風險管理是指一個在與各利益方磋商過程中權衡各種政策方案的過程,該過程考慮風險評估和其他與保護消費者健康及促進公平貿易活動有關的因素,并在必要時選擇適當的預防和控制方案。與風險評估對專家、科學的極度依賴不同,風險管理是在選取最優風險管理措施時對科學信息及其他因素如經濟、社會、文化與倫理等進行整合和權衡的過程。[23]
在風險社會,食品安全風險管理應當確立風險預防原則。該原則最早起源于德國的環境法領域,是指在缺乏充分科學確定性證明人類的行為會損害環境的情況下,要求采取預防的措施。根據預防的強度,預防原則可以分為強風險預防原則和弱風險預防原則。前者指除非能夠確定一項行動沒有任何危害,否則不能進行;后者指缺乏充分的確定性不能作為采取措施預防可能帶來危害的行為的理由。[24]前者條件過于嚴格,后者則綜合考慮相關成本收益、社會經濟因素、尋找替代方案,在實踐中被較多采納,亦符合我國的現實國情。
風險交流是指在風險分析全過程中,風險評估人員、風險管理人員、消費者、產業界、學術界以及其他感興趣各方就風險、風險相關因素和風險認知等方面的信息、看法進行互動式交流,內容包括風險評估結果的解釋和風險管理決定的依據。風險交流的必要性來源于食品安全風險信息的不對稱性和風險認知的差異性。“充分和真實可靠的食品安全風險信息,是食品安全風險規制機關制定食品安全風險規制政策,進行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實施食品安全風險溝通以及管理的基礎。”[25]因此,在風險交流過程中,需要保證食品安全信息的充分和真實,打破風險信息的不對稱性。
風險源于不確定性,風險規制的難題在于規制者必須決策于不確定性之中,而這種不確定源于相關信息的缺乏。[26]同時,食品安全信息具有公共產品屬性,這意味著政府在食品安全信息供給上負有法定的義務。[27]但是,在食品安全信息的獲取上,食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處于優勢,而政府和消費者均相對處于劣勢,且食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在利益驅動之下選擇 “集體沉默”。面對這種情形,一方面,需要食品安全風險規制機關發現并利用不對稱的預期利益的策略,通過激勵制造不對稱性預期利益的策略來打破同行食品生產和經營企業之間的集體沉默。[28]另一方面,需要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平臺,及時公開食品安全風險信息。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如何保證食品安全風險溝通的有效性,克服風險溝通中的障礙以及建立溝通中的信任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由于風險溝通過程中溝通主體的地位并非是平等的,公眾一方往往處于接受信息、詢問信息的狀態,因此,溝通的另一方,無論是政府部門或者是其他的管理機構,是否將公眾視為伙伴,對溝通的有效性具有決定性的影響。[29]
(三)通過復合治理規制食品安全風險
在現代風險社會,作為面向未來的風險規制,具有高度的復雜性、情境依賴性和不確定性。[30]我國傳統食品安全規制模式是一種以行政命令為基礎、以政府為單一規制主體的管理模式,重政府管理而輕社會參與,顯然無法應對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泛在性的現代食品安全風險。因此,食品安全風險規制應當從傳統命令式的管理模式向現代參與式治理模式轉變,鼓勵和支持包括專家、食品經營者、消費者及其他社會組織在內的多元主體參與到食品安全風險治理中來,走復合治理之道,以應對食品安全風險。
治理有別于傳統的政府統治與管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認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1]治理符合人類對善治的價值追求,與現代協商民主的精神內核亦高度契合,是協商民主的集中體現。因為,“在協商民主中,公民們通過交換他們的公共理性在自由而開放的談話中坦言相見,即使他們的理由沒有說服對方,只要他們認真對待和回應對方關切的事情和所持的看法,他們也就能夠得到對方對他們看法的領會與思考。”[32](p7)這實際上是力圖在“公”主體與“私”主體之間形成一種合作伙伴關系。這種多元主體參與下的食品安全復合治理模式能夠最大程度地克服專家和政府在應對現代食品安全風險中“有限理性”的不足,克服科學和技術在食品安全風險規制中的固有局限性。
因此,當務之急,一方面,要實行食品安全風險信息公開,保障公眾的食品安全風險信息知情權,這是公眾參與食品安全風險規制的前提和基礎;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風險規制參與程序,通過具體的制度設計,保障公眾參與食品安全風險規制的程序性權利,這是公眾參與食品安全風險規制的關鍵。
[1][2](德)烏爾里希·貝克,約翰內斯·威爾姆斯.路國林譯.自由與資本主義——與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對話 [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7](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M].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2004.
[4](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再思考[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04).
[5]陳光,溫珂,牟治平.專家在科技咨詢中的角色演變[J].科學學研究,2008,(02).
[6]徐凌.科學不確定性的類型、來源及影響[J].哲學動態,2006,(03).
[8][9](德)烏爾里希·貝克,(英)安東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代化: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與美學[M].趙文書譯.商務印書館,2001.
[10]韓震.關于不確定性與風險社會沉思——從日本“3·11”大地震中的福島核電站事故談起[J].哲學研究,2011,(05).
[11]莊友剛.風險社會理論研究述評[J].哲學動態,2005,(09).
[12]貝克,鄧正來,沈國麟.風險社會與中國——與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的對話[J].社會學研究,2010,(05).
[13][30]趙鵬.風險規制:發展語境下的中國式困境及其解決[J].浙江學刊,2011,(03).
[14]劉亞平.中國式“監管國家”的問題與反思——以食品安全為例[J].政治學研究,2011,(02).
[15]劉亞平.中國食品安全的監管痼疾及其糾治[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03).
[16]宋華琳.風險認知與議程設定——評桑斯坦《最差的情形》[J].綠葉,2011,(04).
[17][19](美)凱斯·R·孫斯坦.風險與理性——安全、法律及環境[M].師帥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
[18][20]戚建剛.風險規制過程合法性之證成——以公眾和專家風險知識運用為視角[J].法商研究,2009,(05).
[21]譚德凡.論食品安全法基本原則之風險分析原則 [J].河北法學,2010,(06).
[22]沈巋.風險評估的行政法治問題——以食品安全監管領域為例[J].浙江學刊,2011,(03).
[23]孔繁華.論預防原則在食品安全法中的適用[J].當代法學,2011,(04).
[24]戚建剛.向權力說真相:食品安全風險規制中的信息工具之運用[J].江淮論壇,2011,(05).
[25][28]高秦偉.論歐盟行政法上的風險預防原則 [J].比較法研究,2010,(03).
[26]金自寧.作為風險規制工具的風險交流——以環境行政中的TRI為例[J].中外法學,2010,(03).
[27]趙學剛.食品安全供給的政府義務及其實現路徑[J].中國行政管理,2011,(07).
[29]謝曉非,鄭蕊.風險溝通與公眾理性[J].心理科學進展,2003,(04).
[31]俞可平.治理與善治:一種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會科學,2001,(09).
[32](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協商:多元主義、復雜性與民主[M].黃相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責任編輯:高 靜)
On Challenges and Enlightenments of Risk Society Theory to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China
Zhang Endian,He Zhihui
Beck's theory of risk society declared the coming of risk society to the world.Risk society theory of Beck thought that the risk of modern society,as a product of civilization,wa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risk.Risk society theory posed challenges to China's food safety regulatory system and regulation.At the same time,it also brought enlightenments for China's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s follow:we should adopt a rational approach to food safety cognition difference on risk,establish a food safety risk regulation system and explore the food safety risk integrated management mode.
risk society;risk analysis;uncertainty;integrated management
C916.1
A
1007-8207(2012)05-0053-05
2011-12-23
張恩典 (1983—),男,江西東鄉人,淮南市工商局謝家集區分局工作人員,法學碩士,研究方向為行政法學、民商法學;何志輝 (1984—),男,江西東鄉人,中共江西安義縣紀委工作人員,江西省委黨校在職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行政法學、發展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