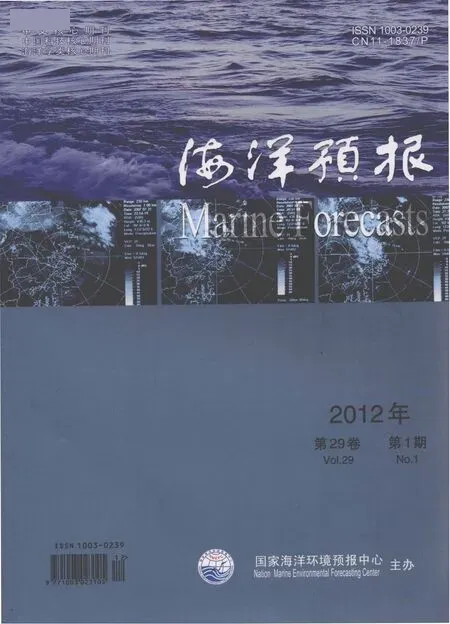0917號臺風“芭瑪”折向東南向移動原因分析
魏新,王力群,李海寧
(中國衛星海上測控部,江蘇江陰 214431)
0917號臺風“芭瑪”折向東南向移動原因分析
魏新,王力群,李海寧
(中國衛星海上測控部,江蘇江陰 214431)
利用NCEP全球數據同化系統(GDAS)1°×1°分析資料,對0917號臺風“芭瑪”折向東南向移動原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中高緯度環流調整是“芭瑪”折向東南向移動的根本原因;0918號臺風“茉莉”通過改變外圍環境場的強度、形狀對“芭瑪”臺風產生間接影響,而兩臺風之間逆時針互旋以及臺風“茉莉”外圍強大的環流對臺風“芭瑪”的直接作用是臺風“芭瑪”折向東南向移動的關鍵。對臺風“芭瑪”經緯向UV最大風速變化診斷分析表明,“芭瑪”經緯向UV最大風速中心的轉移對“芭瑪”折向東南向移動有重要影響,經緯向UV最大風速差的變化對“芭瑪”轉向具有預示作用,經緯向最大風速差的合成風方向與臺風中心未來移動方向有一定的關系。
臺風;異常路徑;環流調整;雙臺風效應;UV最大風速差
1 引言
臺風長期以來被視為受環境場引導而移動的渦旋,對其移動路徑的預報轉化為對環境場引導氣流的預測。但預報實踐中,在環境場引導氣流無明顯改變的情況下,臺風移速、強度、移向仍會發生突然變化。20世紀80年代Holland[1]提出了β效應,認為臺風移動不僅受大尺度環流場的引導,還有β效應,臺風的移動受環境流場和β效應的共同影響,氣流引導理論得到廣泛應用。但由于影響臺風移動路徑因子復雜,如環境場調整、臺風自身結構與強度變化、β效應、環境加熱以及臺風與周圍大氣環境場的相互作用等,都會影響臺風移動路徑,因而對異常路徑臺風的預報準確率還不理想[2],特別是在弱環境場中臺風實際移動路徑往往發生突然轉向,導致預報失誤。陳聯壽[3]提出了臺風結構不對稱概念,指出臺風移動路徑變化與臺風結構有關。20世紀90年代,Elsberry[4]把環境流場、β效應和非對稱對流總結為影響臺風移動的三個基本因子,之后對臺風的研究主要圍繞這三個因子展開。
本文利用國家氣象中心熱帶氣旋定位資料、NCEP全球數據同化系統(GDAS)1°×1°分析資料,從環流場演變、β效應、雙臺風相互作用、經緯向風速變化方面對2009年9月下旬生成于西北太平洋關島以南洋面的0917臺風“芭瑪”活動過程及特點進行分析,探討“芭瑪”移動路徑折向東南向移動的原因,為今后在實際業務中預報異常路徑臺風提供參考。
2 “芭瑪”臺風概況及特點
“芭瑪”臺風于2009年9月29日在西北太平洋關島以南洋面8.0°N、140.0°E附近海域生成。“芭瑪”臺風生成初期向西移動,9月30日之后轉向,穩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動。臺風在移動的過程中強度逐漸增強。10月1日14時,中心位于12.5°N、129.7°E附近,強度達到最強,中心氣壓920 hPa、風力55 m/s(16級)、7級風圈半徑300 km、10級風圈半徑150 km,達到超強臺風強度。“芭瑪”臺風10月3日14時在呂宋島東北部登陸時減弱為強臺風,中心最大風力減弱到14級,移動速度減慢。穿過菲律賓北部后,繼續向西北方向移動。10月5日晚于20.1°N、119.7°E附近的巴士海峽180°轉向,折向東南方向移動。10月6日第二次登陸呂宋島西北部,登陸時臺風減弱為強熱帶風暴,中心最大風力10級。10月7日,“芭瑪”臺風移出呂宋島,強度逐漸減弱為熱帶低壓。10月8日凌晨在呂宋島近岸海域重新發展,增強為熱帶風暴,并轉向偏西方向緩慢移動,中午第三次登陸呂宋北部,在呂宋西北部入海進入南海北部,10月12日上午登陸海南島萬寧市,晚上移出海南,強度突然增強,加強為強熱帶風暴。10月14日晚登陸越南并減弱為熱帶風暴,隨后迅速減弱為熱帶低壓填塞消失(見圖1)。
從“芭瑪”臺風的整個活動過程看,“芭瑪”臺風有如下特點:
(1)臺風生命期長。“芭瑪”臺風從9月27日形成熱帶低壓到10月14日減弱為熱帶低壓,整個活動過程持續18天,經歷了從熱帶低壓到超強臺風的所有過程,生命期是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臺風之一,是一般熱帶氣旋的生命期的3倍;
(2)強度變化反復無常。“芭瑪”臺風從9月29日生成后,強度一直加強,30 h后加強為臺風,21 h后又增強為超強臺風。在第二次登陸呂宋島后,10月7日,強度一度減弱為熱帶低壓,之后又加強為熱帶風暴。10月10日在中國南海又一次減弱為熱帶低壓,直到在12日登陸海南島之前加強為熱帶風暴,之后強度迅速增強,一度達到強熱帶風暴,登陸越南后才逐漸減弱為熱帶低壓;

圖1“芭瑪”臺風的移動路徑和“茉莉”臺風的移動路徑
(3)路徑詭異,登錄次數多。在“芭瑪”臺風整個生命史中,經歷了2次主要的轉向、5次登陸過程,其中在菲律賓登陸3次。臺風生成初期向西北方向移動,在10月5日晚上突然180°轉向,折向東南方向移動。10月8日再次轉向偏西方向移動,經過中國南海直至在越南登陸,其中臺風轉向東南方向移動路徑實為罕見,預報難度大,預報失誤率高;
(4)影響范圍廣,造成損失大。“芭瑪”臺風是歷史上造成損失最大的臺風之一,強風暴雨持續時間長,影響范圍廣,在歷史上少見。“芭瑪”臺風使菲律賓、臺灣、海南、廣東、廣西、越南等多地不同程度受災,尤以菲律賓損失嚴重,造成菲律賓數百人傷亡和巨大的財產損失。
3 環流場對“芭瑪”臺風折向東南前、后移動路徑的影響
臺風移動路徑受大尺度環流場和β效應的制約[5]。在研究西北太平洋臺風移動路徑時,許多專家學者注重環境場變化的研究[6],特別關注西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演變對臺風移動路徑的影響[7]。“芭瑪”臺風從9月29日生成到10月5日轉向前,穩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動。10月5日后移動路徑突然折向東南,“芭瑪”臺風移動路徑的這種變化,與此期間500 hPa等壓面上環流場變化有關。
3.1 環流場變化對“芭瑪”臺風折向前西北向移動路徑的影響
在9月29日20時500 hPa等壓面上(見圖2a),中高緯度大氣環流為兩槽一脊型,西風槽分別位于貝加爾湖和鄂霍次克海附近,兩槽槽底在40°N以北,高壓脊位于大興安嶺一帶,西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呈東西帶狀,
勢力強大,5920 gpm閉合線的面積大約10緯距×20緯距,脊線在28°N附近,西脊點伸展到120°E以西,5860 gpm線控制我國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中高緯環流呈緯向分布,冷空氣活動偏北。隨著高壓脊東移,副熱帶高壓加強西伸,10月2日14時500 hPa等壓面上,20°—30°N歐亞區域被副熱帶高壓脊控制。此期間臺風“芭瑪”在副高南側偏東引導氣流和β效應的共同作用下,以5—20 km/h速度穩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動。

圖2 500 hPa等壓面環流場
臺風“芭瑪”向西北移動的過程中,位于貝加爾湖的西部槽緩慢東移并發展加深,3日14時,槽線位于120°—130°E之間,槽底伸展到30°N。副熱帶高壓在西部槽東移南壓過程中減弱,斷為兩環,西環位于中南半島,東環中心位于西北太平洋中部。西部槽后的高壓脊發展加強,在貝加爾湖以西形成阻塞形勢,北部冷空氣在新西伯利亞堆積,在500 hPa等壓面上100°—120°E之間、45°N以北區域形成一橫槽,我國西南地區有一南支槽生成,并沿西環副高北側向東快速移動,和橫槽形成階梯槽形勢。此時臺風“芭瑪”中心位于122.1°E、17.7°N的位置,與槽底相距10個以上緯距,距離較遠,西風槽對“芭瑪”臺風影響較小,引導“芭瑪”臺風移動的引導氣流變弱,臺風處于弱環境場中(見圖2b)。
隨著西部槽和南支槽繼續東移,3日后,西環高壓單體在南支槽的影響下南壓西退,臺風“芭瑪”西部的位勢高度減小。受0918號臺風“茉莉”向西移動過程中對副高擠壓,臺風“茉莉”與臺風“芭瑪”之間的副熱帶高壓西進,臺風“芭瑪”東側的位勢高度增加。位勢高度的這種變化,產生指向“芭瑪”西部的位勢梯度力,使“芭瑪”向西移動[8]。而“芭瑪”東側位勢梯度增大,使引導臺風北上的偏南氣流增強,有引導“芭瑪”北上的趨勢。在這幾種因子與β效應共同作用下,促使“芭瑪”向西北方向移動。但由于“茉莉”與“芭瑪”之間的副熱帶高壓在西進過程中向“芭瑪”南北兩側伸展,在“芭瑪”北部受形成一高壓區,對臺風“芭瑪”北上產生抑制作用;而嵌入“芭瑪”臺風南部的副高則迫使臺風向北移動[9]。臺風“芭瑪”10月3—5日期間在弱環境場中的西北向移動,是以上幾種因子共同作用的結果,由于這幾種因子相互牽制,臺風移動速度非常緩慢,甚至打轉。
由此看見,“芭瑪”臺風10月3日后在弱環境場中向西北向移動,是β效應以及中低緯度天氣系統相互作用的結果。中低緯度天氣系統通過改變西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強度、位置、形狀的變化,使影響“芭瑪”臺風移動路徑的作用因子發生改變。這幾種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因子使“芭瑪”臺風10月3日后的移速非常緩慢。這與3日前臺風由副高引導向西北向快速移動有本質區別。
3.2 中高緯度環流的調整是“芭瑪”臺風折向東南向移動的根本原因
陳聯壽等[5]認為,大尺度環流場的調整易造成熱帶氣旋移動路徑突變。
臺風“芭瑪”向西北緩慢移動的過程中,貝加爾湖以西形成的阻塞形勢進一步發展。在此期間,隨著南支槽的東移,原來位于120°—130°E之間的西風槽減弱。當位于巴爾喀什湖附近的低壓在4日14時東移到貝加爾湖以西,并向阻塞高壓南部切入,阻塞高壓被切斷,中高緯度環流進行了劇烈的調整,南下的冷空氣使南支槽發展加深。在5日20時500 hPa等壓面環流場上,南支槽東移到122°E附近,取代原來西風槽的位置,槽底伸展到27°N附近。中南半島的高壓單體在南下冷空氣的影響下進一步減弱西退,我國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逐漸由原來的偏西氣流轉變為西北氣流控制(見圖2c)。
臺風“芭瑪”5日20時位于西風槽的底部,與槽底相距8個緯距左右。隨著西風槽繼續東移,臺風“芭瑪”逐漸位于西風槽后部。西北太平洋的副熱帶高壓單體在西風槽的作用下又一次減弱東退,臺風“芭瑪”與臺風“茉莉”之間的高壓也隨之減弱,原來使“芭瑪”臺風西北向移動的位勢梯度力和偏南引導氣流減弱消失。隨著5日20時槽后西北氣流侵入,“芭瑪”臺風北部逐漸由槽后西北氣流控制,西北氣流5日20時后突然增強。而中南半島的高壓單體在南壓的過程中,與“芭瑪”臺風南部的高壓打通,形成西北-東南向的高壓帶,使其東北側西北氣流增強。“芭瑪”臺風正是在上述西北引導氣流增強的情況下,5日20時后折向東南方向移動。之后,隨著西風槽的進一步東移,環流場西北氣流逐漸轉為偏西氣流,但隨著“茉莉”臺風的北上,其外圍西北氣流對“芭瑪”臺風的影響增強,受這幾種因素的共同影響,“芭瑪”臺風繼續向東南方向移動(見圖2d)。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阻塞形勢崩潰與“芭瑪”臺風移動路徑的突然轉向相對應。中高緯度環流場調整使弱環境場中影響“芭瑪”臺風西北向移動的作用因子減弱,西北引導氣流增強,從而使“芭瑪”臺風折向東南方向移動。因此,中高緯度環境場調整是“芭瑪”臺風移動路徑突變的根本原因。
4 “茉莉”臺風對“芭瑪”臺風折向東南向前后移動路徑的影響
4.1“茉莉”臺風對“芭瑪”臺風西北向移動的影響
對于雙臺風的研究,騰原效應的模型概念在分析雙臺風的相互影響時被廣泛應用,但這個模型無法解釋雙臺風之間距離大于臨界距離(大約7個緯距)時仍存在相互作用的問題。90年代后期,Carr[10]提出了雙臺風之間存在直接、半直接、間接相互作用新模型,指出當兩臺風之間距離小于7個緯距時,存在顯著的互旋,大于15個緯距時,多通過環境場發生間接作用。羅哲賢[11]對這個模型進行了數值研究,證明了模型合理性。
在“芭瑪”臺風形成6 h后,0918號臺風“茉莉”也在關島以南洋面生成,并以10—15 km/h的移速沿副高南側向西北方向移動。“茉莉”臺風在10月2日增強為強臺風,10月3日移速顯著加快,移速達到25—28 km/h,強度繼續加強。10月3日中午,“茉莉”臺風和“芭瑪”臺風之間相距20緯距左右(見圖1)。

圖3 500 hPa等壓面時流場
從兩臺風的活動過程看,3日14時前臺風“茉莉”與臺風“芭瑪”中心之間的距離大于20個緯距,它們之間的距離較遠,相互作用并不明顯。隨著臺風“茉莉”3日14時后逐漸靠近“芭瑪”,兩臺風中心之間的距離逐漸小于20個緯距,“茉莉”臺風對“芭瑪”臺風移動路徑產生一定地牽制作用。從3日14時500 hPa等壓面流場圖上分析(見圖3a),隨著“茉莉”臺風向西北向移動,臺風“茉莉”與“芭瑪”之間的副高在“茉莉”擠壓下向“芭瑪”靠近,受中南半島副高單體對臺風“芭瑪”西進的阻擋,副高向“芭瑪”臺風南北兩側切入,形成包圍“芭瑪”態勢。如前節分析,副高在環流場上的這種變化,使“芭瑪”臺風東部位勢高度梯度增大,產生使“芭瑪”臺風向西移動的梯度力,同時“芭瑪”臺風東側的偏南引導氣流增強,臺風南側高壓的發展使“芭瑪”臺風北上,它們的共同作用使“芭瑪”向西北方向移動。但由于“芭瑪”臺風西部中南半島的副高單體和臺風北部的高壓區阻擋,抑制了“芭瑪”臺風西北向移動速度。因此,“芭瑪”臺風在10月3日14時后正是在這幾種因素的共同影響下仍繼續向西北方向移動,但移速減小到2 km/h,甚至在原地打轉。
由此可見,臺風“芭瑪”折向東南向移動前的西北向移動路徑,與臺風“茉莉”對“芭瑪”間接作用有關。臺風“茉莉”西北向移動引起副熱帶高壓形狀、強度、位置變化,使作用于臺風“芭瑪”的環流場發生改變,從而影響了臺風“芭瑪”的移動路徑。因此,臺風“茉莉”對“芭瑪”的間接作用,是臺風“芭瑪”折向前繼續向西北移動的主要原因之一。
4.2 臺風“茉莉”對臺風“芭瑪”移動路徑折向東南向移動的影響
“茉莉”臺風通過環流場對“芭瑪”臺風的牽制作用是“芭瑪”臺風10月3日后向西北方向緩慢移動或打轉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雙臺風效應最顯著的特點是兩臺風之間的互旋,這種互旋作用容易引起臺風移動路徑異常[10]。
臺風“茉莉”中心4日14日位于17.0°N、140.9°E,中心風力達到17級(65 m/s),中心氣壓為905 hPa,達到超強臺風強度。5日20時,臺風“茉莉”中心位于20.0°N、133.6°E,以25 km/h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動。臺風“芭瑪”中心5日20時位于20.1°N、119.7°E,中心最大風力僅為11級,兩臺風之間的距離最近,相距大約11個緯距。從圖1可以看出,當臺風“茉莉”在5日20日后繼續北上進入“芭瑪”臺風東北象限時(見圖3b),也正是兩臺風中心之間距離最近的時候,臺風“芭瑪”180°轉向,折向東南方向移動,與臺風“茉莉”形成顯著的逆時針互旋,這是兩臺風之間的直接相互作用。6日14時之后,隨著臺風“茉莉”繼續北上,臺風“茉莉”與“芭瑪”之間距離逐漸變遠,兩者之間直接作用減弱,但“茉莉”西南側的西北氣流進入“芭瑪”北部,使“芭瑪”東南向移動的西北引導氣流增強,引導臺風“芭瑪”繼續向東南向移動,這是“茉莉”對“芭瑪”的半直接的作用過程。
由此可見,“茉莉”臺風對“芭瑪”臺風折向東南向移動路徑有顯著的影響。臺風“茉莉”與“芭瑪”之間的互旋是“芭瑪”臺風折向東南向移動的關鍵,臺風“茉莉”對“芭瑪”臺風的半直接作用是“芭瑪”臺風維持東南向移動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臺風“茉莉”對“芭瑪”的直接、半直接作用過程,對“芭瑪”臺風東南向移動路徑有顯著的影響。
5 UV風速變化對“芭瑪”臺風移動路徑的指示作用
陳聯壽[5]指出,在弱環境場中,臺風的非對稱結構是造成臺風移動路徑異常的重要原因。張勝軍等[12]對Helen臺風(9505)移動路徑進行診斷分析與數值模擬結果表明:當最大風速區位于臺風環流的西南象限,臺風表現為顯著西行北翹異常路徑,當最大風速區位于臺風東北象限時,其路徑為西北行,沒有明顯的北翹過程。吳乃庚[13]等在研究“派比安”臺風移動路徑時發現,“派比安”臺風最大風速區的長軸軸線方向與臺風的移動方向一致。為了探討“芭瑪”臺風折向東南向移動的原因,我們對“芭瑪”臺風500 hPa等壓面上經緯向UV最大風速在臺風“芭瑪”折向東南向移動前后的特點進行分析。
在“芭瑪”臺風活動過程中,500 hPa等壓面上經向風速V和緯向風速U各存在兩個最大風速中心,分別位于臺風的南北和東西兩側。在5日20時臺風折向東南方向移動前,經向南風(+V)最大風速大于北風(-V)最大風速,緯向東風(-U)最大風速大于西風(+U)最大風速,經緯向最大風速在東西、南北方向表現為不對稱,表明臺風結構在風場上也呈不對稱。從5日20時開始,經向北風(-V)最大風速大于經向南風(+V)最大風速,緯向西風(+U)最大風速大于緯向東風(-U)最大風速。顯然,經緯向最大風速中心發生了轉移,強風區的轉移極易導致臺風移動路徑的突變,結果“芭瑪”臺風5日20時后移動路徑折向東南向移動。

圖4 △V、△U隨時間變化(△V=V-(-V),△U=U-(-U)
進一步分析發現,臺風移動方向與經緯向最大風速差存在一定對應關系。圖4是經緯向最大風速差隨時間變化曲線。由圖可以看出,“芭瑪”臺風在5日20時折向東南向移動前,500 hPa等壓面上南風(+V)和北風(-V)最大風速差△V指向北(△V為正值),東風(-U)和西風(+U)的差值△U指向西(△U為負值),△V、△U的合成風方向指向西北方向,與這期間臺風西北向移動路徑相一致。
從5日20時開始,△V、△U的方向發生了變化,南風(+V)和北風(-V)最大風速差指向南(△V為負值),東風(-U)和西風(+U)的差值指向東(△U為正值),△V、△U的合成風方向指向東南方向,與這期間臺風折向東南向移動路徑相對應。
通過以上分析看出,經緯向最大風速的轉移導致“芭瑪”臺風移動路徑的突變,經緯向最大風速的差△V、△U對臺風轉向及移動路徑具有預示作用,“芭瑪”臺風未來移動方向與經緯向最大風速差△V、△U的合成風方向一致。
6 結論
(1)“芭瑪”臺風生成后在副熱帶高壓南部偏東氣流的引導下穩定地向西北向移動。10月3日后在弱環境場中的西北向移動,是中低緯天氣系統相互作用的結果。中低緯度天氣系統通過改變西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強度、位置、形狀變化,使影響“芭瑪”臺風移動路徑的作用因子改變,是幾種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因子共同作用的結果;
(2) 中高緯度環流調整是“芭瑪”臺風移動路徑折向東南的根本原因。“芭瑪”臺風折向東南方向移動與中高緯度阻塞形勢崩潰、環流從經向型向緯向型調整有關;
(3)“茉莉”臺風對“芭瑪”臺風移動路徑有直接、半直接和間接的影響。臺風“茉莉”通過改變副熱帶高壓形狀、強度、位置變化,進而使作用于臺風“芭瑪”的環流場發生改變,從而影響了臺風“芭瑪”10月3日后的西北向移動路徑。10月5日后臺風“茉莉”與“芭瑪”之間的逆時針互旋是“芭瑪”臺風折向東南移動的關鍵。“茉莉”臺風通過外圍環流對“芭瑪”臺風東南向移動仍有一定影響;
(4)“芭瑪”臺風經緯向最大風速的變化對臺風轉向有重要的預示作用。經向風最大風速差和緯向風最大風速差的變化不僅對臺風的轉向有預示作用,而且其合成風方向對臺風未來移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示意義。
[1]Greg L.Holland.Tropical cyclone motion: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 plus a beta effect[J].JAtmos Sci,1983,40:328-342.
[2]陳聯壽,孟智勇.我國熱帶氣旋研究十年進展[J].大氣科學,2001,25:420-432.
[3]陳聯壽.熱帶氣旋運動研究和業務預報的現狀和發展[A].臺風會議文集(1985)[C].北京:氣象出版社,1987:6-30.
[4]Russell L.Elsberry.Global perspectives of tropical cyclones[M].Geneva:WTO,1995:114-117.
[5]陳聯壽,丁一匯.西北太平洋臺風概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
[6]朱永褆,程戴暉.環境基流變化對熱帶氣旋移動的影響[J].大氣科學研究與應用,1994(7):31-36.
[7]楊美川,朱永褆.熱帶氣旋穿越副熱帶高壓的數值試驗[J].熱帶氣象學報,1998,14(1):85-90.
[8]紀文君,郭湘平,劉正奇.臺風轉向的動力診斷分析[J].海洋預報,2002,19(2):7-14.
[9]高珊,何小寧,凌士兵.0407號臺風“蒲公英”路徑突然北折的原因分析[J].臺灣海峽,2005,24(4):448-454.
[10]Lester E.Carr,Russell L.Elsberry.Objective diagnosis of binary tropical cyclone interactions for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basin.Mon Wea Rev,1998,126:1734-1749.
[11]羅哲賢,馬鏡賢.副熱帶高壓南側臺風相互作用的數值研究[J].氣象學報,2001,59(4):451-457.
[12]張勝軍,陳聯壽,徐祥德.Helen臺風(9505)異常路徑的診斷分析與數值模擬[J].大氣科學,2005,29(6):937-946.
[13]吳乃庚,林良勛,李天然,等.環境流場和“派比安”結構變化對其異常北抬路徑影響的診斷分析[J].氣象,2007,33(11):9-15.
Analysis of typhoon Parma's track southeast turn
WEI Xin,WANG Li-qun,LI Hai-ning
(China Satellite Maritime Tracking and Controlling Department,Jiangyin 214431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data of 1°x1°Global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GDAS)from NCEP,No.0917 typhoon Parma's path turning southeast are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urning of Parma's path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adjustment of Mid-latitude circulation.No.0918 typhoon Jasmine indirectly influences Parma’s path through changing the strength and shape of peripheral environmental field.The counter-clockwise rotation between the two typhoons and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Parma's peripheral powerful circulation are key factors for Parms's track southeast turning.The analysis of Parma's UV maximum wind speed change in warp and weft direction shows that the transference of its center and the variation of its maximum wind speed difference respectively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and indicating function,and its synthetic wind direction ha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typhoon's future motion way.
typhoon;abnormal path;circulation adjustment;double typhoon effect;UV maximum wind speed difference
P444
A
1003-0239(2012)01-0006-07
2011-03-22
魏新(1966-)男,高級工程師,從事海洋氣象保障工作。E-mail:whh980707@189.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