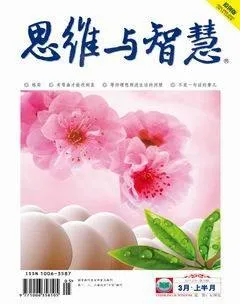掬水月在手
極喜歡一句有趣、空靈的佛語,叫“掬水月在手”。曼妙夜空,皓月高懸,近之又非嫦娥吳剛,于是慧心一閃,掬一捧水,月亮美麗的臉龐就燦爛在手掌心里,一片禪心也在月色里氤氳開來……
有月當空,有水可掬,有月盈手,虛實相映,虛幻縹緲。掬之趣,趣在一念之轉,趣在一掬得月,趣在有月映心。
每每品味“掬水月在手”,腦中總浮現這樣的場景:萬里春江,一片空明,水光月色,交相輝映。在澄明迷幻的色調中,在幽邃渺遠的意境里,端坐著一位白衫老者,白發銀須飄動,目光清澈悠遠,手掬一捧江水,思緒穿越千年。背景有五十弦錦瑟彈奏的清麗古曲,點綴著清風徐徐,浮云縷縷……似乎,不是這樣的圖景,就對不住這浸透心扉的禪語。
如果跌回現實里,這樣的圖景,幾近癡人說夢了。在喧囂繁雜中生活慣了,我們極少有“掬水月在手”這樣的情懷與韻味了。為了生存,我們總是讓身體在現世中不停奔波,讓心情在紅塵中不斷起伏,讓精神在得失中迷茫悲喜,我們恰恰忘記了,心靈最好的營養是寧靜,寧靜是心靈最喜最愛的境界。“水靜極則形象明,心靜極則智慧生。”唯有寧靜之時,才能傾聽靈魂之歌,才能靈光一現,掬一捧水而得月。
不是嗎?當青蔥男女由嬉戲打鬧轉為羞怯寧靜時,甜美的愛情要來臨了。當文人騷客由奔放高歌轉為憂郁寧靜時,傳世的作品要誕生了。當凡人百姓由奔波忙碌轉為安詳寧靜時,心與神要幸福契合了。
“人莫鑒于流水,而鑒于止水。唯止能止眾止。”莊子這里說的“止”,便是一種清澈見底的寧靜。止心如水,止水澄波,雜念、妄悲、喜怒哀樂一切皆空,是修心修道者奉行的方法,也是常人所追求的境界。
如果說“此時無聲勝有聲”是人生的妙趣,那么,寧靜超然則是心神來臨的永恒形式。黎巴嫩詩人紀伯倫曾經感嘆:“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而出發。”也難怪,置身滾滾潮流中,人難免會不由自主地被挾裹前行,又有誰能真正停下來思考紀伯倫之嘆呢?又有誰能停下來等一等落在身后的靈魂呢?
世界永遠是熱鬧的,熱鬧的生活是逃不掉的,世俗也是避不開的,心靜如水固然是有難度的,那么怎樣才能透過熱鬧享受其背后的無限廣袤與寧靜呢?最簡捷的方法可能就是讀書了。一冊在手,能穿越時空的束縛。智者哲人的低語,也許能引領我們摒棄浮躁,回歸自然。
“這么好的夜晚,寧靜,孤獨,精力充沛,無論做什么,都覺得可惜了,糟蹋了。我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燈前,吸著煙……”周國平先生的方式很空寂,煙頭火光明滅之間充滿了無限禪意,與“掬水月在手”有異曲同工之妙。
由此看,得月之法,遠不止一掬,就看你怎么悟了。
(編輯 慕容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