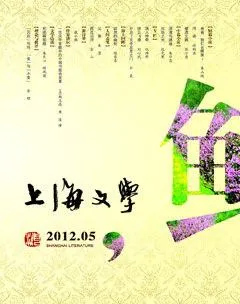開啟了文學反思之門
一
到現(xiàn)在,當我回憶起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時候,仍對那時的“思想解放”感到向往。這是只有經(jīng)歷了長期思想桎梏后的人才會有的感受,因為可以獨立思考,自由表述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真實看法了。用周揚的話,是要從“現(xiàn)代迷信”、“新蒙昧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哪怕僅僅是開始,還有相當?shù)闹萍s。在黑屋子里呆久了,當有了一點亮光,對那時人們來說卻是那么寶貴、慶幸和興奮!至于是不是足以稱為“思想解放運動”就是另一回事了。
那時的思想解放,可說是全社會的,各行各業(yè)都在議論紛紛。文學界的許多人也充滿著激情和期待,在進行回憶與思考。人們雖然呼喚“寫真實”,樹起了現(xiàn)實主義的大旗,使“傷痕文學”這樣的作品得以通行,幾十年來被打成毒草的文學藝術作品開始恢復名譽,但仍覺得許多歷史和理論上的是非沒有弄清楚。在探討和質(zhì)疑“文革”的同時,很自然地會與“文革”前的歷史聯(lián)系起來。在思考怎樣才能使文學藝術真正得到健康發(fā)展時,面前橫亙著毛澤東在1963年、1964年兩次對文藝工作的批示,經(jīng)過毛多次精心修改和增補審定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幾乎像三座大山仍然壓在人們頭上,成了不可逾越也不可回避的問題。如果仍還像有些人堅持的“現(xiàn)代迷信”:凡是毛欽定的都不能變,即使“文藝黑線專政”論可以不提,但“‘文藝黑線’還是有的,那就是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那么未來還有什么希望呢?
第一個寫文章公開批駁這種觀點的是張光年。他在1978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發(fā)表《駁“文藝黑線”論》,指出:“在這種說法的影響下,文藝界的一些冤案、錯案至今未得到徹底的平反,文藝上的精神枷鎖未能完全解除,文藝界很多同志感到惶惑不安。”張光年明確地說:“我是不贊成這種說法的,當時不贊成,現(xiàn)在也不贊成,因為它不合事實,經(jīng)不住客觀實踐的檢驗。”他在文中列舉解放后十七年來的文藝思想理論、文藝作品、作家隊伍等情況,認為是好的,有成績的,是執(zhí)行了毛澤東革命文藝路線的,而不是像‘四人幫’所污蔑的那樣執(zhí)行了劉少奇反革命修正文義文藝路線。那時前者被稱為“紅線”,后者被稱為“黑線”。他強烈地呼喊:“‘文藝黑線’之類莫須有的罪名,不僅是精神枷鎖,它首先是政治枷鎖,至今很大程度上束縛著文藝生產(chǎn)力。事關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命運,我們不能長期保持沉默。”
那年10月,張光年應邀到安徽合肥訪問,12月應邀到廣東訪問。所到之處所作演講、報告、發(fā)言,都是駁斥“文藝黑線論”。他的文章就是寫成于此時。可說這個時期他的思考就集中于此。因為這個帽子壓在文藝界的頭上實在太嚴重了。文章發(fā)表后,果然引起巨大反響。直到1981年2月,周揚在一次文藝界會議上還贊賞說:“張光年在這個問題上表現(xiàn)了勇氣,這仗不是容易打的。”為什么?我想,因為針對的是某些正在臺上掌握大權的人,還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龐然大物即毛的神像。
與此同時,羅蓀也寫了一篇批判文章,題名為《“文藝黑線”論必須推倒》。他用趙岳的筆名發(fā)表在《文藝報》1979年第1期,與光年的文章相呼應,配合得很好。他把文章先給我看看,要我?guī)退魄猛魄谩K麑懙煤苡袣鈩荩览砗褪聦嵳f得很充分。光年的文章交給《人民日報》排出小樣后,也曾給謝永旺看,要老謝也幫著推敲。老謝是光年多年信任的老部下,他也給我看,囑咐幫著推敲。我提了一個意見:光年為了要與劉少奇劃清界線,文內(nèi)有一小段話說,劉少奇沒有怎么管過文藝,與文藝界也沒有什么聯(lián)系,我們覺得他是個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人,不喜歡他這個人……我對老謝說:“這段可以不說。罵他干什么?焉知將來劉少奇的問題不會翻案?”老謝聽了覺得有理,就說:“你給光年去說說。”我說:“我不去說。他是給你看的,你覺得我說的有理,愿對他說你就去說。”老謝還是對光年說了,光年從諫如流隨著就刪去了。而劉少奇的問題直到一年后的1980年2月五中全會上才得以正式平反。從此劉少奇的“黑線”也就不了了之。
“思想解放”、“撥亂反正”固然舉步維艱,但有志之士都在勇于思考,敞開思想,破除迷信,沖破禁區(qū),說真心話,暢抒己見。突出表現(xiàn)在1979年1月18日召開的理論務虛會。這個會是由中央決定舉行的,全國有一百六十多人參加,前后長達一個月。鄧小平曾肯定稱:“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問題,總的說來開得是有成績的。”*這些問題其實都涉及到有關國家前途、命運的理論和實際,現(xiàn)實和歷史。會上思想活躍,解放的情況和談到的問題,常常通過馮牧等渠道及時傳遞到編輯部,對我們有極大的鼓舞和啟發(fā)。張光年的文章發(fā)表后的反響,也進一步激勵和引起我們的深思:被視為“文藝黑線”基礎的“黑八論”又該怎么看?“文革”十年以及前十七年的文學歷史應該怎么總結和認識?怎么把文藝界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引向正常、健康的發(fā)展之路。編輯部醞釀很久,決定召開一次“文學理論批評工作座談會”研討這些問題。
那時,召開這樣的會議不冠以“全國”之名,也就徑自召開了。其實參加者除北京外,還有上海、天津、廣東、江蘇、安徽、湖南、陜西、山西、湖北、黑龍江、吉林、遼寧,以及電影界、戲劇界和部隊作家、評論家、編輯、高校教師等等一百多人,自3月16日到23日,在崇文門向陽招待所開了八天會。有的人是會開起來后才來參加的,如有一次有人說到劉賓雁在社科院有一個發(fā)言,講得很好。那時“右派”還沒有平反,聽到他的動向就像聽到什么出土文物消息似的。羅蓀一點也不在意,當場就派人去找他,讓他也來參加會議。
馮牧在開幕時說:“像這樣專門研究文藝理論批評工作的會議已有很多年沒開,問題很多。”
馮牧介紹了理論務虛會上的一些情況。他和羅蓀發(fā)言中都提出,“就當前大家最關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展開討論:一是探討和總結三十年來文藝理論正反兩方面的教訓,包括十七年中文藝界幾次大的批判和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的爭論等等。二是當前文藝創(chuàng)作中涉及到的幾個重大問題。”馮牧列了一個詳細的問題表供大家參考。最值得注意的是深入聯(lián)系到“文革”前十七年歷史的反思,這正是大家所關注的。因為禍起于斯時,人們都有切身體驗。
會議開得很熱烈,思想也很開放,敢于提出問題說出自己的真實看法和疑問。對于“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藝工作議論紛紛,評估有分歧。有的說執(zhí)行了毛的革命路線,成績是主要的。有的說,毛是正確的,做工作的人執(zhí)行時有左的或右的錯誤。也有的說,特別是1957年后,左的錯誤是主要的,如“文藝界有七次大的運動,都是用階級斗爭形式搞的,造成極嚴重的惡果”。也有人至今認為這些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對此有人則質(zhì)疑說,那又怎么理解毛說的“基本上不執(zhí)行黨的政策”。
許多發(fā)言中,都對“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文藝批評是哨兵”、“文藝為政治服務”等等幾十年流行的基本觀點提出質(zhì)疑。上海的李子云系統(tǒng)地就這個問題作了發(fā)言。她在回顧了十七年的文學歷程后認為:“建國后不斷片面強調(diào)文藝與政治關系,把文藝當成階級斗爭工具,是不全面不科學的指導思想,對文藝創(chuàng)作起著多方面的有害影響。”諸如取消了文藝的特性,限制了文藝的多種功能,堵塞了文藝的豐富源泉。
錢谷融則專題談了人道主義、人性、文學是人學的問題,詳細闡釋了早在1950年代他曾發(fā)表過的也因此遭到過猛烈批判的觀點。他說:“文學既以人為對象,既以影響人教育人為目的,就應該發(fā)揚人性、提高人性,就應該以合于人道主義精神為原則。”“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階級所產(chǎn)生的偉大作品之所以為全人類所愛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為共同的基礎。”
人們還非常重視對三十年來文藝運動中許多復雜現(xiàn)象的探討,渴望弄清事實真相,作出正確的令人信服的解釋,對至今存在的許多創(chuàng)作和理論的禁區(qū)認為有待突破,對如何評價毛的文藝思想和《講話》也展開了充分討論。一些被誣為資產(chǎn)階級或修正主義文藝理論觀點如《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現(xiàn)實主義深化論”和“中間人物論”等冤案錯案要正本清源。文藝的真實性,人物創(chuàng)造的多樣性,揭示和批判社會生活陰暗面的作品……都應該受到鼓勵。對政治標準第一、暴露與歌頌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對領袖人物至今還在被神化提出了批評。認為“作家一切聽命于權力又怎能寫出好作品?”說生活是文藝的源泉,但真正描寫生活的真實面貌又不被允許反倒受批判。大家對幾十年來流行的文藝批評尤為不滿,說文藝批評變成鸚鵡學舌,看風使舵,涂脂抹粉;或是像法庭判決,不容申辯;或是按上面氣候風向?qū)懪u,說是哨兵,有時更像奴才、打手、憲兵。
劉賓雁說:“文藝界、新聞界被打成‘右派’的人很多,大都因為真實性即能否批判某些社會現(xiàn)象而引起的。”他認為:“1957年后,某些封建法西斯的東西開始萌芽,剝奪了社會主義文學與黑暗勢力斗爭的權利……文學的朝氣所余無幾了,大批人云亦云,沒有思想的作品出來了!”“最后,還是人民的力量將其逐步糾正過來。文學應該忠實生活,忠實人民的愿望。”許多發(fā)言中,特別支持文藝要做“人民的忠實代言人”,“文藝就是要為民請命”。
這些發(fā)言對十七年里把許多作家、作品和理論觀點打成“階級敵人”、“右派”、“毒草”等列舉了大量實例,認為“長時期來‘左’的危害發(fā)展到后來變成了‘左’的迫害,失去了大批有才華的作家,斷送了創(chuàng)作優(yōu)秀作品的機會”。“‘文革’時極左的文藝路線形成不是偶然的,正是過去十七年里‘左’的文藝思想、觀點、路線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會議中談及的問題和意見很廣很多,在今天有些人看來可能會覺得都是屬于意識形態(tài)、政治性的,非文學性的,似乎很多余。殊不知那都是從幾十年歷史實踐中,甚至包括了許多“血的教訓”、“慘痛經(jīng)驗”中總結出來的,所以要求從政治束縛中解放出來,直接關系到文藝的生存和發(fā)展。這些意見在當時可說是驚世駭俗,在某些人眼里幾乎就是離經(jīng)叛道的異端邪說,是“砍旗”,常常引述一些陳腐的教條來反駁、爭辯。如李子云的發(fā)言隨即發(fā)表在《上海文學》1979年第4期,以《為文藝正名》為題,署名為本刊評論員。此文引起了上海的高校文科、報刊以及文藝界的激烈爭論,影響所及北京和一些外地文藝界也有參與,就是很好的一例。可見人們都在關注、思考,十分認真對待。
可以說,這次會議開啟了文學反思之門,對前三十年的文學歷史和有關的各種理論問題幾乎都重新加以審視、探討,用歷史實踐來檢驗它的是非得失,不再為舊思維和偶像所束縛,而是充滿了批判的精神,顯得生氣勃勃。如果說,這是文學界的一次理論務虛會,或是已經(jīng)開了個把月的全國理論務虛會的一個分支,也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事實上也確實推動了文藝界的反思,諸如“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說法從此不再成為金科玉律了。過了一些日子,胡喬木也鄭重其事說,以后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了。
說到這里,我順便講一件半年后與此相關的事情。那是中國社科院(那時還稱學部)舉行國慶三十周年科學討論會。各個學科分成各小組開會,我參加了文學組。各組討論過程中不約而同地談到本學科與政治的關系,包括文學歷史哲學經(jīng)濟學等等為政治服務這個焦點問題上。據(jù)說無論哪個學科三十年來幾乎沒有一本學術論著可以不經(jīng)修改而繼續(xù)出版,其理論觀點至今還能站得住的。文學方面這個現(xiàn)象在這次《文藝報》召開的會議上就已經(jīng)觸及到了,開始反思了。
二
就在這個會議期間,周揚、林默涵、陳荒煤等文藝界領導人都作了長篇講話。周揚講話中,仍按照上面的口徑竭力維護“文革”,維護毛和《講話》,但告誡不要把后者當作教條。他肯定曾被當作右派代表性理論的秦兆陽《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是對的,承認對邵荃麟的批判是錯的。他還強調(diào)要保證“自由討論,藝術民主”,“沒有這些思想就會僵化”。
林默涵的講話引起了較大的反響,是這次會議中的一個插曲。和之前的一些會議上一樣,他仍以“文革”前文藝領導當事人身份講了三個部分:第一,回顧了文藝界的幾次大的政治運動或謂路線斗爭,多數(shù)都加以肯定,認為前十七年基本上執(zhí)行了毛的革命路線,但在工作中也犯了不少錯誤,有左的,也有右的。原因是對形勢估計錯了,與在社會主義時期對資產(chǎn)階級的認識和估計不足有關,而毛的所有批示意見都是對的。第一個斗爭是批判《武訓傳》,“現(xiàn)在看來是完全必要的”。文藝界對此沒有看出來,是毛提出來的,“這個批判證明我們思想是右的”。他還回顧了抗戰(zhàn)時在重慶,后來在香港,直到解放后連續(xù)批判胡風的詳細過程,說“胡風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推翻不了的”,“是鐵的事實”。批判胡風說的“寫真實”是因為他借此強調(diào)“要寫黑暗才算寫真實”,并沒有一概反對“寫真實”。他認為,“反右以前的斗爭可能也有過火的,但都掌握得比較好”。如對《武訓傳》,對俞平伯“都掌握得比較穩(wěn)”,《武訓傳》的編導演并沒有受沖擊。“反右”時就擴大化了,把大量知識分子當作資產(chǎn)階級,但又說保護了大批作家藝術家。毛所以“反右”是因為看到蘇聯(lián)變修給了他很大的刺激。對毛評價,“現(xiàn)在我們應該實事求是,有些問題要糾正,糾正了就不要再說了,完全沒有必要再說,如彭德懷冤案、天安門事件,做而不說,說過頭更不合適”。否則“老干部那里就通不過”。
第二,講文藝工作重點轉(zhuǎn)移。他強調(diào)要寫英雄人物是“重要的任務”。他本來就對“傷痕文學”持批評態(tài)度,這次又講“要防止感傷主義,那是腐蝕人的,對青年沒有好處。現(xiàn)在青年人受感傷主義毒害已經(jīng)很深了,會使人消沉下去”。
第三,講文藝批評問題。認為“‘為民請命’的提法值得商榷……對革命隊伍中的官僚主義等等要批評,但是不是要站在人民利益之上向黨和政府請命?不能把兩者根本利益對立起來,這樣很危險……在我們社會不能這樣講”。他也主張“提倡民主作風”,“要允許反批評”,“不要動不動就提到路線斗爭上來”,“不要隨便扣帽子”等等。
林默涵的講話引起了許多與會者的不滿和批評。對他講的十七年情況覺得與歷史事實不盡相符。如說批判《武訓傳》有理,政策掌握得比較穩(wěn)。事實上不僅編導演都一再受批判和檢討,全國各地凡與武訓有關的書、畫、報刊言論、教育家(如已故的陶行知)、出版者等等,無一例外都受到批判和株連,真可謂全國共討之。演員趙丹為此許多年沒有能演戲。這還算掌握得穩(wěn)?對俞平伯也是如此,根本沒有申辯的余地,也是全國共討之。林還全盤肯定批判胡風從言論追查到歷史,從批判發(fā)展到抓捕等,到現(xiàn)在他還在肯定毛的兩個批示,說是事出有因。回避十七年文藝工作主要問題是“左”的錯誤,及其在“文革”中得到惡性發(fā)展的事實。
許多與會者說,當前主要問題是解放思想還不夠,阻力太大。不要老是把社會上的個別負面事例與解放思想、發(fā)揚民主連在一起,上綱說事是“砍旗”;說老干部通不過,好像年輕人就分辨不清,沒有頭腦。林對當前文藝界包括指責“傷痕文學”有“感傷主義”的批評也難以使人們接受。江蘇的陳遼說,林說魯迅作品沒有一點感傷情緒就不符合魯迅作品的實際。文學作品有點感傷情緒有什么可指責的呢?
人們還對“為民請命”的反彈更激烈,說,當人民利益受到損害,人民受到壞人迫害時,為什么就不允許作家“為民請命”呢?彭德懷在1959年就是“為民請命”。現(xiàn)在上面有人提出要為彭平反也是”為民請命”。作家應該做人民的忠實代言人。
在對林默涵講話提出批評意見的人們中,陳遼曾作了專題發(fā)言。會后他回到江蘇,恰好那里正在召開全省文學創(chuàng)作會議。陳遼就應會議要求傳達了周揚、林默涵、陳荒煤、馮牧等的講話,引起了與會者對林的強烈反感和失望,又提出了許多尖銳的批評。
我曾冷靜地想過林默涵這樣的思想狀況:在經(jīng)歷了“文革”這場大劫難后,仍然把十七年看成理想的王國,繼續(xù)維護和肯定毛和那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維護已被歷史證明不成功的僵硬體制,不能反思和正視人民和國家所受到的嚴重傷害,結果只能隨著已逝去的歷史而去,未能作出有利于文藝發(fā)展和進步的建設性的貢獻,這是很遺憾的。因此,他在當時和隨后的日子里,和文藝界以及其他領導人存在思想分歧,多次發(fā)生爭論,甚至和劉白羽一起到中宣部部長王任重那里反映對周揚、陳荒煤、馮牧的批評意見,其中包括他抑悶已久的對“傷痕文學”的意見。
時隔兩年后,有一天我在沙灘大院遇見荒煤。那時他已在院內(nèi)文化部大樓上班,是分管電影的副部長。我們作協(xié)等單位在院內(nèi)原民主廣場上搭建的地震棚里辦公,所以有機會在院子里相遇。他的情緒很不好,問了我?guī)拙浣鼪r后,就憋不住說到近期文化部黨組開會,默涵老是盯著他,追問和批評他處理電影《苦戀》不執(zhí)行中央指示。荒煤很苦惱地說:“怎么不執(zhí)行?每次中央領導有什么指示,我都及時向黨組匯報的,都是按中央指示做的。他這么胡攪蠻纏,真叫人煩!中央指示每次我都記在本上。我準備把每次指示在黨組會上全部再念一次,哪一件事是不按指示做的?”我聽了很難過,覺得這些領導們做工作真為難,非常同情他們,但我們小人物實在欲助無力。
言歸正傳,仍說《文藝報》的會議開了八天,我負責大會的簡報組,組里還有唐達成、何孔周等幾位。我們一共編發(fā)了十九期簡報和陳荒煤的一個單獨講話稿。林默涵的講話稿也整理出nkox12kCLIUO9ThQ0WP9vG6TwaFDI17ai7uVmYC5fcc=來了,送給他本人審定。他退回時給馮牧、羅蓀寫了一封信,說:“刪去了一兩段題外而可能引起誤會的話,至于我的觀點完全保留。希望登簡報。聽說會上許多人對我的發(fā)言很不滿,逐條駁斥,我建議把他們的發(fā)言也原樣登簡報,這樣才能反映會議全貌,并使我知道我的發(fā)言錯在哪里……”他還說:“對這次會上的分歧,外邊傳說不少,聽說江蘇還有一份材料,對我進行討伐,可我一點不知道……這次會上談的,許多是方針性的重大問題,應該讓大家來討論……現(xiàn)在有些文章的旁敲側(cè)擊的做法是不好的,非同志式的。”他還要求把全部簡報通通發(fā)表。
默涵寫這信時已是4月17日,會議結束已經(jīng)二十多天了。所以,馮牧、羅蓀考慮后只能不了了之。至于他們?nèi)绾蜗蚰淮忉尩模揖筒坏枚恕倪@件事也可看出,那次會議是相當開放的,批評和反批評都是平心靜氣說理講事實。人們獨立思考的精神正在恢復,敢于爭論,敢于質(zhì)疑,即使長官的講話也敢提出批評意見。可能是我孤陋寡聞,也可能是我見識少,我不記得什么時候開會有過這樣的場面,對我好像還是生平第一次的經(jīng)歷。同樣,這樣民主開放的現(xiàn)象后來并不多見,不知是什么原因。
在我管簡報組時,還碰到過一件趣事。有一位青年學者在小會上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體系”這個說法提出質(zhì)疑,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有關文藝方面的論述就是一些信件,是“斷篇殘簡”,沒有專門著述構成體系。過了幾天,他忽然來找我,說想看看小組會的記錄是怎么記他的話的。我說:“可以,你去看吧!”他看完后又來找我說,記得不準確,要求刪去他的發(fā)言。我說可以,但問他小組記錄是不是有錯。他告訴我說,昨晚聽說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講話說要堅持VbekGPwQqoZXdqCCK3VdsSKWpZoQYCdbFpAz7Rd4pu0=四項基本原則。所以,他不想惹什么麻煩了!看來人們的政治神經(jīng)還是很脆弱,對詭譎多變的氣氛反應往往過于靈敏。
這個會議是在崇文門向陽招待所舉行的。這是為了組織各地干部民眾輪番來京瞻仰毛澤東遺容,分別在崇文門和宣武門專門建了向陽一所和向陽二所。人們住上一兩個晚上就完成任務回去了。后來瞻仰高潮過去后,我們就得以借此開會。這樓雖新建但設施比較簡陋,室內(nèi)除了三張床和一兩把桌椅就什么都沒有了。如廁要到樓道公用盥洗間。熱水每周開放兩天可以洗澡。我第一次見到王蒙就在會議期間。那天他剛洗完澡,頭上還正冒著熱氣,光著腳丫,只穿內(nèi)衣,像陣風似的沖進來坐在別人的床沿剪腳趾甲。室內(nèi)還有好幾個人,大家瞎聊一會,他嘻嘻哈哈地把我的年齡長相奚落了一番。我發(fā)現(xiàn)他是個開心的人,“大智若玩”。他那時在會上說話并不激烈尖銳。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在會上說,現(xiàn)在好像一口鍋破了,你若是把它砸了,那就什么都吃不上了。如果設法把它補好,即使鍋里只有粥,大家也還能吃上一口不至于挨餓。后來人們就戲稱前一種是“砸鍋派”,他這個是“補鍋說”。王蒙大概很愛吃粥,常常以粥作比喻,后來還寫過一篇小說就叫《堅硬的稀粥》,還引起一場風波。
這個會議開得很活躍,人們意見也不盡相同,對問題是非都有自己的認識和判斷,毋須什么人來做結論。理論問題、歷史問題不是靠權力可以一錘子定音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確實解除了多少年來束縛人們思想的枷鎖。其實,這不過是一個基本常識。我們年輕時都讀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論文,知道他說過,“‘實踐’是一切理論的無可爭論的試金石……”如今又聽到此話似遇故人,又似醍醐灌頂,清醒起來。不管怎么說,1978—1979年在中國肯定是一個值得懷念和研究的年份。《文藝報》在這半年多時間里連續(xù)召開的這些會議,推動了文學界的前進步伐,文學創(chuàng)作從此走上了一條與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不歸之路,在高揚“寫真實”和反思、探索的旗幟下,先后出現(xiàn)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知青文學”、“問題小說”、“尋根文學”、意識流—現(xiàn)代派……畸變紛繁,令人眼花繚亂。文學思潮也從為政治服務、崇高美、英雄傳奇……漸行漸遠,走向個性化、世俗化、平庸化,以至商業(yè)化……我想,現(xiàn)在這樣的狀態(tài)恐怕也是人們始料所未及的。
*參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78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