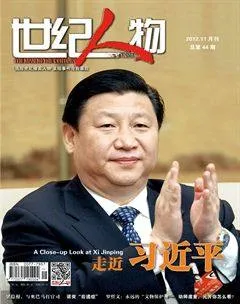感動了上帝的人
2012-12-29 00:00:00閻正
世紀人物 2012年11期








劉石平先生一定是一位用繪畫和作為感動濟源、感動河南、最終感動中國的人。
公元前3000年,所羅門國王曾說:“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無新事。”
我站在濟源太行蟒河口玉皇嶺上劉石平老人的“家”。猛然想起這句話,細細地品味著,在此之前,誰的境遇和他一樣呢?以前千百年里,有過他這樣的人和他這樣的事嗎?陶淵明?髡殘?八大?曹雪芹?都象又都不象!這些都是名留青史的人,是偉大的,而劉石平一點也不偉大,普普通通的平凡再平凡不過了。除了少數人知道他的名字,更早些時甚至一文不名,年近九十隱居深山,過著基本上原始的生活。
這是怎樣一位神秘人物。
劉石平是幸運的。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年紀輕輕就考進了當時中國最高的美術學府。“重慶國立藝專”,受教于潘天壽、林風眠、豐子愷、倪貽德、傅抱石、關良諸先生,與李可染、席德進、吳冠中、蘇天賜等師出同門。在今天看來,這一串令人高山仰止光芒四射的名字匯成的燦爛星河。當年的劉石平則沐浴其中,名師高徒,位列孫山,將他一生的摯愛做了最雄厚的鋪墊。
劉石平是不幸的。五十年代后期,正值如日中天大好年華之時,他被錯劃右派。從天堂跌進地獄,遭受了許多年不公正的待遇,在惡劣的政治環境里,他的名字徹底在人們視線中消失了,我翻看了最近大部分有關劉石平的報刊報道,都盡量不提這一段生活,或者蜻蜓點水一筆帶過,然后用一些美麗的詞藻,淡泊名利,甘受清貧啊;潛心教育,桃李天下呀等等輕輕掩飾,其實,在這段漫長時間里,劉石平遭遇了許多難以言云的屈辱與坎坷。這是那個時期中國大部分知識分子無可避免的命運。劉石平絕無例外。也正是那艱難困苦的年月,劉石平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腳,盡管沒有永世不得翻身,但當他重新回到“革命隊伍”的時候,早已是“無論魏晉,不知有漢”,物是人非了!
三十年前在濟源,我曾見過劉先生兩次,那也是搞什么展覽,其中掛有他的作品,混列在市縣級作品之中。既不突出也不醒目,如同他的為人一樣,既不多言也不多語。大家見個面,點點頭,握下手而已。一切都是淡淡的。我那時就聞聽劉先生的背景,當時來濟源也有不少“名家”,及個別的趾高氣揚,招搖過市,不知天高地厚的在劉先生面前稱大。其實按學歷資歷,大多該是兒子輩或孫子輩的。劉石平少言寡語,在當時以至以后的幾十年中,真個的“沉默是金”了!
我沒見過年輕時的劉石平,但我想他一定不是我見過時的樣子。是命運改變了他的一生使他變得無欲無求,與世無爭,終生孤苦一人。面對大千世界,他幾近銷聲匿跡。美術批評家范洪在推薦張伏山的文章中一開頭便寫道:“畫家張伏山先生的藝術,被社會湮沒多年,直到今天才引起社會的關注,在張朋、陳子莊、黃秋園、梁崎相繼被發現的今天,仍有許多卓有成就的大畫家,默默無聞,遺賢鄉里。這實在是我們的悲哀,也充分暴露了以前的文化體制存在的缺陷。”這里所指的默默無聞、遺賢鄉里的大畫家,劉石平又一個!在那一段漫長的歲月里,受盡人間凄苦的他,從不對人講訴他的過去,這也是所有采訪過他的記者們沒有記錄下他那段生活的根本原因。我與他匆匆見過幾面,亦不愿刻意觸碰他那不曾示人的痛處。起碼是對老人的一種尊重。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了,不必再提。近二十年來,這方面的描述太多,于事無補,不如放下,按一句時髦話講叫“向前看”。好在劉石平先生比陳子莊、黃秋園、張伏山幸運的多,直至今日還健健康康的活著,直至今日還揮毫不止!這就足夠了!誰說老人沒有愛?繪畫就是老人一生一世的摯愛,大愛無疆。他除去生病臥床之外,幾十年沒有離開過畫,有一個記者曾寫道:“劉石平又回到學校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他開始進入了創作的旺盛期。他每天早晨或課余都要到大街或集市上畫速寫。凡走卒、乞丐、老人、小孩都是他畫的對象……”這一段描述是真實的貼切的!但這時的劉石平只是為了愛去畫,決不是為了出人頭地或其他,他從苦難中走來,把全身心的愛都傾注在始自童年就酷嗜的繪畫上了。
劉石平先生自己講述:他從小愛畫京劇,正因為愛京劇,他的幼年,也就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正是京劇鼎盛時期,那時在濟源也有京劇,叫做黃戲。但縣里沒有劇院,有的都是民間自發組織的劇團,每逢節日廟會時常演唱,只要有機會,他總跑去看,從不輕易放過。
其實那時他只有幾歲十幾歲,哪里懂得什么叫戲,只能說是與生俱來的天性,為那些悅耳的唱腔,華麗的服裝以及火爆的武打深深吸引著,到了癡迷的程度。
正因為戲看多了,又聽大人們不時地講解,慢慢對戲里的故事也有所了解,什么鐵面無私的包龍圖呀、寒窯受苦的王寶釧呀!還有趙子龍、穆桂英、黃天霸等等、等等,舞臺上英俊的形象和優美的動作,深深刻進了他幼小的心靈里,每次看戲回來,情不自禁就拿出筆來畫,憑著記憶和想象去畫,畫著畫著自己心里美滋滋的,簡直是一種絕美的享受,于是畫京劇人物就是劉石平學畫的開始。
除了看戲,年畫京劇人物對他的幫助也很大。由于京劇盛行,京劇人物印刷品就應運而生,特別是年畫,無論書店市場都有銷售。他的父親經常買一些張貼在屋子里,給他的印象很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那時有一種名叫“哈德門”的香煙,煙盒里裝有京劇小畫片,彩色精印,十分美觀。他積攢了許多這樣的小畫片,時常拿出來把玩,愛不釋手,那是他學畫京劇人物的最好范畫,直至今日他還念念不忘“長坂坡”里趙子龍一手舉槍,一手拿馬鞭的英武形象。那馬鞭和槍什么樣,盔甲和靠旗怎么扎,靴子是怎樣穿,諸如此類,早在孩提時代他已是捻熟在心了。
隨著年齡增長,由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功課忙了,畫畫的時間少了,中學雖有美術課,畫的都是靜物、風景之類。后來抗戰興起,流亡在外,看戲的機會少了,在學校里無論課內課外,搞宣傳,出墻報,劉石平的興趣自然也轉到這一方面來,畫出了大量的抗日宣傳畫。
在我國繪畫領域里,歷代畫家所畫的題材大都是山水、花鳥,畫人物也都是高人雅士或仕女之類,似乎這才是傳承的正統。即使有畫戲曲人物的,如清代蘇州的胡三橋,也只是偶爾為之,鳳毛麟角,極為稀少。如此種種原因使他對京劇人物逐漸淡忘了。
然而秉性難移,劉石平對京劇的愛好始終沒有變,非但不變,且與日俱增,他不但學唱,而且學拉。在學校里,他與愛好京劇的同學們自發組織了京劇社,演唱傳統京劇,寫到這里我要代上一筆極有意義的小插曲。在“重慶國立藝專”,劉石平與李可染雖不同屆,但都是林鳳眠的得意弟子,所謂名師高徒,兩人都喜愛京劇,兩人都會拉京胡,兩人又都會唱京劇,在一次演唱會上,豐子愷先生的女兒豐一吟第一次登臺演出《王寶釧》,大受歡迎,還有一次劉石平在飯棚里看京劇《烏盆記》。扮演劉世昌的是鄒佩珠同學,后來成了李可染的夫人,而操琴的是李可染先生。李先生不但畫的好,那時他才知道李可染也是一位操琴高手。至于李可染畢業即留校任教,并成為我國畫壇上的大師巨匠那是后話,還有前面提到的吳冠中至今仍名揚海內炙手可熱。席德進畢業后去了臺灣,成為臺灣最負盛名的頭牌畫家。蘇天賜畢業后任教于南京大學藝術系,后任廣州美術學院院長,享譽藝壇。唯有我這篇文章的主人公劉石平,同是天字一號的資格與才華,一生困守“山城”。這山城不是重慶而是濟源。地利及天時、人和三項俱無。英雄暮年走進深山,不被人知,不被人曉,如不是幾位熱心的領導和朋友發現,如不是濟源市委市政府極力關懷搶救,劉石平這個人和他的名字以及他的作品就徹底湮沒在天蒼蒼野茫茫的大山之中了……
濟源市委書記段喜中、市長趙素平幾次和現常委副市長薛玉森到玉皇嶺上劉石平的家去看望并明確的說:“劉石平老人是濟源的財富,我們一定想方設法通過舉辦展覽,出版畫冊,讓老人的畫走出濟源,叫響全國。”
我第一次和濟源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李軍星坐在“劉石平藝術研討會”上暢談時,就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對老一輩藝術家關愛的決心和力度,晚宴時政協主席任傳國又反復詢問了劉石平老人的各方面情況,時隔一周,在濟源龍頭企業“予光”的支持下,“予光杯劉石平藝術作品展”在濟源大會堂舉行。濟源市國畫院同時成立,劉石平先生被任命為第一任院長。我與市委宣傳部李軍星部長,河南書畫院院長謝冰毅一同為展覽剪彩和畫院掛牌,感慨萬千。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聽到市委市政府的介紹匯報后也專門在濟源看望并慰問了劉石平,給老人帶來了極大的鼓舞。盡管是遲來的愛,但它宣告了劉石平先生新的生命周期在和諧的時代將邁出隆重的一步!
一個國家、一個省、一個市都有他的標志、象征和品牌。譬如國徽、天安門、華表是中國的標志,二七塔為河南的象征,那么劉石平就完全可以打造成一張濟源市的名片。以他的年齡、資歷和藝術上的成就,僅存于世的老一輩藝術家能與之匹敵的已寥寥無幾,有濟源市委市政府的全力舉薦,有廣大擁戴者眾星捧月的搖旗吶喊,劉石平先生苦盡甘來,必將為自己奏出最華麗的一章,劉石平這一生也不枉此行了。
有人成名是一幅畫、一支歌、一首詩,譬如羅中立畫“父親”,德德瑪唱“美麗的草原我的家”,未央寫“祖國,我來了!”一舉成名。有的人甚至一夜之間,譬如趙本山,春節晚會一個小品,名揚天下!
劉石平不是。劉石平是一生砥礪,一生磨練,一生修行,一生積累,所有這一切也都不是為了出名,是一種矢志不渝的興趣與愛好。我想起了諸葛亮,如果沒有“三顧茅廬”的故事,他只能是躬耕南陽,歷史上也就沒有了這個人物,諸葛亮的出山,其實是一種偶然。劉石平的出現,也是一種偶然,但沒有偶然性,就沒有歷史,常常偶然中帶有必然,劉石平重返畫壇,獲得他理應得到的了解與尊崇也在情理之中了。
我們不妨再回放一下劉石平心中早年的鏡頭:
從重慶沙坪壩穿過兩旁低矮的破舊民房,順著彎彎曲曲的石板小路不久就到了嘉陵江邊,渡過江,沿著山路再往前走,約摸七八里路,迎面山坡上豎立著兩座高大的石坊,上面刻著斗大的黑色行書字體“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走上山坡,穿過這個大門,只見前面不遠處綠蔭掩映下,一片黑色的瓦房,漸漸走近,還隱約聽到叮叮咚咚的鋼琴彈奏聲,這里就是抗戰時期由杭州藝專和北平藝專合并成立的國立藝專。
1943年秋,22歲的劉石平千里迢迢從河南家鄉來投考這個學校,有幸被錄取,當時喜悅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困難也接踵而來了,他帶的路費早已花完,家鄉淪陷,信息不通,沒有錢,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怎能入學呢?連續幾天都是向親朋借貸度日,但終究不是常事。記得有次一位好心朋友寫了封信讓他給一個人送去,意思是向那人借錢。劉石平跑了好遠好遠的山路,卻被婉言謝絕了,害得他整整一天水米未進,深秋時節,又冷又累又餓,筋疲力盡苦不堪言。
本來按國家規定,凡淪陷區學生可享受公費待遇,但要等上邊批下來才能付諸實施,為解燃眉之急,劉石平只得暫時放棄學業,謀了一份香國寺小學教師職位,以圖暫時糊口,不久國立藝專舉辦了一次師生作品展,琳瑯滿目的書畫布滿展室。有潘天壽、傅抱石、李可染的山水,關良的戲曲人物,劉石平趕去參觀,看后興奮不已,他想想不能再等,毅然辭去教師職位,前往藝專報到,恰好公費很快批了下來,盡管僅能解決吃飯問題,但已是喜出望外了。
劉石平在藝專是學習西畫,他們班的同窗如蘇天賜、劉頤勇、陳澤浦、譚訓鵠、李宣、何正慈、李承仙、梅先芬等。在后來的歲月里,其中幾位已成為中國美術界頂天立地的人物。
當時的教室就設在山坡前一片開闊地帶,房屋都很簡陋,是用竹子和泥灰做的墻壁。一排一排的,教素描的是廣東籍的胡善余先生。胡先生為人和善也很嚴肅,如果你畫得不好,他會嚴厲批評,然后再給你講。
畫素描用的是木炭條。用木炭條畫畫是可以打掉的。劉石平買不起好素描紙,只能用本地生產的土紙,為了省錢,他每次畫完以后就打掉再畫,或把紙翻過來再畫,如此這般一張紙就可畫三四次。開始畫石膏像,后來轉入畫人體,這對同學們來說非常新鮮,模特兒們男女老少都有,每當上課鈴一響,他(她)們就到教室把衣服脫光,在指定位置上擺個姿勢就開始畫了,冬天也一樣,那時沒有暖氣,只是把模特兒兩邊放個火爐,這樣要堅持一個課時。西畫主要科目是油畫,所有油畫用具劉石平根本買不起,只好暫時借用同學們的,說實在話,劉石平當時除了吃飯是公費外,平時連一文錢也沒有。冬天里也常常穿著草鞋,多虧一位貴陽的親戚和朋友們接濟,才勉強可以度日。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在來信中鼓勵他:“不要向困難低頭,要學宋士杰告狀,走著說著!”這句話讓劉石平銘刻在心,一次次刻苦振奮,度過了難關。
學校的寢室是在離教學區不遠的一個大院里,他住的那座房間橫七豎八放了許多雙人木板床,他睡上鋪,上下很不方便,同室都是外班同學,很陌生孤獨的劉石平常常趴在鋪上想家,做惡夢。
這院子后面是廚房,緊接著一個大飯廳,所謂飯廳無非是一個竹子加茅草蓋的大棚,每到開飯,許多大木桶盛滿了飯,你自己去舀,平日多是大米飯,飯里有很多草籽,每周改善兩次,四川人叫“打牙祭”,這時可以吃到肉,面條、饅頭什么的,是劉石平最高興的時候了。
當然,除了緊張的學習,也有娛樂。那就是唱京劇、演話劇或舞蹈歌曲。他們演過曹禺的名劇《日出》,導演是李樸園先生,當時在重慶的次坪壩連演十余場,場場客滿,轟動一時。
人生是那樣的微妙神奇與不可捉摸。當年在這快樂圣土上的藝術家,經過了一個甲子的歲月變幻,有的成了新中國建國以后舉足輕重的大師泰斗,有的流走海外成為某國某地區的一代宗師,有的改弦更張去做了別的,林林總總但大部分已不在人世,至今健在如劉石平者形單影支,隱居深山,遠離世俗,無名無利,仍在拉著京胡,唱著京劇,畫著自己的摯愛,恐已是這世界上的唯一了。
2000年剛過,劉石平得了一場大病。在恢復間隙,老人由侄兒劉鴻喜陪同到城外山里轉。走到蟒河口玉皇嶺上,忽聽有人唱京劇《霸王別姬》,對于酷愛京劇大病初愈的老人來說,這唱腔音樂猶如天籟之音,他愣住了,大山里怎會有人唱京劇?循聲而下,竟發現一位老農在放錄音,這老農叫宗福元,是一位經歷過上百場戰役的老戰士,解甲歸田,隱居山林。宗福元子孫滿堂,卻喜歡獨自居住,自食其力,每天在山上山下忙碌。雞鳴即起,日落而息,老人樂呵呵的說:“一年打的糧食三年也吃不完,還是勞動最幸福,最愉快!”老人種樹成癮,二十多年來,他把玉皇嶺上下整整披上了一層綠裝。宗福元也喜愛京劇,劉石平大他五歲,兩位老人攀談之下,相見恨晚,瞬間成了知己。宗福元邀劉石平來山上住,劉石平也正有此意。宗福元騰出一間房子作為劉的畫室,很快劉石平就搬進山中。說來也怪,原先劉石平睡前總要吃幾片安眠藥,然而進到山里之后,每天都睡得非常安穩,身體也日益健壯起來。
原先宗福元買不來京劇磁帶,劉石平那里很多,都隨他帶上了山,濟源常委副市長薛玉森聽說劉石平住進山里,馬上趕去看望,并專門派人去為他修繕了房屋,兩位老人說在山里不通有線電視,薛玉森隨即又指示有關部門為他們安裝了電視接收器,現在兩位老人可以自由自在地收看戲劇頻道了。
嗣后的歲月里,劉石平與宗福元相依為命,相得益彰,生活充滿了和諧歡樂。用劉石平的話說:“這里雖然條件很差,但山清水秀,風景優美,他種地我做飯,一個擔著挑子能上能下,一個拿起筆來能寫能畫,他吃了飯去勞動,我上午畫畫,午休后看書、養花,晚上一起看京劇碟子,生活愜意得很!”有的記者采訪時打趣的對一身泥土的宗福元說:“你看劉老師穿的多干凈。”宗老漢笑起來:“我整天和泥土打交道,人家是畫家,性質不一樣。”宗老漢最高興的是自從劉老師搬來后,這里一下子熱鬧了,每個月都會有一群京劇票友追到這里來,讓劉老師拉弦過戲癮,每到這時候他就不去干活了,跟著劉老師一塊過戲癮。
市委書記段喜中聽說劉石平京胡拉的不錯,也曾在看望老人時讓老人來一段。劉石平轉身取下掛在樹上的京胡,歡快的曲調在大山中震蕩起來,老人的侄兒劉鴻喜脫口隨著琴聲開唱,隨后,劉石平又自拉自唱了一段《紅燈記》,贏得了陣陣掌聲,余興未盡,段書記又隨老人來到畫室。劉石平乘興揮毫,瞬息之間,一幅“蘇三起解”躍然紙上,令大家嘆為觀止。
這就是老人的晚年生活,一幅歡樂祥和的田園風情畫,兩位老漢盡可貽養天年了。
然現實并非到此為止,如若那樣也不必我浪費這許多筆墨了。
劉石平是一座藝術金山,屬于自己也屬于社會與國家。我們如今開采他挖掘他,決不是要打破老人安詳而平靜的生活,老人盡可永遠在大山里住下去生活下去,但老人的藝術經歷了一個甲子的鍛造、錘煉,已達到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境地,也應該讓世人知道,讓世人了解,不要悄無聲息地埋沒在大山里。這其中有兩個人功不可沒,這兩個人一個叫王錫柱,一個叫任再錄。
任再錄是濟源當地一個中學的黨支部書記,喜好京劇,酷愛劉石平的畫,多年來在老人生活困苦的時候,經常資助老人,實實在在幫了不小的忙,老人出于感激,也為他畫了不少的畫,這都符合中國傳統的禮尚往來,在艱難的歲月,老人沒有什么可以回報的,秀才人情紙半張,只有送畫了。今天人們也許會說:“任再錄這家伙太聰明,太有眼了!”我要說聰明也好,有眼也罷,那就是任再錄。善惡有報,任再錄正應了理所當然的福份!
至于王錫柱,曾是濟源三十年前的宣傳部長,按說是我的老領導,后調沁陽任常務副市長,人大副主任,今年七十開外早已退休。前年他帶了個苗大壯找我,要我收做學生,我說:“濟源有個劉石平,那是多大的畫家呀!干嘛找我?找劉老師啊!”我這位老領導就認真的把孩子送到了山里,一開始劉老似乎并不愿意,過一段時日,覺得這孩子挺不錯,也就留下苗大壯做了關門弟子。王錫柱與劉石平交往越多,就越覺得老先生鳳毛麟角,非比尋常,便決心為老人奔走呼號,不能讓一位大師級畫家就這樣被隱埋深山了,任再錄和劉鴻喜自然而然充當了王老奔走的左膀右臂。而劉石平老人此時依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對三個人的舉動不置可否。冬去春來,他們不斷地往返于北京和幾個城市之間,單是我的家里他們自己都說不清跑過多少趟了。一開始我激動著又猶豫著,劉老先生本身是金近足赤,絕對堅挺。問題是天下之大,頭緒之多,不是我們這些百無一用的書生可以吹動風的!然而,禁不住王錫柱這位老市長的執著、誠懇、無私無畏,我靜下心來想,他圖什么呢,圖名?沒有他的,圖利?更談不上,這正是一個退休老人的博大胸懷。同時,我看到了濟源市委市政府的堅定態度,于是義無返顧地和他們融在了一起。劉老先生終也開始配合,回歸三界,走進五行中來。
這是一批感動了上帝的人們。首先是劉石平本人,再有市委和四大班子的領導們,還有廣州軍區首長李曉剛、安陽市常務副市長陳明,當然也有沁陽老市長王錫柱,再有苗哲、李中偉、姚天征、閻雅琴,原聚文、任再錄、劉鴻喜、徐衛偉、盧曉更、馮淑娟等等、等等,所有這些為劉石平吶喊幫助過的人,他們感動了我,也感動了我身后更多的人。我堅信待大山之外都知道劉石平之后,一定會感動整個中國的上帝,甚至全世界。
文字收尾的時候,我想起了百年戲魂翁偶虹先生,翁先生名票出身的大劇作家,一生寫戲無數,如《鎖麟囊》、《紅燈記》、《將相和》、《野豬林》、《生死牌》、《李逵探母》、《夜奔梁山》等。在當今中國經常上演的劇目中,他的劇本超過了三分之一。我覺得劉石平與他有點相像,翁先生寫過一篇《自志銘》,容我抄錄如下:
也是讀書種子,也是江湖伶倫,也曾粉墨涂面,也曾朱墨為文。
甘做花虱于菊圃,不厭蠹魚于書林。
書破萬卷,只青一衿,路行萬里,未薄層云。
寧俯首于花鳥,不折腰于縉紳。
步漢卿而無珠簾之影,儀笠翁而無玉堂之心。
看破實未破,作幾番閑中忙叟;
未歸反有歸,為一代今之古人!
我寫著想著,這銘文不也正是在說劉石平嗎?何等近似,何等相象!劉石平老人,好一個泰山北斗,好一個閑中忙叟,好一個今之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