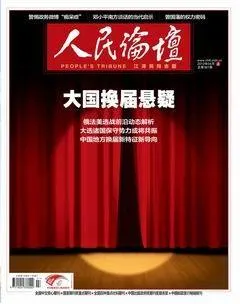陌生人社會的政治圖景
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人行動的解放。一方面,人們越來越不受神學的、階層的、教條的羈絆,日漸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貨幣逐漸符號化、象征化,這就讓人們可以自由地離開自己的出生地生活,可以自由地跟不同地域的人們做生意、打交道。
人們常常看到觀念和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但卻忽視了自由流動時代帶給社會的關鍵性影響。
這種人口的大流動帶來的移民政治圖景是嶄新的。吉登斯所說的那種風險社會的色彩更加濃厚了,人們日益依靠所謂的“抽象系統”來獲得安全感:大家更相信管理體制和規范的可靠,而不再信賴人格、名聲和地位。“質疑”變成了一種廣泛的社會心態。四顧茫然的生活意識注定了人們會喜歡那些沒有組織性的組織活動。從Facebook到微博,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們聚集在網上,用無害討論的形式來嘗試消除社會公害的可能性。責任感變得與道德感無關。美國文化中大力強調家庭和社區的價值,好萊塢電影不斷渲染為家人犧牲的神圣感。只要對親人負責,就是對自我生命價值的最高肯定,傳統社會中其樂融融、小家大國的倫理道德價值感,逐漸被悄悄掩埋了。
簡單地說,中國社會開始進入了這樣一個嶄新的時期:我們必須通過更好地跟陌生人相處,才能更好地活下去;同樣,一個社會的內在力量是通過聚集了大量陌生人而實現的。這就是所謂的“陌生人社會”。
早在上個世紀初的英國,威廉斯等人就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在那個時代,這個問題還是局部的、社區的,還屬于恩格斯所描述的那種屬于工人階級的。盡管如此,威廉斯也認識到,如此眾多的產業工人聚集在一起,立刻就會出現一個如何教育和引導的問題。換句話說,現代社會建立在一個陌生人聚集所養成的新的文化體制和政治體制的基礎上,也就需要面對諸多新的問題;而其公民則需要一套新的法則和制度來進行制約和引導。
在這里,陌生人社會的核心特征,就是個人的自組織性空前提升,“節制”、“責任”、“風險”、“隱私”、“民主”、“權益”等,立刻變成了現代人生存的關鍵詞。與之相應,族群的倫理組織能力則明顯降低了,人們把與他人交往的一切問題都拋給了社會管理體系。于是,“凡是與自己無關的,就一定是歸社會管理的;反之,凡是社會組織管理的,就一定是與自己無關的”,這個生存法則滲透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陌生人社會變成了一個難以信賴他人的社會,也就反而越是吊詭地變成了人們日益依賴的抽象系統社會。陌生人社會設計了復雜的規則系統來合理管理人們的生活,反過來,這個系統已經復雜到了讓人們只相信程序、不相信結果的地步。
所以,陌生人時代的社會政治,必然是一種嶄新的政治:它對傳統的政治形勢的依賴日益降低,人們越來越不愿意信賴別人,而越來越喜歡信賴程序;與之相對應,人們不再從情理社會角度重視政治治理,而是從法理社會角度重視政治功能。講究感染力的政治管理方式,那種榜樣的、楷模的、激情的與道德的規訓,不再起到核心的召喚作用。人們比以前更加挑剔政治管理者,更容易走上街頭或者聚集于社交網絡,表達自己的懷疑。
懷疑,必然成為陌生人時代中國政治管理的主要對手。即使執政黨做得再好,還是會處處有不信任——因為生活在一個陌生人的環境中,人們自身權益得到保障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毫不猶豫地依靠政府部門和政治管理。
總而言之,國家—社群—個人,這種傳統的三方關系已經破壞,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矛盾緩沖帶消失了,這正是陌生人時代中國社會政治面臨的新局面,如何研究和應對這一局面,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課題。
(作者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責編/李逸浩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