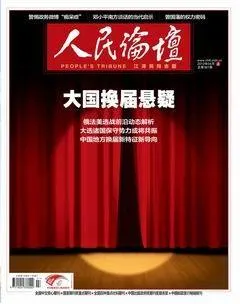當前幾個熱點問題走向思考
* 國有企業應當從競爭性行業進一步收縮,在非競爭行業特別是大型自然壟斷性行業要進一步轉變經營機制,與其他行業平等競爭。但不能私有化
* 在一個具有“不患寡,而患不均”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中國,貧富差距的過度擴大,必然會引發社會的不穩定
*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市場經濟需要法律的治理,更需要道德文化的約束
* 從長期來看,推出房產稅,努力構建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促進住房價格合理回歸才是最為基本的
國有企業改革的下一步是否要私有化
近日,世界銀行一份關于中國未來20年發展的研究報告引起了極大爭議,該報告稱我國經濟在經歷高速增長的30多年后,已經進入了一個轉折點,需要進行一次根本性的戰略轉變,并特別強調要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一時間,國有企業改革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國有企業改革,歷來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從“放權讓利”到“承包制”,再到“現代企業制度”,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路由經營層面的激勵機制逐步深入到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從“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到“抓大放小”、“國退民進”,再到“公有制占主導地位,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無不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國有企業地位和公有制內涵的新認識。
當前,國內幾乎占主流的聲音都在批評國有企業,指責其效率低下,與民爭利,并成為貧富差距的助推器。而所有問題的癥結在于國有企業所擁有的“天然特權”,如低資金成本、低土地成本、高補貼等。因此,改革就必須打破既成的所有制結構,消除對國有企業的優待,實行私有化。如吳敬璉、茅于軾、張維迎、陳志武、許小年等一批主流經濟學家。易憲容的態度比較折中,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式可多樣,私有化也是其中可以選擇的一種。而林毅夫則堅決反對私有化。
主張私有化和反對私有化的爭論從來都是如火如荼、勢不兩立,但稀有把私有化的概念明辨清楚的,使得這種爭論成為自筑理論營壘、誰也說不服對方的僵局。這里的關鍵是要把關鍵詞“化”辨析清楚。
要辨析“化”字,可上延到20世紀50年代,50年代中期黨和國家的戰略任務是“一化三改”,這里的“化”是指工業化,“改”是指對農業、手工業、準備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50年代后期實行人民公社,稱之為“公社化”。199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又有人簡稱為“市場化”改革。當我們大力發展私有經濟時,又有人鼓吹“私有化”。縱觀我國半個多世紀的歷程,往往與“化”字結下了不解之緣,又帶來了一次次危害,還是要咬文嚼字反思和推敲一下這個“化”字的內涵了。“化”者,即“轟轟烈烈、全部、快速實現”某個目標也。其結果呢,眾所周知,沒有一次“化”好,每一個“化”都后患無窮,過去的“化”都成為后來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今天我們要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收縮國企規模,積極發展非國有經濟,也該理性一點,謹言“國有企業私有化”。
不搞全盤私有化,是中國模式成功的重要基石之一。從提高效率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并不意味著全盤私有化,而在于內部治理結構的優化。為此,我認為可做以下三方面調整:其一,國有企業的定位首先應該是獨立的企業,對于國有企業而言,要逐步甩掉歷史上國家所賦予的沉重包袱,全面走向市場,真正做到“自負盈虧”。其二,在中國,并不存在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社會經濟條件,即便是席卷世界的非國有化浪潮,也并非是全盤私有化,而是對原有國有企業進行多元重組。對于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而言,要尋求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型產權制度。其三,在產權明晰的前提下,要繼續完善國有企業的內部分配機制,全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解決激勵不相容、責任不對稱等問題,借此來引導國有企業揚長避短,提高效率。
縮差共富下一步如何多條腿走路
對于如何解決我國的貧富差距問題,不同的專家和學者,提出了很多見解,如有些學者認為要完善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有些專家指出可征收富人稅,等等。我認為,僅從這些方面入手,并不是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有效辦法。從縱向來看,我國的貧富差距問題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新中國成立后先工業化的經濟趕超戰略,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的改革開放戰略,以及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都對當前的收入分配格局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并導致了收入分配在城鄉、地區、行業,以及職位之間的差距。因此,解決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需看清導致其出現的歷史因素,在此基礎上,多頭并舉,從以下四個方面同時入手。
首先,對于城鄉收入差距而言,既有普遍性,又具特殊性。其普遍性在于,無論是發達的東部地區,還是561a707e9028f4ff5c599a4abe078e72較為落后的中、西部地區,都存在這一問題;其特殊性則在于,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在西部地區最為突出。這也就意味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要著眼全國,更要突出重點,在加快發展農村經濟社會事業的同時,有重點地加大國家對于西部農村地區的扶持力度。
其次,優先發展東部、先富帶動后富的改革開放戰略,雖推動了國家經濟30多年來的高增長,但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在地區間的差距。近年來,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東部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都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在今后,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統籌區域發展為基礎,全方位縮小地區收入差距。在今后,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統籌區域發展為基礎,通過統籌東西部地區經濟的同步協調發展,來全方位地縮小地區收入差距。
再次,行業間的收入差距,也是造成貧富差距懸殊的重要因素之一。從市場結構上來看,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以石油、電信、銀行、證券等為代表的壟斷行業,與紡織、制造、手工業等為代表的非壟斷行業之間,在職工的收入上一直存在著很大的差距。為打破這種不合理的格局,必須加大力度促進行業間協調發展,進行宏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縮小行業收入差距勢在必行,特別是對特殊行業更加應當有專門的法規和政策予以限制和規范。而縮小行業間收入差距的關鍵,在于宏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最后,從職位上來看,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在企業內部,管理人員與普通職工之間,在收入上的差異愈加明顯。這本也無可非議,但是在一些上市企業,高管的薪酬甚至高出職工百倍,這無疑偏離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當前,應從微觀層面來推動企業內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扭轉這種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
怎樣走出行業道德淪喪的“囚徒困境”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司法、立法和法規建設不斷地向前推進,與此同時,各類違法行為卻不斷地與司法、立法和法規建設賽跑,使得許多法律規范成為一紙空文。在我國食品安全立法和司法不斷健全的當下,蘇丹紅、瘦肉精、地溝油、假雞蛋、毒奶粉、毒大米、染色饅頭等一系列惡性事件大行其道,沖擊著人們的心理和生理底線,揭開了更多行業道德缺失的所謂“潛規則”,以至于溫家寶總理感嘆“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從理論上來說,我們必須正視市場競爭的二元本性。市場經濟是以自利激勵為基礎的競爭性經濟,自利心的合理張揚可以在一個時期帶來經濟繁榮,但私欲的無限泛濫則必然給社會造成長期的無窮災難。在社會分工高度發達的今天,如果一些企業生產的“偽劣”甚至“有毒”產品得不到有效治理和抵制,最終各行各業的生產者將陷入“囚徒困境”式的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