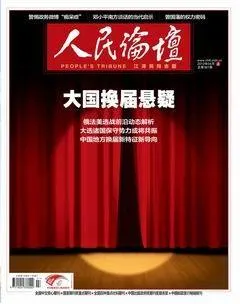鄉村價值世界“淪陷”之憂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我國農村的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與此相伴的是,傳統農村的價值世界領域也發生了深刻變化,農民的價值世界出現了“淪陷”和“撕裂”,尤其是在體制深刻轉換、結構深刻調整、社會深刻變革的轉型期,表現尤為突出,必須采取措施予以解決。
道德力量衰落
傳統農村是農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單位,人們在長期的共同生活和頻繁互動中,建立了親密關系和相互的了解、信任,形成了共同的習俗慣例、規范和道德觀念,從而構成了支持這些非正式社會規范運行的輿論環境。其實這些均可歸納在道德的范疇之內。這些道德范疇通過社會化的途徑滲透到農民的內心深處,成為他們行為和意識的一部分、成為約束農民行為的道德力量。如果有人逾越了自己的位置與角色所“規定”的行為邊界,就會被認為是行為越軌而受到村莊普遍的輿論鄙視并承受著心靈羞愧的懲罰和自責。
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滲透,隨著“村莊共同體”被打破,村莊逐漸成了陌生人社會和半陌生人社會,利益原則成了鄉村社會關系中的一個重要緯度。先前鄉村社會既有的行為范式、價值觀念被普遍懷疑、否定,或被嚴重破壞,逐漸失去對社會成員的影響力與約束力,從而使得社會成員產生存在的意義危機,行為缺乏明確的社會規范約束,呈現某種紊亂無序狀態。諸如:自我價值的認知完全趨于利益化;村莊不再有共同的榮辱、是非、對錯、善惡的判斷標準,不再有地方性的共識、規范和倫理。農民們現在可以逐漸不再受道德力量的約束,不再受鄉村道德輿論的譴責,可以臉不紅心不跳地干許多違反鄉村道德規則卻不一定違反法律的事。
人情關系異化
人情關系是人的一種內心深處的需求和精神的寄托。傳統農村人情往來是鄉村社會關系的重要特征,它以血緣、親緣和地緣關系為中心,使每個農民及其家庭形成特定的“人情圈”。改革開放后,利益因素的侵入已在不斷地侵蝕著鄉村社會人情關系中的感情因素和親密感,農民們逐漸以物欲化、工具化的角度來看待人情關系,基于社會交換中的情感支持、互惠規則的人情關系逐漸變得麻木、冷漠,村民間基本的人際互動難以維系,導致了鄉村社會村民間的信任危機,其反過來又促使鄉村人情關系更加疏離。
此時的人情與人情關系已失去了人情的本真意蘊,由人們自由、自主的本質活動而蛻變成為一種被迫的、扭曲的、片面的活動,一種人們用以謀生、維持生計的手段。異化或物化了的人情交往活動不僅失去了屬人的自由的本質特征,而且使得人情關系變得更加勢利、冷漠、虛偽而世故,從而也就部分喪失了人情所應有的價值。農村熟人社會實質上已處于“解體”的狀態。
民俗傳統消失
傳統民俗是鄉村特有的文化遺產。民俗是一個民族尤其是農民的精神圖騰,其發揮著巨大的整合功能,承載著村民的精神歸宿和身份認同。人們在這樣的活動中找到了自身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拜金主義的盛行,人們關注于金錢和利益,傳統民俗的生存空間急劇縮小。尤其是隨著大量勞動力的外流,農村空巢化突顯,其實質是農村成人的集體缺席,加深了農村的民俗危機,許多民俗儀式如各種生活儀式(喜宴儀式、婚禮儀式、喪禮儀式)、各類手工制作(臉譜、木版年畫、剪紙、刺繡、草編、面花、紙扎)、鄉間(藝人)技藝絕活、表演評論等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再也找不到傳承的對象。民俗的流失在不斷地吞噬著農村的生存環境尤其是人文環境。
可以說,隨著鄉村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公共精神的喪失,農民們沉溺于對物質與利益的追逐,已經不知道用什么價值來統領他們的精神世界,農民的精神逐漸無處可依。這不僅極大沖擊了傳統鄉村文化的地位,并使在鄉村社會中產生具有同一性、穩定性和持續性的價值體系逐漸“瓦解”和趨于“崩潰”,使其越來越失去自身的意義而走向消亡,內聚力消弭,村莊也越來越成為一盤散沙。
同時,城市文化則通過各種“壓迫式”的方式和“短、平、快”途徑不斷向鄉村社會灌輸自己的文化理念與精神,改變著鄉村社會的價值理念與存在狀況。當“一切向錢看”或者是“一切用錢來衡量”成為一些人所信奉和堅持的價值準則時,農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居住狀態、人際關系甚至語言習慣都在潛移默化地發生變化,他們越來越無法在鄉村社會找到家園感、歸屬感、依賴感和生存價值。這導致鄉村社會逐漸陷入紊亂無序狀態,不利于和諧農村的構建。有人說,“一旦農村無法呼吸,那么城市也將窒息”。因此,必須對此予以重視。
(作者單位:國家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