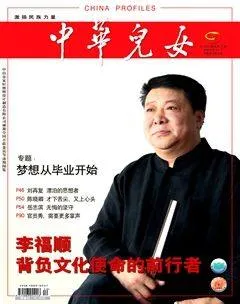胡圣虎 歸去來兮北大“狂生”
2012-12-29 00:00:00劉之昆
中華兒女 2012年12期



導(dǎo)語:十年后,胡圣虎從部隊轉(zhuǎn)業(yè)回到湖北,任職省直機(jī)關(guān)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似乎從這時起,他才真正畢業(yè),踏入社會,開始自己規(guī)劃人生
主句:機(jī)遇與命運(yùn)卻不像胡圣虎所言。他認(rèn)為只能修身的冷門專業(yè),在某些特殊部門卻成了急需的人才,加之胡圣虎世代“赤貧”的出身和出眾的成績,1987年畢業(yè)后他先去了外交部,繼而參軍入伍,分配到軍隊特殊要害部門,做了與他所酷愛的書法毫不相干、但卻與所學(xué)專業(yè)密切相連的“機(jī)要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十年。
1984年10月1日,國慶35周年天安門廣場閱兵式后,舉行了盛大的群眾游行。當(dāng)北大的隊伍行至天安門廣場時,兩名學(xué)生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標(biāo)語,此舉震撼人心,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此標(biāo)語的書寫者,正是時為北大東方語言文學(xué)系大三學(xué)生的胡圣虎。
燕園才子有狂名
1982年高考文科外語類招生時,出臺了一項新政——不考數(shù)理化,只考外語、語文、政治、歷史和地理。偏居湖北省仙桃市毛咀鎮(zhèn)的高三復(fù)讀生、文學(xué)怪才胡圣虎因為這項政策而創(chuàng)造了奇跡。由前一年只夠上中專的成績一躍成為1982年全省文科外語類第一名。被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學(xué)東方語言文學(xué)系錄取。
消息傳來,整個村莊沸騰了,縣領(lǐng)導(dǎo)也十分激動,鄉(xiāng)村中學(xué)首次冒出了全省高考狀元,當(dāng)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財政撥款四十大元重賞。胡圣虎說他像一個在夢境中追逐彩云的傻孩子,今天可以駕著這朵彩云去北京了。
北大無疑是中國知識界的精神燈塔。1982年9月,胡圣虎走進(jìn)北大校門,心中的那份神圣與自豪不言而喻。記得剛?cè)胄r,系主任季羨林,老教授金克木等都親自來看望他們,慈父般師長們的問長問短,讓他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頭。
他忘不了就在入學(xué)當(dāng)年三個月后,一股寒流突襲北京,一些南方來的貧困學(xué)生在瑟瑟寒風(fēng)中病倒了。季羨林等老教授心急如焚,他們紛紛捐款,買來了洋布和棉花,并組織大家通過自己的勞動來獻(xiàn)愛心。從小跟著兄長做過裁縫的胡圣虎輕車熟路,大顯身手,把自己的做好了,又指揮班里的十位女生為貧困學(xué)子縫制了十余件棉衣。
棉衣雖出自胡圣虎等人之手,卻飽含著老教授們的關(guān)懷和一片心意。這種“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的情感,叫北大學(xué)子難以忘懷,并把它變?yōu)橐环N“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的巨大力量。
在北大的5年(東語系比別的專業(yè)多一年),他在知識的海洋中遨游,最令胡圣虎驕傲的是,他是當(dāng)時在圖書館呆的時間最長的學(xué)生。他知道什么樣的書分布在哪個館里,哪本典籍放在書架的哪個部位。每到周末,他買上幾個饅頭,早上進(jìn)館,晚上出館,去得最多的是三樓東面的那間古籍室。那里全是善本和工具書,很少有學(xué)生去那里,在那里他卻有大快朵頤的快感,他在這里碰到并結(jié)識了朱光潛、宗白華、鄧廣銘、吳小如等名教授,并與他們交上了朋友,不懂就問他們,邊學(xué)邊問,常學(xué)常問,不恥上問,于是肚子漸漸鼓了起來,將很多教授都不放在眼里了,在北大漸漸就有了“狂”名。
八十年代初期的一個晚上,幾名研究生相約來到社科院錢鐘書先生家,還是大二生的胡圣虎拿著根一尺多長的竹笛,也緊隨諸師兄之后。眾師兄將所研究的課題一一向錢先生匯報,錢先生也將眾生應(yīng)讀書目一一列出。輪到胡圣虎了,他指著手中竹笛說:“我是研究樂經(jīng)的。”錢先生見胡圣虎年齡小,個兒也小,故意開玩笑,“月經(jīng)?那是醫(yī)生的事呀?”眾師兄哄然大笑。但胡圣虎一本正經(jīng)侃侃而談——
剛才眾師兄向錢先生請教了四書五經(jīng)方面的情況,但中華元典是“四書六經(jīng)”,對第六經(jīng),也就是“樂經(jīng)”,古文經(jīng)學(xué)認(rèn)為,樂毀于秦火,我認(rèn)為這是站不住腳的。秦始皇焚書坑儒,許多書籍在民間仍然得以保存,重新整理當(dāng)非難事。中國的詩不叫詩,叫“詩歌”,在人民群眾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情況下,詩得以流傳靠的就是曲調(diào)。在古代,這些曲調(diào)是固定的,也是被老百姓掌握了的,要不然,就流傳不開。由于清末簡譜才傳入中國,中國的古曲調(diào)大部分“失傳”了,但我認(rèn)為,是沒有被發(fā)掘出來,原來的“律呂”、“工尺”通過對照可譯成現(xiàn)代樂譜。兩千年來,自稱“大師”的和被稱為“大師”的人不少,但通四書五經(jīng)的不通音樂,通音樂的不通四書五經(jīng),所以,樂經(jīng)遲遲沒有被發(fā)掘整理出來,這真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憾事……
聽了胡圣虎的話,錢先生陷入了沉思。只見先生緩緩站起來,踱著方步:我怎么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呢?可惜,我對這一領(lǐng)域涉獵甚少,后生可畏啊!希望你做成這件前無古人的事情!
從此,胡圣虎與錢先生論“月經(jīng)(樂經(jīng))”的故事在北大校園傳為美談,更令其名聲大振。
北大5年,實際上也是他的書法技藝從理論到實踐全面提高的過程。
當(dāng)年,北大名師云集,王力、朱光潛、宗白華、季羨林、金克木等數(shù)十位大師,都是書壇大手筆,在這樣濃厚的藝術(shù)氛圍之中,經(jīng)過李志敏、陳玉龍教授的耳提面命,經(jīng)過京城眾多名家的悉心指點(diǎn),胡圣虎眼界大為開闊,書法進(jìn)步很快,繼之聲名遠(yuǎn)播。未幾,便與中文系曹寶麟、國政系白謙慎、圖書館系華人德、歷史系張此夫四人一道,并稱為北大書法“五小虎”。在校園,他將頑童式的到處題詞又上了一個臺階,樹枝、抹布、手指、筷子上綁棉花都可以當(dāng)筆使,宿舍的墻壁、課堂的桌椅、女友的掌心,甚至廁所的門板都是他的“宣紙”,最經(jīng)典的還是在“三角地”宣傳欄不斷地出海報、寫通知,整個北大校園,到處都是他的手筆。1984年國慶游行那幅標(biāo)語在“秘密策劃”時,兩個生物系的同學(xué)之所以找到胡圣虎,當(dāng)然是因為他的書法名氣;但那幅標(biāo)語從最初醞釀的七八個字,因找不到大的毛筆和合適紙張,最后被濃縮成“小平您好”四字經(jīng)典,并以抹布作筆被寫在床單上,這事絕對只有胡圣虎想得出來并且能辦得到。
不能不說卻不能多說的畢業(yè)故事
上世紀(jì)八十年代中期,社會結(jié)構(gòu)急劇變化,一批新興的一夜暴富階層迅速崛起,而構(gòu)成這一階層的不少人要么是文盲半文盲、曾經(jīng)的社會邊緣人物,要么是一批大小權(quán)貴子弟。被譽(yù)為天之驕子的大學(xué)生心理失去了平衡,大學(xué)生空懷報國之志,難成濟(jì)世之才,于是厭學(xué)風(fēng)陡漲,“讀書無用”、“六十分萬歲”在大學(xué)校園里迅速蔓延。堂堂北大,同樣不能幸免。
王利芬做節(jié)目好,部分得益于她對人的判斷與解讀。“我原來的專業(yè)是文學(xué)評論,看過很多長篇小說。文學(xué)作品也是在刻畫人物,表現(xiàn)人生。在電視節(jié)目中我接觸這么多優(yōu)秀的人,我也是在觀察他們的人生,他們怎樣判斷事物,怎樣渡過自己的難關(guān);觀察他們怎樣判斷他人,怎樣做出決策。應(yīng)該說原來文學(xué)專業(yè)所學(xué)的都是非常有利于我的。你跟什么人同行,你就大概能夠從什么人那里學(xué)到什么東西,這個是很重要的。”
糾結(jié)也來源于此。在《新聞?wù){(diào)查》的三年多的時間里,王利芬一路狂奔,看不到身邊的人,好像還是校園里,只管埋頭苦讀,能得到好成績就是好孩子。
“我真可謂埋頭拉車不問路,只懂得做事,不懂得做人,只懂得向前沖,不懂得兩點(diǎn)之間的距離有時并不是直線最短。只懂自已的能力就是一切,就像一個考高分的高中生,不懂得即使有能力,讓別人的感受不好也是一種沒有能力的體現(xiàn)。”
長于理性分析的王利芬,多年后這樣總結(jié)那段日子。不知概括性的語言背后藏著多少無奈。
夢想就是堅持
調(diào)查記者做得風(fēng)生水起,她卻又轉(zhuǎn)身離開。
上世紀(jì)90年代,改革開放進(jìn)行了十幾年,經(jīng)濟(jì)改革是國家的主題,在全球經(jīng)濟(jì)浪潮裹挾之下,民眾迫切了解中國社會的運(yùn)轉(zhuǎn)機(jī)制,那么要懂經(jīng)濟(jì)。跟時任臺長趙化勇談完之后,王利芬接手新欄目《對話》制片人,調(diào)入央視財經(jīng)頻道。
當(dāng)時整個欄目組只有一部電話,一個分機(jī),四個人——兩個主編,兩個助導(dǎo)。只過了一年,王利芬就讓《對話》成為了央視二套的王牌節(jié)目。她的秘訣之一是為《對話》打造的“81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負(fù)責(zé)到人,環(huán)環(huán)相扣,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