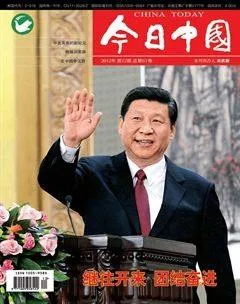“虐童”的無法適用
2012年10月24日,“@將講090080”在微博里發了一張照片,引來眾多網友瘋轉。照片里,女老師一臉微笑,兩只手分別揪著一名男童的左右耳朵,將男童雙腳提離地面約10厘米,耳朵被扯得變形,男童因劇痛張著嘴巴哇哇大哭。“@將講090080”稱,照片是女老師本人通過微信發給一位家長的,她還稱自己在溫嶺牛津幼兒園當老師。
事發后不久,該教師虐待班上幼兒全過程的視頻在網上被曝光,一時間眾網友聲討不斷,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然而,隨著照片中的“肇事者”顏艷紅被刑拘、眾人的擔憂和憤怒才稍有平復時,卻傳來了虐童女教師涉嫌尋釁滋事罪一案未經當地檢察院批捕、已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的消息。這一看似意外的結果不免令很多人心生質疑:為何如此“罪大惡極”,竟也能“逍遙法外”?
其實,這個結果不難預見,顏艷紅的行為從客觀上來講無疑是一種虐待行為,但就目前中國刑法中虐待罪的適用范圍來看,該罪要求虐待行為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而本案顯然不符合這一條件。因此公安機關選擇“涉嫌尋釁滋事罪”來“兜底”立案,雖然有些牽強附會,但在虐待罪無法適用、而中國刑法中又尚沒有“虐待兒童罪”的法律困境下,這確實是一種謹慎卻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于是質疑過后,我們不得不正視當現實遭遇了法律困境后的尷尬,而將“虐待兒童罪”列入中國刑法加以規制似乎也成為了近期一股甚為強大的“民意”。
正如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姚建龍所說:“在國外,虐待兒童的行為是法律的高壓線,而在中國還是一條虛線——雖然形式上禁止但定性模糊,而且處罰疲軟。”的確,雖然中國《憲法》、《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中對保護兒童權益都有相關規定,但對于何為虐待兒童,法律定性卻并不清晰。
放眼歐美法系,虐待兒童的行為早已被納入嚴格的法律規制。美國早在1974年就通過了《虐童防止與處理法》,對虐待兒童罪名的認定、懲罰和救濟措施都做了詳盡的規定;美國疾病控制和保護中心更將虐待兒童定義為對任何兒童導致傷害、潛在的傷害,或恐嚇的傷害的行為。此外,英國的《兒童法案》也有規定:凡是影響兒童生理、智力、情緒、或社會發展的行為都是兒童虐待行為,對虐童行為實行強制報告制度,對虐童事件立案偵查予以懲處。而日本也在2000年通過了《防止兒童虐待法》,并不斷予以修訂和補充,確保兒童免受家長、教師和其他社會成員的虐待。
虐童事件性質的惡劣和所激起的公憤,盡管不動用刑法并不代表肇事老師會躲過行政處罰、教育系統內部懲處等制裁,但公眾之中對這一結果表示失望者也大有人在。從虐童事件曝光之日起,呼吁對肇事者給予嚴厲的懲處就是一種普遍的民意,而上升到刑法層面無疑是契合這一民意的最為理想的結果。
“虐待兒童罪”對于中國的刑法立法來說并非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早在去年年初,在談及救助流浪兒童的問題時,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政協副主席史貽云就曾呼吁中國刑法應該增設“虐待兒童罪”,她提出只要是有損兒童身心健康的行為,不管是其親生父母還是其他組織或者個人,都應依法追究其責任,構成犯罪的還應追究其刑事責任。因此她建議增設“虐待兒童罪”以保護未成年人。而隨著此次虐待兒童事件的出現,有針對性地去完善立法已然成為民心所向,中國眾多法律界人士也紛紛呼吁,中國《刑法》應盡快增設獨立的虐待兒童罪罪名,放寬虐待兒童的入罪標準,將沒有造成死傷但性質惡劣的虐童行為予以犯罪化,從而消除目前在中國虐待兒童的行為難以準確適用刑法罪名的尷尬、被動局面。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此次教師虐童事件的出現除了會令教育界警醒,還或將有望推進中國刑法的立法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國刑事立法上的發展趨勢。
世界上沒有萬能的刑法,但世界上的刑法也無疑都是在民意的訴求與司法裁判間的博弈中逐漸完善的。民意無法左右司法,司法也確實不該被民意所綁架,但此次教師虐童事件所遭遇的民意與司法獨立的沖突或許會成為中國刑法增設“虐待兒童罪”的一副強有力的催化劑,中國在虐童領域內的法律困境也或將因此事件而有所突破。中國的“虐待兒童罪”或許無法完全杜絕下一個“顏艷紅”的出現,但毫無疑問的是,在未來,隨著中國刑事立法的不斷完善,虐待兒童的行為除了要接受群眾的“輿論審判”外,還必將面臨最為公正而嚴厲的法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