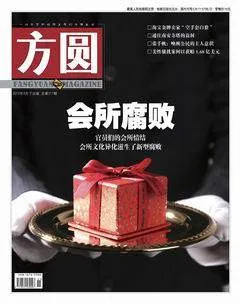張千帆:喚醒公民的主人意識
2012-12-29 00:00:00馮建紅
方圓 2012年8期

【√】倘若權力話語體系不能撐起中國的憲政大廈,那該尋求何種支柱呢?這個問題讓張千帆很是困惑,他想找到答案
近日,著名憲法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的最新力作《為了人的尊嚴:中國古典政治哲學批判與重構》(以下簡稱《為了人的尊嚴》)面世。
這是一本哲學宗教類書籍,讀起來有些枯澀難懂。
“通俗地來講,您寫此書的目的意義何在?”《方圓》記者單刀直入地問張千帆。他沒有正面回答,反問記者:“2011年的小悅悅事件中,那些圍觀者們都認為自己沒有責任,這說明了什么?”
“這說明現在大多數人沒有樹立所謂人格,更加沒有道德義務感,中國新的倫理道德體系已經呈現真空。”他自問自答。
“承載著幾千年文明的中國鮮有像今天這樣沒有信仰、沒有是非、沒有道德勇氣、沒有自我反省和凈化的能力,貪官污吏鮮有像今天這樣多如牛毛,空氣鮮有如此渾濁,食品鮮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鮮有萎縮得如此之快……”這樣的國之現狀,使得張千帆憂心忡忡。
如果社會缺少對基本道德規范的普遍認同與尊重,就不可能建起一個法治國家。張千帆想要做的,就是重塑一種新的倫理道德體系。而這種新的話語體系的核心,便是尊嚴理念。
“現在的人們人格上極度走偏,他們常被稱為臣民、順民,甚至暴民,恰恰卻不是公民。”張千帆說,他所主張的以尊嚴為核心的話語體系,實為糾偏,希望人們能夠成為真正的公民,一個有尊嚴的人。
張千帆曾擬馬丁·路德金的名篇,作《我有一個夢——做一個有尊嚴的中國人》,呼吁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要忘記做人的尊嚴,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還是普通民眾。
十年一夢。為了這個夢,他走過了很曲折的道路,而且,他知道,正走的這條路還很長很長。
棄理從文
張千帆走上法律研究的路子,與魯迅棄醫從文的經歷有著驚人的相似。
張千帆1964年生于江蘇南京,童年時光大部分是在上海外婆家度過的。雖成長在文革期間,但他從小就愛讀書,學業上從未荒廢。1980年,他以高分考入南京大學物理系,學的是固體物理專業。
“當初選擇學物理,是時代風氣使然,尤其是李政道、楊振寧回國掀起的‘物理熱’,對我的影響很大。當時百廢待興的中國,需要大量科學技術人才,學成報國是我從小的夢想。”張千帆說。
1981年,李政道在美國主持“卡斯比”考試,美國八十多所大學每年從中國大陸招收通過這一考試的一百多名學生赴美留學。1983年本科畢業后,張千帆順利考取“卡斯比”,來到美國讀碩士,學習生物物理。他的課程與科研工作都得到導師們的高度評價。1989年,他博士畢業,接著做博士后。
然而,在做博士后之前,張千帆的世界觀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在做博士論文的最后階段,張千帆突然對他以前工作的價值從根本上改變了看法。他發現以前的工作與成功只是一種自我陶醉,它和中國的現實離得太遠。
這種現實就是,中國歷來鼓勵自然科學研究,而且中國人也很聰明,不缺乏自然科學人才,但社會科學方面卻不一樣,中國從來都缺少哲學家和思想家。有人將這解釋為,中國人虛偽、不實在,思想浮于表面,喜歡人與人斗,所以中國盛產權術高手和人際關系高手,卻誕生不了世界級的思想家和哲學家。
張千帆意識到,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或許不是傳統的技術類科學知識(盡管他從來沒有否定過它們的重要性),而是一種新思想、新知識。而對多年浸泡在西方思想里的他而言,或許能夠在此方面作些努力。就在這些想法蹦出的那一秒,他開始認識到法律與政府學對中國社會的重要性,仿佛在一瞬間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歸屬,并且決定在這方面做點事情。
然而,在作出上面決定時,張千帆的社會科學知識基本是零。所以,在做博士后的兩年多時間里,張千帆開始抽時間系統地學習西方政治思想的課程。
一開始,他考慮著做一名“業余愛好者”,在從事自然科學的同時關注一點社會科學,但因為美國大學對論文發表的壓力很大,自然科學本身又是一項很艱苦的工作,要求全力投入,“腳踏兩只船”不現實。
“除了徹底‘改行’之外,別無選擇。”就這樣,張千帆毅然決定轉向,棄理從文。1992年,張千帆來到馬里蘭大學法學院,開始為期三年的法科學習。
找到能夠“安身立命”的東西
從物理學到法學的跨越,曾帶給張千帆強烈的陣痛感。雖然預料到這個選擇會帶來一段艱難的過渡期,只是沒想到,這個過程如此記憶深刻。
在轉向之前,張千帆靠著做物理學博士后的工資,存了一部分積蓄。但來到馬里蘭大學后,就失去了穩定的收入,而法學院又學費昂貴,第一個學年就花光了他銀行里所有的積蓄。“那是我一輩子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心里產生了恐慌。”張千帆回憶說,雖然一開始在馬里蘭沒能解決“溫飽”問題,但他沒有放棄法學的繼續學習。后來,他幸運地在大學計算機中心找了一個底薪但還算清閑的咨詢工作,勉強“糊口”。
第二年和第三年,因為沒有經濟能力注冊,張千帆靠著旁聽完成了三年的法科學習。
經濟上的壓力只是一部分,對張千帆來說,更大的痛是學習的壓力。因為“改行”時對社會科學的知識是“一窮二白”,完全重新開始,要吸收的知識量很大。同時,文科對于閱讀與寫作的要求比理科高得多,這讓他很不適應。
有一次,寫一篇政治經濟學期末論文的時候,張千帆坐在電腦前,盡管知道要寫什么,但卻一個詞也打不出來。“自己對寫作不夠自信,好像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把自己罩住了。”但后來,那篇論文還相當成功,得到了老師很高的評價,并構成了他第一本書的思路。
從此 ,張千帆利用空余時間收集大量的資料,開始寫作。在馬里蘭大學第三年的學習結束時,看著一個又一個同學都在興高采烈地參加畢業典禮,張千帆卻一個人默默地帶上書的草稿,開始計劃下一段的生活。
“在馬里蘭的三年,是非常充實、相當多產的三年,我目前已經發表的成果,絕大多數是在那個時期完成的。”張千帆說。
1995年,張千帆來到德克薩斯奧斯汀政府學院,讀政府學博士,解決了個人的經濟危機。之前三年的積累,也讓他的思想獲得了一次很大的飛躍。在此后相對寧靜的三年,他選修了自己一直感興趣的哲學課,并坐下來對困惑自己的一些基本問題作一個比較深入的思考,可以說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尋求的世界觀,一種讓他感到能夠“安身立命”的東西。
這種“安身立命”的東西或是一種信仰,與憲政有關,與法律有關,更關乎中國權利保障的實現問題。
沒有誰會否認,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在一步步覺醒。網絡便是一個重要證明,近年來,通過網絡監督權力、參與政治,已成不少中國人權利意識覺醒的鮮明注腳。作為一個憲法學者,張千帆當然不反對談論權利。“事實上,憲法成天在談論各式各樣的‘權利’,尤其是在中國人的權利保障還很不到位、個人權利和政府權力仍然嚴重失衡的情況下,更有必要大張旗鼓地宣揚人權理念。”
但他以為,任何事情都需要把握一個度,即便權利也不例外,“權利”談太多了,也會出問題。因為,“權利”在本質上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話語體系,它有其局限性,比如,權利話語暗含了自私人格,它會使得人們一味地享受權利,而不注重履行義務,而這恰恰是實現中國權利保障的最大障礙。
倘若權力話語體系不能撐起中國的憲政大廈,那該尋求何種支柱呢?這個問題讓張千帆很是困惑,他想找到答案。
十年一夢,為了人的尊嚴
帶著困惑,從1995年到1999年間,在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研習期間,張千帆完成了哲學經典的閱讀,思考著、尋找著解決之道。
那些日子,張千帆像是著了魔,整日扎在書堆里。他清晰地記得,1996年夏天,他去密西根大學擔任ICPSR(美國校際政治與社會研究聯盟)暑期班助理時,某天晚上,他從密大的東亞圖書館抱著一大堆中文資料下樓,遇到一家“老外”,笑他會“遭搶”。因為他當時是一副應接不暇、完全無助的樣子。
1998年,張千帆寫作的《儒學的重構——中國古典中的人格尊嚴觀念》一文,在波士頓召開的第二十屆世界哲學大會上發表。在文章中,張千帆提出了“儒家的人格尊嚴概念蘊含著更為平衡和連貫的權利與義務概念”。除此文章外,張千帆還通過多篇論文,梳理并評價了墨家與道家思想對尊嚴理念的獨到貢獻。
“中國古典哲學的共同主線是人格尊嚴這一永恒理念。”張千帆通過展開討論儒家、墨家、道家不同學派的諸多差異,得出三個思想流派只是體現了一個共同道德原則的不同方面的結論,那就是人是作為目的的自身,而不是僅僅作為其他目的的手段。這種內含人格尊嚴的道德愿景只有通過適當的社會和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實踐。
“作為新的話語體系核心,尊嚴理念不僅是建造中國憲政大廈的起點,也將成為溝通中國與世界文明的橋梁。”這是張千帆長期思考的結晶。
他的這一理念與北京大學哲學系已故教授張岱年的研究理念不謀而合。在他關于中國古典政治哲學批判與重構的論文英文寫作期間,張岱年曾對其指導和鼓勵。
“張先生博學儒雅、平易近人,在我這個不知名的學生面前沒有一點架子。他對人格尊嚴理論素有研究,還專門寫信囑我深入探討這個論題。”張千帆在書的引言中寫道。
1999年,張千帆拿到政府學博士學位后回國,先是在南京大學法學院當教授,2003年,調入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授。張千帆說,他調入北京工作后,張先生年逾九旬,平時他人不便登門叨擾,不想此后不久便溘然長逝,留下了永久的遺憾。
此后的多年里,張千帆陸陸續續的將人格尊嚴理念的論題英文版本翻譯成中文,并于2012年3月集結出版,即為《為了人的尊嚴》。
“該書的最終出版也算是自己對張先生囑托的一個交代,亦或是其未經事業的一個延續。”張千帆說。
何為公民尊嚴
不少人曾問張千帆,何謂公民尊嚴?他從憲政層次角度給予了解釋:尊嚴,簡單地說,就是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平衡。
“一個只是主張權利而不盡自己義務的人是沒有尊嚴的;但是反過來,如果一個人只知道履行義務,而沒有權利意識,那也不是一個有尊嚴的現代公民。”在張千帆看來,不管是在古代,還是現代社會,公民都未能真正實現尊嚴。
張千帆解釋說,中國古代哲學對“權利”不夠重視,例如,儒學是一種義務導向哲學,主張人要履行與其身份地位相稱的義務。相反,霍布斯以來的現代西方自由主義哲學偏向“權利”,不夠重視“義務”。
“如果僅將西方的‘權利’話語簡單照搬到中國,不足以實現尊嚴。只有中西結合,達到權利與義務的平衡,才能實現‘尊嚴’的理想。”帶著這樣的想法,張千帆通過《為了人的尊嚴》一書重構了以尊嚴為中心的新話語體系。
但對民眾來說,很難理解這種“以尊嚴為中心的話語體系”,因為可能每個人對“尊嚴”的理解都不一樣。
古人說:“衣食足而知榮辱。”作為個人,吃飽穿暖是尊嚴的前提,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如何去談尊嚴?
再者,現實中,人們對尊嚴的理解還停留在較低的層次中。譬如,哪天我的房子沒有任何商量就被拆了,補償又不到位,造成生活十分拮據,那么我的尊嚴就顯然受到侵犯;即便補償到位,沒有經過協商和同意就拆我的房子,同樣也侵犯了我作為公民的尊嚴。
張千帆對這種現狀表示理解,但他認為,雖然物質基礎是尊嚴的必要條件,但卻不是充分條件,而且只要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尊嚴其實與金錢或物質生活關系不大。因為,在一個共和國,公民的尊嚴更體現在能通過理性的公共參與去影響更高層次的國家政治生活,使這個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而不是像一只微不足道的螞蟻那樣任人踐踏、碾壓。
從選票開始
“但目前,公民參與不夠積極,因為他們覺得參與沒有太大意義。這種情況下,公民如何去提升尊嚴呢?”《方圓》記者問張千帆。
“從選票開始。我曾多次說過,改變中國,就從你的選票開始。”張千帆接著說,“選舉權是最重要的公民權利,也是尊嚴的重要體現;沒有選舉權就只能是臣民,是不可能有尊嚴的。村委會選舉、居委會選舉、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公民都應積極參與。”
有一次,張千帆的一個學生向他抱怨,說自己所在的地區選舉過分流于形式,負責選舉工作人員給選民每人一張人大代表的提名候選人名單,要求選民從中挑選幾人,而選民連這些候選人長什么樣子都不知道。
“當工作人員拿一份候選人名單讓你選幾名時,你可以提議讓提名候選人公開演講為自己爭選票。一個人的這種行動力可能很小,提出的建議甚至不被有關部門理睬,但當越來越多的公民都行動的時候,就能促使政府有所行動。”張千帆如此回應學生。
張千帆自己也身體力行地踐行著。2005年,他對河北省石家莊東營村進行的村民代表選舉進行了一番考察,并深入探討了在農村基層選舉中被普遍忽視的問題村民代表的選舉和村選區的劃分。
“現在選舉問題是很多,但我們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局面,這需要公民和政府的合作,但公民要先行動起來。” 張千帆始終相信,“我欲仁,斯仁至矣”,尊嚴公民的未來,就掌握在每個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