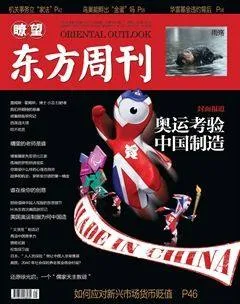吃不吃苦
我們經常用“能吃苦”來形容一個人的精神品質。這里的“苦”當然不是它的本意。苦的本意是一種味道,一種令人不愉悅的味道。進化學家認為,人類對苦味的感知是一種保護機制。因為自然界中苦的那些物質,比如植物中的生物堿,往往是有毒的。對苦味敏感的人,就更容易發現有毒的食物,從而獲得更多的生存機會。
1931年,一位名叫福克斯(Fox)的化學家報道了一項發現:同樣的苦味物質苯硫脲(PTC),有大約28%的人嘗不到苦味,有65%的人能嘗出。后來的研究發現,這個比例跟人種密切相關,比如中國漢族人中嘗不出苯硫脲苦味的人只有百分之幾,而某些少數民族的人中則高達百分之幾十。
PTC因此成了研究苦味與遺傳的一個工具。后來發現另一種叫做“丙硫氧嘧啶(PROP)”的物質,更適合作為工具。人們對它的敏感情況跟PTC不同,大約有25%的人嘗不出它的苦味,50%的覺得一般苦,而另外25%的人則感覺“非常苦”。感覺非常苦的這部分人,被稱為“超級品嘗者”。而嘗不出苦味的那部分人,可以稱為“苦盲”。
不過味道是很復雜的現象,不僅跟身體結構有關---而這一般是由遺傳決定的,還跟后天的培養以及文化傳統有關。超級品嘗者是根據對PROP的敏感性來確定的,但PROP只是眾多苦味物質中的一種。嘗不出PROP苦味的“苦盲”,對其他苦味物質并不見得也“盲”---這也就可以解釋,雖然平均四五個人中就有一個“苦盲”,但卻幾乎沒有聽說過誰不知道苦是什么味道。
在遠古的時候,祖先們只能依靠自己的眼睛和舌頭來確定食物是否安全,超級品嘗者當然就有了不小的生存優勢。到了今天,人類對食物安全性的評估已經有了許多精確而非常可靠的工具,用舌頭來嘗味道從而估計毒性,就很原始且可靠性很低了。作為一個超級品嘗者,還有值得驕傲的地方嗎?
超級品嘗者對其他味道的敏感性沒有充分確定的規律,但這些人確實可能對其他味道更加敏感。對于那些限制攝入有利健康的食物成分,如果超級品嘗能力使得人們更容易滿足,那么就不需要攝入那么多的量,卻依然可以滿足口腹之欲。比如酒味、咸味、甜味等等,如果在較少的攝入量下產生了同樣的感官享受,無疑就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很多時候為了健康不得不犧牲一些美味,而超級品嘗者在他們敏感的美味上,做出的犧牲也就要小一些。
左右逢源的事情當然是很少的。超級品嘗者的敏感,也可能會使他們對于口味更加挑剔。比如他們中不少人對辣味更敏感,大概就難以享受川菜湘菜的精華。還有很多天然的食物,比如豆類、茶、咖啡、橄欖等等,含有一些苦味物質。它們的苦味對普通人或者味盲們沒有多大的困擾,而超級品嘗者們卻可能因為自己的敏感而無福消受,失去了不少舌尖上的樂趣。
降低或者去除食物中的苦味是現代食品技術中的一大挑戰。小朋友吃苦的藥,媽媽們可能會用糖水來送服。在日常語言中,苦的反義詞是甜,人們也會有“加糖可以去除苦味”的錯覺。實際上,人類感受苦味和甜味的受體并不相同,苦味物質和甜味物質可以共存在一起,甜味也不能真正地“中和”苦味。
我們覺得加糖之后不那么苦了,是因為強烈的甜味把大腦的注意力吸引了過去,從而忽視了苦味。這就像小聲說話的時候,如果有人大聲喧嘩,我們聽到的就是喧嘩的聲音。如果仔細聽,那竊竊私語的聲音依然存在。那些經過培訓的專業品嘗師,就能夠不受糖的干擾而品嘗出苦味。
通過加入其他的味道,來“掩蓋”苦味等不受人待見的味道,一直是食品廠家的秘笈。對于苦味,釜底抽薪的思路是:從食物中分離純化找到苦味物質,然后通過細胞生物學技術識別出舌頭上對這些苦味物質的受體,再找到安全可食用、能與受體結合、卻不產生苦味信號的物質,加到食物中去“阻擊”苦味。這種思路的研究有了一些進展,不過距離實用,還有比較遠的路要走。
云無心:
食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