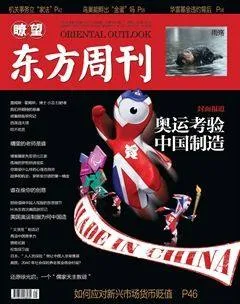為什么紀念徐光啟
2012-12-29 00:00:00楊天劉耿
瞭望東方周刊 2012年29期

2012年是徐光啟450周年誕辰,整個上半年,上海的一系列紀念活動廣受關注。
徐光啟去世至今近380年,其間,隆重的紀念活動共有過五次,2012年上半年這次紀念活動算是第六次。
而新世紀的12年是明顯的紀念密集期。除了上面提及的第五、六次的紀念活動,還有2003年重修徐光啟墓、建徐光啟紀念館;2004年,將一棟有四五百年歷史的南華春堂搬到徐光啟墓附近作紀念館;2008年,上海組織了徐光啟逝世375周年的祭掃活動。
學者、官方、民間合力
紀念徐光啟的這一波波高潮,要突破的最大障礙是這位愛國科學家的天主教徒身份,而這個突破是由學者、官方、民間合力完成的。
上世紀50年代起,徐光啟的科學家身份在不斷地宣傳,教徒身份則避而不提,碰到與徐光啟的宗教信仰有關的書籍也就不出版了。
1988年,青年學者李天綱發表了一篇論文《徐光啟與明末天主教》,講徐光啟的宗教背景。“這個文章寫出來,很多人都大吃一驚。徐光啟怎么可能是天主教徒?大部分人只知道他是科學家,根本不知道他的天主教徒身份。”現為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的李天綱對《瞭望東方周刊》回憶說。
李天綱和他的老師朱維錚持續而有力地推動社會對徐光啟的重視,并找到徐匯區文化局副局長宋浩杰。學界在這個問題上保持著與有關部門的良性互動。2003年大修徐光啟墓,大十字架重新豎立在墓前。
民間亦參與其中。
上海市南郊中學的退休歷史教師王成義從“文革”起就開始了對徐光啟的研究。原因有二:家與徐閣老(光啟)墳山為鄰;妻子的外婆、舅媽都是徐光啟的后裔。
從獲取史料的先難后易,王成義感覺學術研究的氛圍逐漸寬松。“上海圖書館的古籍書當時是不開放的,改革開放之后,才慢慢地放寬。”他對本刊記者說。
2007年之前的幾次研討會,王成義去旁聽,“全是教授、博士,沒有人搭理我,他們去吃午飯,我就自己去外面吃”。
王成義花了幾萬元自費出版了3000冊《徐光啟家世》,又花幾萬元制作了200個紀念大銅章,送給熟悉的與會者。學者和官員看到了這位民間研究者的學術誠意,從2007年起的紀念活動合影中,都能找得到王成義。
從“徐上海”到徐家匯
上海做紀念徐光啟這篇文章,自然與上海有關。
上海開發較晚,“大人物”少,但在明朝晚期出了個徐光啟。
徐光啟在病逝以前,已被歐洲人士稱作“徐上海”。
余秋雨稱徐光啟是“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今日上海人的一些要素,在徐光啟身上有跡可尋:“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著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并自然而然地匯入人生。”
利瑪竇在描述上海人時說:“這里的人,特別是城里人,都非常活躍,不大穩定,頭腦聰明。”說明近代上海的市民文化性格在更早期就有自己的端倪。
明、清時期的上海,教徒聚集的地區,如浦東、松江、崇明、青浦、徐家匯、盧灣、虹口、南市等地,至今仍是教徒聚集地區,古今是存在因果關系的。
上海市政協主席馮國勤在紀念大會上的發言說“徐光啟現在已融入了上海的城市精神”,這是官方對徐光啟與上海精神之勾連的認定。
“徐光啟可以看作是一個文化的地標,對上海人是一個很大的激勵。”李天綱說。
徐光啟歸葬于當時上海縣城西門外十余里的法華鄉,這里是他從事農業實驗的地方,徐家后人從上海縣城搬到墓地附近,在此繁衍生息,漸成“徐家匯”。
歷史上法國的耶穌會士以徐家匯為活動中心,對上海以及江南一帶的教育和科學發展都產生了巨大且持久的影響。
“以徐光啟為首的一代人,在明清文化最繁榮發達的江南地區,開創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局面,這使得后來上海在19、20世紀成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李天綱對本刊記者說。
“三步走戰略”:翻譯、會通、超勝
明清之際,中華帝國與西方近代科學有了第一次接觸。徐光啟與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等,可謂歷史上歐洲與中國首次重大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徐光啟差不多后半生都與利瑪竇、郭居靜、熊三拔等傳教士交往研習。這一跨文化的交往是中西交流史上最成功的范例。
學者對徐光啟是否“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仍存爭議,但在“中西會通第一人”的稱謂上基本達成一致。
“融通中西是徐光啟自己的主張,海納百川是我們今天對他的概括。”宋浩杰說,“海納百川”是上海城市精神的第一個詞組。
翻譯、會通、超勝是徐光啟制訂的“三步走戰略”,在李天綱看來,這樣循序漸進的三階段,自信、溫和、不失衡、心胸開放,比兩百多年后“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心態要好很多,“中國人應該回到徐光啟的高度,重溫大國的氣度和開放情懷。唯其如此,中國在重歸世界大國舞臺的過程,才不會讓他國誤解”。
“徐光啟對于異質文化的包容態度對于中國人意義很大。可以克服中國一些人自大、自我甚至自戀的意識。”李天綱說。
遺銀一兩、舊衣數件
不久前,徐光啟紀念館被徐匯區定為公務員的廉政教育基地。
徐光啟是明末最后三朝的重臣,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宰相),是歷史上京中官階最高的上海人。
“官品”確實是學者研究徐光啟的一個維度,已故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在《晚明巨人“徐上海”》一文中稱贊他“清廉自守,終身苦貧而拒收合法的苞苴”、“死時京寓僅遺銀一兩、舊衣數件”。
明末黨爭迭起,“他只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碰到朝廷有黨爭就躲開,去天津種地去了。現在很難查明徐光啟到底是屬于東林黨還是屬于閹黨。”李天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