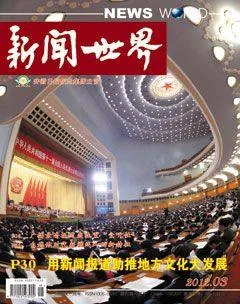“不確定”的動畫景觀
【摘 要】2011年的國產動畫電影迎來小陽春,其中出現的多元文化混雜傳播現象十分明顯。本文試從“文化雜交”理論的角度,以年度國產動畫電影中叫好不斷的兩部大制作——《魁拔》與《兔俠傳奇》為例,分析其中的文化雜交現象。
【關鍵詞】文化雜交 國產動畫 《魁拔》 《兔俠傳奇》
剛剛過去的2011國產動畫大片“怒放”之潮,很是讓人激動和鼓舞了一把——年初有《喜羊羊與灰太狼之兔年頂呱呱》,《恐龍寶貝》,然后是中日合拍片《老夫子之小水虎傳奇》,中德合拍3D動畫《熊貓總動員》的再接再厲,暑期檔的大爆發則有《西柏坡》、《兔俠傳奇》和《魁拔》。另外,科幻題材的《賽爾號之尋找鳳凰神獸》和網絡游戲改編的《摩爾莊園冰世紀》等,也在聲勢上頗有貢獻。現以2011動畫大片中,兩部業內業外都叫好不斷的作品《魁拔》與《兔俠傳奇》為例,談一談文化雜交理論背景下“不確定”的動畫景觀。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所謂“文化雜交”的概念。
這個詞匯因墨西哥學者加西亞·坎克里尼于1989年出版的專著《雜交文化——兼論進入和離開現代性的策略》而廣泛流傳,他試圖用“雜交文化”一詞,描述當今拉美國家既非現代又非傳統,本土文化和外國文化雜陳的特殊社會文化形態。1999年,英國著名傳播學者湯林森在他的著作《全球化與文化》中,則將這一詞匯提升到了理論高度,正如他在書中所說的:“當今加速的全球化,意味著雜交文化的雜交化”。
全球化的浪潮浩浩蕩蕩,洗刷著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技術的迅猛發展,更令文化產品之間的模仿滲透變得簡單。誤讀與同化此起彼伏,解構和重建更是火光飛濺。于是,當一部部文學藝術新作問世,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藝術意義上的審美奇觀,更看到傳播學意義上的傳播景觀。而表現在這兩部國產動畫大片中的景觀,則因其“兼容并蓄”而呈現出特有的“不確定”性。
我們先來看看《魁拔》。
影片首先虛構設定了一個魔怪生物“魁拔”,每333年復活一次殘害無數生靈。生活在平靜鄉村的“獨行族”妖俠蠻小滿和他的養子蠻吉,在第六代魁拔復活出現時,與各族豪俠一同出征、殲滅魁拔。而主角蠻吉其實就是忘記了自己大魔頭本質的魁拔。
來自主創方面對這部電影的宣傳主題定調是——國內首部原創玄幻動畫電影。其中,關鍵詞“玄幻”體現了它的核心文化是偏中華傳統文化的。
縱觀全片,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道家文化的痕跡還是相當鮮明,雖然在名詞形式上作了一定變型,但本義不變。如將“氣功”變稱為“脈術”,“穴道”換作為“脈門”,以“元泱境界”形容“混元宇宙”,以“神族”“龍族”“人族”“獸族”等各個種族代替傳統武林的各大門派。
但這個在中華傳統文化略作修飾的外衣包裹之下的武俠故事的主題,卻令人頗感意外——既不是江湖俠義,也沒有國仇家恨,而是“反抗等級制度”。
圍繞“反抗等級制度”作文章,恰恰是一個相當西方民主化的表達。中華文化向年來強調“忠孝”,提倡倫理秩序,雖然《西游記》中有叛逆的孫悟空,但也是為了將他降伏于比“天庭體制”更大的“宇宙體制”之中。而在《魁拔》中,推動主角成長的“發動機”,卻是“紋耀”。
“紋耀”類似于身份證,是區分俠士們高貴和強大等級的憑證。片中的兩位主角“蠻小滿和蠻吉”從一開始執著于找村長比武,就是為了獲得村長對他們的身份認證,在后來的參軍伏魔之路上的幾個主要場景,故事也都是圍繞“紋耀”展開,如與龍族高手的比武,港口蠻吉對抗衛兵等。
蠻小滿和蠻吉父子之情的情緒線索,則是完成了對“反抗等級制度,證明自身價值”理念的強化。父子之情作為蠻吉的動機輔線,來源于日本文化特有的“情感訴求”傳統。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在于“理”。相對于“理”,“情”是很淡化的。筆者覺得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的動畫電影總是流于說教的原因。
于是,我們看到故事最一開始的“除魔”完全被虛化了。換之以來自西方的和日本的多重主題。或許,在《魁拔》的續集之中還會繼續“除魔”這一主題,而在此片中,則是僅僅被當做了背景。這在表現武俠文化的國產電影中,還是相當罕見的。這是一種頗為奇特的主題混雜。
除去主題內容之外,這部國產動畫的美術風格上,也是相當混雜。影片片花首度曝光后,不少媒體都認為《魁拔》與日本動畫經典《七龍珠》、《千與千尋》等有異曲同工之妙。
人物的服裝設定既有傳統東方式的農裝,也有中世紀西方式的官服,還有像極了明朝錦衣衛的軍服。
而影片前半部分的獸族場景,則多見于日本動畫中對日本妖怪文化的演繹。后半部分的港口大戰,亦有著鮮明的“奧特曼”元素和西方科幻風格。
綜上,文化雜交的征象已經相當明顯,如果不看影片制作信息,很難去確定這樣一部作品屬于哪個民族國家、屬于哪種美術門派。它不再是一種傳承的產物,而是多種思潮的混合。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部文化雜交的作品,除國內市場外,出品方更打造了日語版《魁拔》,希望將“中國制造”打入日本市場,讓眾多喜愛日本動漫的少男少女們看到國產動畫的進步,向世界展示中國動畫人的才氣。這番“二次雜交”不知又將獲得怎樣的傳播效果和文化效果。
再談一談《兔俠傳奇》。
據制片方宣傳,《兔俠傳奇》是由代表我國動畫最高水平的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學院和天津北方電影集團聯合投資1.2億拍攝,歷時三年,目前是我國動畫產業投資規模最大的一部作品。
幾乎所有第一眼看到此片畫面的觀眾,都會感覺與夢工廠的《功夫熊貓》非常相似。從人物造型到環境渲染再到動作設計,都有著十分明顯的模仿痕跡。動畫作品與真人表演作品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動畫表現的影像風格,這本身就是一種美術文化。《兔俠傳奇》采用了源自美國的三維毛發技術、動作捕捉技術和表情捕捉技術。片中毛發3D效果細致入微、栩栩如生,畫面細膩、動感十足,并把真實表情融入動畫影像,使片中人物表情更加逼真自然。這些在中國動畫電影界還是首次。《兔俠傳奇》受到《功夫熊貓》所代表的美國3D動畫的影響,不得不理解為美國動畫美術文化的全面滲透。
或許,主創人員還是有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意思吧,影片雖然全面模仿了《功夫熊貓》,但卻將大反派的形象留給了“熊貓”,主角兔俠最后“頓悟”,把熊貓打趴下,隱喻《功夫熊貓》的被擊敗。且不論如今現實下中美兩國動畫的差距,這份勇氣還是可嘉的。
從文化雜交的角度看《兔俠傳奇》與《魁拔》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兔俠傳奇》是中國文化通過《功夫熊貓》與美國文化雜交之后,再回到中國“二次雜交”后的新品種。
前度《功夫熊貓》如何借用中國文化的表層形象元素,來傳達美國式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和反專制主義政治觀,在此限于篇幅,略去不表,這里主要分析《兔俠傳奇》“二次雜交”的傳播路徑。
《兔俠傳奇》講述了京城的武林盟主被徒弟熊天霸(化妝成熊貓的白熊)暗算,臨終前把畢生武功傳授給純樸的炸餅廚師兔二,并將統領武林的令牌交給他,請他一定要把令牌親手交給女兒牡丹。兔二進京尋找牡丹,遇上重重危險,并在日常勞作中悟得絕世武功,最終打敗熊天霸,將令牌交還給牡丹,拯救了武林。在電影中我們看到,正是因為已經注意到《功夫熊貓》對中國文化誤讀的深層用意,所以在《兔俠傳奇》中,個人主義價值觀的“俠義”被二次解構,置換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信義”——主角兔二受人之托,再苦再難也要完成任務。于是故事圍繞著“找牡丹、送令牌”的主要動機展開。此為“信”。輔線則是牡丹的報仇,此為“義”。
主角兔二為人憨厚耿直,不求名利武功,只想過著平淡的生活。他沒有任何壞心眼,甚至有點死心眼——那就是有著執著的誠信。別人交辦的事情一定要完成。這可以看作是中國文化對《功夫熊貓》式文化雜交的一次“撥亂反正”,然而,大部分撥亂反正的結果,往往是矯枉過正或方向偏差。誠然,“信義”確實是中國文化中的主要部分,但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信義”屬于契約范疇,“信”是人際契約,“義”為天倫契約。“義”是文學藝術作品中經常表現的主題,“信”則罕有。因為“守信”屬于基礎性的道德層面,一般很少上升到展現人性沖突的藝術層面。這就像是唐詩宋詞和識字卡片的關系。那么,在此片中,基礎的道德常識特別拿出來強調,則說明受到背后更深層面的文化影響,筆者覺得,那就是當今意識形態文化影響,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重點倡導公正、包容、責任、誠信的價值取向。
于是,我們看到文化再次被雜交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元素與美國價值觀的雜交之后,回到中國與意識形態文化的雜交。
《兔俠傳奇》就是這樣一部二次雜交的作品,也成為了一個“不確定”的景觀。——“中華傳統文化”“美國式個人成長”和“意識形態”三者同時混雜,不確定到底哪一個是主要部分。這也正應合了本文開頭引用英國著名傳播學者湯林森所說:“當今加速的全球化,意味著雜交文化的雜交化”。
羅素曾指出:“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了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的歐洲則仿效著拜占庭帝國。”在傳播速度較慢的時代,文化滲透已然如此,那么在光速傳播的時代,來自不同方向的滲透則更快更多的同時到達,相互碰撞融合,形成“文化雜交”的新景觀。這種景觀帶有明顯的混合性和不確定性,無法清楚界定這景觀所屬的文化類型,它可能對某種文化構成消解,也可能賦予某種文化以新生。
正如“雜交”一詞本意所指的生物學概念一樣,在文化傳播的領域,這樣的“進化”也在不斷進行,或殘酷、或驚喜、或無奈、或自覺,構成了百花齊放的文化景觀,和這個精彩紛呈的多元世界。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