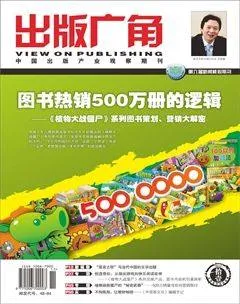論數字化時代口述史出版物傳播中的三種關系
[摘要]在數字化時代,口述歷史的紙媒出版似乎并不具有明顯的傳播優勢,如何在堅守住口述歷史作品品質的同時,突破小眾傳播局限,成為優質的出版物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口述歷史作品水平的優劣、高低,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呈現過程,要保證口述歷史紙媒作品的質量,需要處理好三種關系。
[關鍵詞]口述歷史 出版物 傳播
口述史是普通民眾參與書寫和表述歷史的方式,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口述史成為了大陸史學界和出版界關注的熱點。當下中國的口述史學及其實踐呈現出一派繁榮和喜人景象,成為了學術界和大眾傳媒的關注熱點。但是,在一個數字化時代,和電視、電影、網絡、手機等大眾媒體或新媒體相比,口述歷史的紙媒出版似乎并不具有明顯的傳播優勢,那么,在傳播載體日益多樣化的今天,口述歷史的紙媒傳播是否還有必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如何繼續發揮口述歷史紙媒傳播的優勢,在堅守住口述歷史作品品質的同時,進一步突破小眾傳播局限,成為大眾青睞的對象呢?
口述歷史需要文本出版物作為載體,這不僅符合口述歷史能將“物傳、言傳、文傳、音傳、像傳等多種形式聚焦一個具體的歷史過程”的傳播特色,也是符合國際慣例的。以紙媒出版物為載體的口述歷史作品,在口述訪談結束之后,不可避免地需要將錄音或影像資料轉換為文字。可以說,口述歷史作品在文字呈現過程中的工作量一點也不少于進行訪談這一環節,口述歷史作品水平的優劣、高低,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呈現過程。那么,怎樣才能確保口述歷史紙媒作品的質量呢?這就需要處理好以下三種類型的關系。
一、真實與規范的關系
口述語言轉化為文字的過程和難度,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簡單,訪談過程中并非所有聲音都適合轉化成文字。一些用語言難以表達出來的副語言,如語氣詞、表情、肢體動作等等,更是如此,而且,即使口述文稿經反復推敲整理完畢后,也有可能出現受訪者不僅要修改,還要增添內容的額外要求,這就涉及口述歷史如何保真的問題;另外,口述歷史也面臨著如何進行規范表達的問題。這些難題都是口述歷史從業者們必須要面對的。
可貴的是,我國的學者們通過實踐與理論研究已經積累了不少經驗。在關于如何處理口述歷史真與美的張力問題上,可以說各有高招,但將“真實”作為首要因素這一點是共通的。在這一前提下,有的學者主張要對文字“進行一定程度的美學加工”。當然,也有學者認為這樣的處理方式有太多后天修飾色彩,不能反映出口述歷史在特定情境之下的特殊之處,而主張盡量不要刪改,“寧留語法十句錯,不讓風格一掃無。對于半截話,寧可留下半截話讓人猜,也不能讓句子補完整了遭人罵”。這種盡可能保留原汁原味訪談內容的做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不過,筆者認為,做口述歷史絕不是為了口述而口述,口述歷史的本質還在于揭示歷史,澄清問題。訪談史料整理過程中在不違背受訪者意愿的情況下進行的文字調整乃至修飾,是可以接受的。劉小萌先生回憶他在整理《中國知青口述史》訪談稿的時候,也談到了要面臨文字的調整、修飾、潤色等工作,他的做法是刪去了主訪人的插話與問話。
口述史料在整理過程中必須時刻有一種整體的把握與評估,如“口述訪談所涉及的一些具有時代背景的歷史事件,其年代與背景的敘述是否正確?某些詞語的用法,在整個口述訪談中,其前后是否具有一致性?如果訪談內容出現前后的矛盾,那么,這些矛盾是如何產生的,原因何在?”
這種對于口述史料的總體性把握的基礎就是尊重。溫州大學的王海晨先生是正在策劃出版的《張學良口述歷史全集》一書的編委會成員,據他介紹,在整理張學良口述歷史的過程中,經多位知名學者、資深編輯及整理組成員會商,將“尊重”作為基本原則之一確定了下來。“尊重”原則最首要的就是“尊重歷史,求真復原”:一是求“口述之真”,以“確保口述歷史的原風原貌、‘原汁原味’、‘原生態’”;二是求“史實之真”,“吸納海內外史學界的研究成果,以注釋方式對記憶性錯誤提供正說,對模糊問題進行考辨,對重大遺漏進行補充,但堅持張學良的話和整理者的話截然分開,不混為一談,整理者的話只能在注釋中表述。”
二、口述與文獻的關系
對于從事口述歷史的歷史學者們來說,不經文獻稽核過的口述史料總是令人不能完全放心的。正如定宜莊研究員所說,“口述因人而異,它是流動的,一次性的,即使是同樣一個人,在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場合,面對不同的采訪者,他的口述也會衍化出不同的版本。文獻卻是穩定的,一旦形諸文字,便很難再修改、再推翻”。史家總以求真為目的,當一部口述歷史作品中頻繁出現史實性錯誤的時候,不管它立意多么深刻、取材多么難得、人物多么重要,那它作為一部史學作品的價值就要大打折扣了。以《文強口述自傳》一書為例,作為文天祥的23世孫,毛澤東的表弟,曾經加入共產黨,不久退黨加入國民黨軍統,官至國民黨中將,后又成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文強老人,在94歲高齡的口述應該是極具價值的。然而這部口述歷史作品卻遭到了海內外的諸多質疑,原因就在于其中存在較多史實錯誤。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沈國凡先生為王文正先生采寫的《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一書。沈先生“每寫一段文字,我都要反復地查看王老提供的原始資料。為了史料的真實性,一些重要的地方,我都請王老以親歷者的身份提供了書面的文字。書稿完成后,又打印出來請王老核對,逐一地過目,并得到他的確認和肯定”。這種艱苦而嚴肅的寫作過程,打造了一本禁得住當下學界考證的口述歷史力作,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可。
可見,在口述歷史的呈現過程中,要注意結合文本資料和訪談資料。整理者不僅需要收集、閱讀、甄別相關的傳記、回憶錄、檔案等,也要關注相關研究成果。另外,還要充分注意與受訪者有關的物品,包括相冊、日記、家譜、紀念品等,這些可能幫助挖掘記憶中更多的信息,也可以幫助證明口述史料的可信度。
文獻與口述史料互證的要求來源于史學求真的需要,但絕不僅僅局限于這一層次。口述歷史的興起在于學界對于傳統歷史敘事的反省,借助于文獻與口述的同與異,學者可以進一步考察其中蘊含的深意。為什么口述者會出現記憶偏差?除了生理意義上的功能衰退以外,是否也有心理學視閾中的自我暗示?人的社會屬性在哪些方面、以何種方式影響著人類的記憶功能?對于中國來說,老人們的回憶又體現出哪些特殊的歷史背景與時代特性?所以,“對于口述而言,文獻是必不可少的基礎和參照物。沒有比較和參照,就談不上研究,更談不上研究的深入。其他學科的學者面對浩如煙海的古籍,很難有進行艱苦繁瑣的爬梳考據的耐心和能力,而這正是史家最見功力的長處”。
三、補遺與建構的關系
我們會遺憾地發現,當下的許多口述歷史作品絕大多數還沒有進入到上述“最見功力”、也最令人興味盎然的層次,更多的還只是將口述歷史視為一種拾遺補漏的方法。也就是說,當下中國的口述歷史還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提供史料的工具狀態,而沒有進入到更新學術理念、轉換學術視角的口述史學的建構層次。
角色定位的高低影響著口述歷史作品的優劣。當下口述歷史的出版物市場的混亂局面一定程度上來源于此,口述實錄的出版領域就非常典型。口述實錄萌生于美國史學界,漸次影響到全球的史學、新聞和文學領域,中國也深受影響。在美國,口述實錄的興起,同口述歷史一樣,是話語權轉移的表現。在中國,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是其中的優秀之作,但是,在近些年新涌現出的口述實錄作品,許多既缺乏文化歷史的長久積淀,也缺乏時代精神的深度開掘,貶損了口述實錄的價值。
如果從更深層次的時代精神層面來進行反思,我們會發現,低質量口述實錄作品的大量涌現,是整個社會都陶醉于其中的感性至上、理性缺失的文化氛圍造成的。在這種文化背景之下,口述實錄的創作者和理論工作者更應該對于這種文體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理想”進行深入思考與探索,發揮出口述歷史作品的真正價值。
當然,口述實錄在運作機制上的成功經驗也非常值得借鑒。有學者為口述實錄類欄目的改革提供了不同的模式選擇,對于口述歷史文本作品的呈現與傳播都很有借鑒意義。如“華爾街日報模式”,該模式對讀者獲取信息采用免費與收費相結合的方式。即刊載于網絡的事件性新聞報道免費開放,而有深度、有分析、有見解的財經報道必須通過網上付費方式或購買報紙獲得。可見,即便在數字化時代,口述歷史文本的傳播,不必糾結于某一固定的形式,而應該多方借鑒,在互相對比中取長補短,從而形成良性發展局面。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思想政治課理論教研部)
[1]劉祖斌.口述歷史的傳播學分析[J].學習與實踐,2007(6).
[2]熊衛民.試論口述史文章的仿真度[J].中國科技史雜志,2009(3).
[3]王海晨,杜國慶.影響口述史真實性的幾個因素——以張學良口述歷史為例[J].史學理論研究,2010.
[4]劉小萌.中國知青口述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8-9.
[5]李向平,魏揚波.口述史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41.
[6]郭俊勝,胡玉海.張學良口述歷史研究[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335.
[7]定宜莊.“天子腳下”的百姓生涯——關于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J].博覽群書,2010(2).
[8]沈國凡,王文正.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317.
[9]孫春旻.口述實錄:話語權的挑戰[J].當代文壇,2010(2).
[10]馬慶.口述實錄類欄目的困境與選擇[J].新聞前哨,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