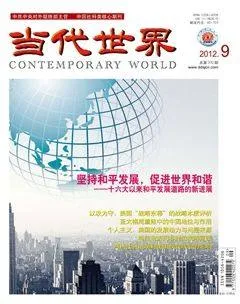關于中國外交戰略一些問題的探討
2012-12-29 00:00:00王嵎生
當代世界 2012年9期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以及美國戰略重心東移步伐的加快,加之日本和幾個東盟國家不斷制造島嶼爭端,中國外交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但機遇也空前大好;形勢錯綜復雜,任務繁重而艱辛。總體說來,現在中國周邊形勢比建國以來任何時候都好,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具魅力。但由于美日一個“絕不做老二”、一個“不甘心做老三”思想作祟,太平洋的水被攪渾了,已經不那么太平了,好像“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國處于“C”型甚至“O”型包圍圈。
形勢決定任務,任務決定政策。任何國家的外交戰略(政策)都離不開它的社會屬性和基本價值觀。中國當然也不例外。目前,國內外專家學者都很關心和重視中國的外交戰略,眾說紛紜。如韜光養晦戰略“已經過時”,現在“應該大有作為”;應該重新考慮是否仍要繼續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需要重新評估“不結盟”政策的利弊,啟動“準結盟”或“半結盟”政策;中國外交“缺乏風骨”,“大國應該有大外交”,等等。作為一己之見,筆者希望就上述問題與有關專家學者進行探討。
“韜光養晦”是不是“戰略性的”,是不是“已經過時”,現在是不是應該“大有作為”了?
就經典意義上的“韜光養晦”來說,它是弱勢群體或個人圖謀霸業和最終擊敗敵人的“策略”,或曰“權宜之計”。在這方面,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最為成功,劉備也是很好的例證。但鄧小平同志提出“韜光養晦”的時代背景和中國的社會屬性已大不相同。外交部一直把它翻譯為“to play low profile”(低調處理),并非偶然,意思是說,要謙虛謹慎,不要張揚和鋒芒畢露。而且,鄧小平講這番話時,緊接著還特別提到要“永不稱霸”和應該“有所作為”。因此,絕不是像某些人所認為的,鄧小平之所以告誡我們要“韜光養晦”,是因為中國太弱;現在中國的GDP 已經是“世界老二”了,綜合國力已大大提高,豈能墨守成規,繼續搞什么“韜光養晦”;中國應該在世界上“大有作為”,“該出手時就出手”。這是很大的誤解。
“韜光養晦”是現代中國的長期戰略方針,是由中國社會屬性決定的,也是中國構建“和諧世界”和“不稱霸”,以及“和而不同”、“平等伙伴關系”等一系列價值觀所決定的,并非是一種策略。它同“有所作為”是辯證統一的。過分拘泥于“韜光養晦”,容易導致“無所作為”;過分強調要“大有作為”,咄咄逼人,就可能影響乃至破壞中國外交大局,也是不合適的。比較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增強韜光養晦意識,積極有所作為”。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特別是自己的周邊,應該也必須“積極有所作為”。但我們必須謹記三點:一是要“審時度勢”,充分評估可能性與可行性;二是要不忘“總體戰略”,以及時代的訴求;三是要注意政策和策略的運用,力求“不戰而屈人之兵”,所謂“上兵伐謀”。總說要“大有作為”,盛氣凌人,動不動就想“教訓”人家,并不可取。
以現在亞太地區形勢為例,美國正加快戰略重心東移的步伐;日本“不甘心做老三”,企圖“借力”美國,乘順風船,緊密配合;菲律賓和越南也制造事端,不斷造勢。顯然,它們就是要把太平洋的水攪渾,刺激和遏制中國,挑動對抗。
面對這種形勢,有人主張“對著干”,“殺出重圍”,教訓一下某某國家。殊不知,如果真“對著干”,可能正中奸計。中國高度警惕和應對一系列事端,“穩坐釣魚臺”,一方面著力提高軍事實力,以防萬一,同時強調要顧全和平與發展大局,采取“以柔克剛”和“釜底抽薪”的方針。這并非是示弱,而是新形勢下的“綿里藏針”。有關方面都十分明白,中國主張構建“和諧周邊”,但有其不可侵犯的“紅線”,必要時可能會“先禮后兵”。美國現在是在虛張聲勢,后顧之憂頗多。日本等幾個國家最多不過是挾洋自重。它們可以把太平洋的水攪渾,但掀不起大浪,成不了氣候。
中國是否應該放棄或者至少
調整“不干涉內政”原則?
“不干涉內政”是《聯合國憲章》核心原則之一,也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一大要素。它是弱小國家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有力武器。中國政府一貫堅持和維護這一原則。有人說,過去我們國弱民窮,怕別人干涉內政;現在強大了,還怕什么?該干涉時就要干涉,不必前怕狼后怕虎。這種想法不僅有違《聯合國憲章》精神,也不符合中國的社會屬性和行為準則,更容易把中國置于強權政治國家的行列,并為敵對勢力利用。
當美國媒體放出試探氣球,宣傳“中美共治”(G2)時,中國有些學者認為,可以考慮和嘗試。這引得當時一些發展中國家反應十分強烈,說中國過去同它們站在一起,現在要伙同美國一起來“共治”它們了。所謂“共治”的“治”,實際上就含有“干涉內政”的意味。中國政府理所當然地拒絕了。
冷戰結束后,美國圖謀建立“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強力推行它價值觀旗號下“保護的責任”,宣傳“不干涉內政原則過時論”,提出“人權高于主權”,主張所謂“人道主義干預”,實行“新干涉主義”。20世紀末,美國和北約發動的科索沃戰爭就是典型的例子。21世紀第一個十年里,美西方在中亞等地區推行“顏色革命”也是很好的例證(雖然很少成功)。2011年利比亞戰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它們名曰“保護平民”,“反對濫殺無辜”,實際上它們在利比亞造成的死亡人數大大超過了卡扎菲,有過之而無不及。
現在,美西方又想在敘利亞故伎重演。它們打著“保護平民”的旗號,企圖再次推行“新干涉主義”和“政權更迭”。奧巴馬總統早在2011年下半年就公開聲稱,巴沙爾總統“已經失去了合法性”,必須下臺,好像奧巴馬成了敘利亞人民選出的“代言人”。2012年以來,美國和個別歐洲領導人也不斷叫嚷:巴沙爾必須下臺。他們表面上支持安南聯合特使六點和平計劃,實際上陽奉陰違,以各種方式支持反對派,全面打壓敘利亞政府。敘利亞局勢之所以不斷惡化,死亡人數和難民日益增多,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和北約一些國家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使用否決權,在安理會對涉及干涉內政的決議大會上投反對票,是中國維護《聯合國憲章》原則、勸和促談的表現,有利于敘利亞問題的政治解決,不怕美西方的無理指責。這也是中國在新形勢下的“積極有所作為”。
中國應放棄“不結盟”政策,準備結盟或“準結盟”嗎?
“不結盟運動”是在冷戰和兩霸爭奪時期應運而生的。它反對結盟對抗,反對兩霸爭奪世界,為維護世界和平和國家主權與民族獨立做出了杰出的貢獻,至今它仍然具有獨特的生命力。當時,最有代表性的結盟是北約和華約,其次是美日安保條約。“美蔣共同防御條約”也是一個,后來中美建交時,美國被迫廢除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也是一個,后來隨著中蘇關系惡化和蘇聯解體,也就等于“廢了”。中國一直是“不結盟運動”的觀察員,自始至終支持“不結盟運動”。
冷戰結束后,華沙條約解體,北約本已失去存在的意義。但美國和一些北約國家的冷戰思維仍陰魂未散。美國奉行“東擴西進”政策,把北約邊界推進到俄羅斯的大門口;把美日安保條約的影響一步一步推向中國周邊,近年來更是咄咄逼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些人沉不住氣了。有專家學者認為,中國正在“被包圍”,處于“C”型甚至“O”型包圍圈,應該考慮“結盟”對抗,爭取主動。
問題是,現在時代不同了。美國繼續推動和加強“結盟”,不得人心。中國順應和平與發展的訴求,主張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和構建和諧世界,首先就占據了“道義制高點”,可以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和“新安全觀”的親和力,巧妙應對美日等國的“軟實力”和“硬實力”。如果我們也開始搞“結盟”或者“準結盟”,同美日或北約“分庭抗禮”,那就勢必要在全球范圍內,導致一場破壞性的“新冷戰”,不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潮流,違背世界人民對新世紀的期盼。
當然,“不結盟”不等于不加深合作。拿中國同美國的關系來說,中國不贊成G2,主張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但近期以來,美國對中國一直是“好話與狠話齊飛”,“兩面下注”。中國同俄羅斯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顯然不同。十多年來,已有了全面深入的發展,實際上已是冷戰后“新型大國關系”的典范,雙方及時就重大國際安全問題進行溝通和磋商,相互支持,彼此都十分注意關照對方的核心利益。但雙方都不主張結盟和不必要的對抗。上海合作組織雖然一致主張不結盟,不針對第三國,不對抗,但在反對三股惡勢力方面,它們是緊密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在這種情況下,“結盟”的意義何在?中國應同誰“結盟”?誰又想與中國“結盟”?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外交缺乏“風骨”
和“大戰略”嗎?
新中國建立60多年來,中國外交雖然也走過一些彎路,有過一些失誤,但總體上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主張建立更加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從反帝反殖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反對霸權主義和冷戰,到主張和平與發展、合作共贏、國際關系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再到“新安全觀”、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構建和諧世界與和諧周邊,中國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戰略都是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從“和平共處”到“和諧共處”是時代變遷量變進程的產物,是中國大外交“更上一層樓”的體現,是一面鮮艷的旗幟。
當今世界,很顯然,有兩個“大外交”戰略在悄悄博弈:一個是美國要建立其價值觀基礎上的“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主張“人權高于主權”,打著“反恐”和“新干涉主義”旗號,對異己國家不斷搞“政權更迭”;一個是中國要構建中國“和而不同”哲學思想基礎上的“和諧世界”,主張國際關系民主化,發展模式多樣化,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美國大外交的關鍵詞是“領導”和“絕不做老二”。中國大外交的關鍵詞是“平等伙伴關系”和“合作共贏”。這種博弈可能要長期存在,甚至要持續一個歷史時期。我們的時代究竟向什么方向發展,新世紀和平與發展的前途能不能實現,中國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世界人民將在實踐中作出正確的選擇。
(作者系外交部前大使、亞太經合組織前高官)
(責任編輯: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