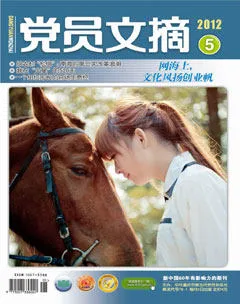給農村“松綁”
用100天跑完224個村子后,鄧偉根組織人員拿出一套農村綜合體制改革方案,并付諸實施。這套改革方案被概括為“六個轉變”,其目標是在保護農民權益的前提下,破解城鄉“二元”治理的難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為農村“松綁”。
農村的問題很多,必須從根上解決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在全國的區縣中,南海的經濟總量排在靠前位置。這里的農村,很早就被滾滾的經濟大潮卷入現代化進程中。
2010年7月,鄧偉根到這個經濟強區走馬上任區委書記。
鄧偉根是產業經濟學博士,步入仕途后,他做過八年鎮黨委書記,干過六年區長、區委書記。鄧偉根到南海之初,很多人猜測,這里一定會改革,突破口則很可能是他最拿手的產業經濟。
改革如期而至,但抓手卻并非產業經濟,而是農村。
上任沒多久,鄧偉根就一頭扎到農村調研。在100天內,他跑遍了南海所有的村,寫了十多萬字的調研日記。224個村跑下來,他乘坐的中巴車四個輪胎全廢了。
就在農村調研途中,鄧偉根和他的同事們醞釀了如今正在實施的“六個轉變”的改革方案。方案最終擬出,經集體討論修訂后,形成《南海區村(居)黨組織工作細則(試行)》、《南海區經聯社工作細則(試行)》、《南海區股份合作經濟社工作細則(試行)》等九個文件。“六個轉變”的旨歸,在這些文件中得以細化。
“六個轉變”分別是指:農村體制由“政經混合”型體制向突出核心、“政經分離”型體制轉變,社會管理從農村管理型向城市社區型轉變,農村集體資產從“享盈不負虧、集體分紅型”向“自主經營、盈虧共擔”的風險經營型轉變,村民社會服務從“無償福利型”向“有償分擔城市管理型”轉變,農村居民住宅從傳統單家獨戶型向現代社區公寓型轉變,農村居民的福利保障從不穩定的分紅式保障向城鄉統籌式的穩定的社會保障型轉變。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評價,“六個轉變”的核心在于“分權”,即“把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資源配置方式分開”。
而“分權”的第一步,就是農村的“政經分離”,即自治職能與經濟職能的分離。
集體經濟組織“綁架”了黨組織和自治組織
南海一直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急先鋒”。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不久,南海農村的村集體就紛紛創辦集體企業。于是,農民剛剛分到手的土地,又自愿被集中起來使用。
“土地和收益分配逐漸成為大問題。”當初的見證者、南海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何享業說。在他看來,土地問題集中在土地性質的改變,以及土地污染等方面。另外,分配機制也不健全,常有村民為此爭論不休。
在此背景下,南海于1992年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思路是沿著股份合作經濟進行,即將農村土地的承包權和使用權分離,將承包經營權作為股份,量化到全體農民,使農民成為股東,實行股份分紅。
在南海歷史上,此舉被稱為南海農村改革的“二次突破”。
改革很快便見成效,并被廣東省作為樣本推廣。后來,南海又推出一些配套措施,以完善1992年的改革。
“回過頭來看,當時的改革方案實質上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改革不徹底,留下很多后遺癥。”何享業說。
最大的一個“后遺癥”,就是“政經合一”。南海農村的股份制改造完成以后,村一級的集體經濟“經聯社”社長,通常由村黨支部書記擔任,而村支書多兼任村委會主任(通稱“一肩挑”);小組一級的“經濟社”社長,則由小組長擔任。也就是說,村一級黨組織、自治組織與集體經濟組織“三位一體”。
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實施以來,這個“后遺癥”暴露出來的問題更加突出。一些人為了控制集體經濟組織,不惜在選舉中“大展身手”。
“由于是‘一肩挑’,監管就成問題,免不了有暗箱操作的事情發生,也容易導致貪腐行為。”南海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可禮說,也是由于“一肩挑”,村(居)“兩委”的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職能有所弱化,跟不上南海農村快速發展的需求,“村干部都在跑項目,發展經濟,哪有空管村里的事?”
這種現象,被鄧偉根稱為“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綁架’了農村的黨組織和自治組織”。
村干部回歸社會管理和服務,經濟組織回歸市場
從2011年下半年起,三年一屆的村委會陸續換屆。南海區的第三次農村改革就在此時全面啟動——“松綁”開始了。
去年年底的村委會選舉,與以往歷屆的選舉并無不同之處。但是,在村委會成員當選之后,有股權的村民又投票選出村組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成員。
早在2004年,南海各村(居)就將股權固化到每一個有資格的村民頭上。而這些“股民”在“政經分離”的改革之前,從未獨立選舉過村組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班子。
為徹底解決“后遺癥”,在此次出臺的改革方案中,明確規定村(居)黨總支部書記、村(居)民委員會領導成員不能與集體經濟組織交叉任職。
余維生原是南海西樵鎮太平社區居委會委員,為競選村經聯社社長一職,他不得不辭去居委會委員的職務。像他這樣的人還有不少。
目前,南海的村組兩級集體經濟組織已全部完成領導成員選舉。
在南海的制度設計中,“政經分離”,首先要實現自治職能與經濟職能之間的分離,以確保集體經濟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擾,公開透明,按市場規則運行。如此一來,即可實現基層組織的各自“回歸”,村委會干部回歸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上,而經濟組織則回歸到市場。
“以前當村支書的時候,一門心思放在發展集體經濟上,顧不上村里的事。不發展經濟,股民們罵;不管村里的事,股民們還是罵。”南海區桂城街道平東社區黨委書記梁錫棋說。他改革前“天然”擔任集體經濟組織的負責人,卸任集體經濟組織的負責人后,他感覺“松了一口氣”,再不用擔心挨罵。現在,他把以前用來跑項目的精力全部投到社區管理中。
“分權”還意味著監督。改革后,基層“兩委”領導成員仍是村集體經濟理事會成員。他們負有監督及建議的義務,但沒有決策權。
為確保集體經濟的平穩安全運行,南海區還建立了集體經濟“財務監管平臺”和“集體資產管理交易平臺”,從制度上確保集體經濟資產運行的公開透明。
“財務監管平臺”完全實現網絡化運行,村(居)及集體經濟組織的資產運營、財務收支等一目了然。每個村(居)都有自己的賬號和密碼,任何村民都可索取。平臺的終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權限,可對資金運行實時監管。一旦發現問題,便可核查,“無一漏網”。
“集體資產管理交易平臺”則要求,達到規定額度的集體資產必須進入交易平臺交易。“一切都在陽光下進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暗箱操作”。
社會經濟要從“無感增長”到“有感發展”
農村的“政經分離”只是南海農村綜合體制改革邁出的第一步。“必須實現社會經濟從‘無感增長’到‘有感發展’的轉變,才算真正完成農村的綜合體制改革。”鄧偉根說。
所謂“有感發展”,即讓社會成員感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變化。為實現此目標,南海加大對民生的投入力度。僅2010年,南海用于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就達80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80%。
然而,由于農村面積大、村民居住分散,要想全面覆蓋,顯然不可能。因此,“村改居”(村委會改為居委會)、讓村民“持股進城”便出現在南海的系列改革中。
“這不僅僅是名稱的變化,居委會可以‘名正言順’接受財政投入,有助于打破城鄉‘二元’治理模式,真正實現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參與此項改革的張可禮說。
“村改居”后,居委會的社區服務中心,即政府在基層的延伸系統,其職能也將與政府的一些部門對接。農民要辦事蓋章,完全不必像以前一樣,跑到鎮政府甚至區里。農民的身份也會發生變化,不再是農民,而是城市居民,能享受到城里人所有的福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如此“惠農”的政策,也要采取民主表決形式,同時保持“六個不變”,即管轄范圍不變、“兩委”班子職數不變、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產權權屬不變、集體資產的權益不變、村民福利不變以及計劃生育政策不變。
目前,南海已有一半的村委會改為居委會。據反饋,“滿意度很高”。
“我們過得比城里人還好。城里人該有的福利,我們都有了。我們還有分紅,村里還有各種補貼。”常會有一些“村改居”后的居民帶著炫耀的口氣說。
顯然,農民的福利保障,正在從不穩定的分紅式保障型向穩定的城鄉統籌式社會保障型轉變。這正是作為南海改革基調的“六個轉變”中的一個。
“這才是開始,還要不斷完善,得膽大心細。”關于南海的未來,鄧偉根在繼續構想著。
(摘自2012年3月7日《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