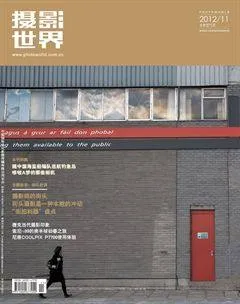街頭攝影溯源
2012-12-29 00:00:00史蒂夫·雅各
攝影世界 2012年11期




概括地說,歷史上的城市攝影作品有兩種風格。一種是整體、全景式地展現(xiàn)城市景觀,這類作品風格意在表現(xiàn)城市建筑及其周邊的自然環(huán)境,其中幾乎沒有人的存在。在攝影發(fā)展的初期,這無疑是由于攝影技術(shù)方面的限制造成的。然而就是在這樣城市攝影的早期階段,對美感和藝術(shù)感的追求促使攝影師們開始拍攝城市的各種景觀,有些注重表現(xiàn)建筑的幾何線條,有些拍攝城市的光影,也有些通過照片表達恐懼、擔憂和城市的冷漠。
另一種城市攝影作品的風格則是從街道的視角來拍攝照片。如20世紀初攝影師尤金 · 阿杰特的作品。他曾經(jīng)拍攝過一組照片,用一個城市漫游者的視角,表達了平日里喧囂的法國巴黎街道幽靜、神秘的一面。這些照片中展現(xiàn)出來的巴黎,似乎不再充滿人間煙火,而更像是夢中的城市。他拍照基本都是采用很長的曝光時間,所以照片里沒有人。就算有,也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某些地位顯赫的現(xiàn)代城市學者,如瓦爾特 · 本雅明,認為這種風格表現(xiàn)出了真正的城市景觀。在人們看來,從一名漫游者的視角來拍攝城市能夠很好地體現(xiàn)快節(jié)奏的都市生活和城市交通。與旁觀者不同,漫游者以一種藝術(shù)的眼光凝視城市,視角超脫表面的世俗,形成一幅幅定格的畫面。用詩人波德萊爾的話說,漫游者的眼光可以在稍縱即逝中發(fā)現(xiàn)永恒。于是當時的攝影師常以漫游者的視角來創(chuàng)作,將充滿活力的城市提煉成為一系列視覺印象。
“有偷窺癖的漫步者”
然而,這些街頭攝影師并非全都像阿杰特那樣用寂靜的方式表現(xiàn)喧鬧的城市。相反,很多20世紀的街頭攝影師記錄下了城市生活動感多彩的景象,以表現(xiàn)城市在高度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千變?nèi)f化。實際上,這種從城市生活的角度記錄城市喧囂的攝影作品早在19世紀就出現(xiàn)了,如查爾斯 · 內(nèi)格雷就拍攝過表現(xiàn)街道和城市擁擠的作品。隨著便攜相機的普及,街頭攝影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蓬勃發(fā)展。保羅 · 馬丁、亨利 · 齊勒、喬治 · 亨德里克 · 布雷特奈和阿諾德 · 金瑟等人都分別拍攝過倫敦、柏林、阿姆斯特丹以及舊金山的街道。另外還有許多非專業(yè)攝影師也在拍攝紐約、巴黎這樣的大城市。盡管這些街9076c52616933d761ec78d18b44c1188頭攝影師的拍攝風格各有不同,但他們對強調(diào)自然、紀實的街頭攝影美學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當時,街頭擺拍平面模特的傳統(tǒng)手法仍然有人在用,但是這些攝影師們同時也在抓拍城市中轉(zhuǎn)瞬即逝的瞬間,因為有很多典型的城市生活場景是即時的、不可擺拍的。這些攝影師注重捕捉被攝體自然、隨意的一面,并希望被攝體可以忽略攝影師自身的存在。街頭攝影師有時不僅僅是一個城市的漫游者,還會是帶著袖珍便攜相機偷拍城市的“有偷窺癖的漫步者”。偷拍在街頭攝影的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從阿諾德 · 金瑟鏡頭下的舊金山唐人街和沃克 · 埃文斯的地鐵人像等作品都不難看出,他們是用袖珍便攜相機偷拍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攝影師熱衷于觀察和表現(xiàn)城市中不為人知的底層人士的生活。為了表達世紀之交政治改革的進步力量,雅各布 · 里斯和路易斯 · 海因拍攝的作品就常常直截了當?shù)卣宫F(xiàn)這樣的場景。
20世紀早期的街頭攝影師創(chuàng)造了如此隨意的紀實美感,這樣的方式也恰好非常適合表現(xiàn)城市生活。城市生活的節(jié)奏在一幅幅紀實照片中被展現(xiàn)出來,有些照片甚至打破了傳統(tǒng)的構(gòu)圖并使用含蓄的模糊手法拍攝。到了20世紀30年代,伴隨一批使用徠卡相機的攝影師的出現(xiàn),這樣的風格達到了高潮,如亨利 · 卡蒂埃-布列松和安德烈 · 柯特茲。布列松著名的“決定性瞬間”的概念就包含了現(xiàn)代城市具備的特點:只有在城市里,才會有如此多的瞬間抓拍的機會;只有生活在城市里,經(jīng)歷了城市快速變化的攝影師,才會有足夠的經(jīng)驗和反應速度來抓拍城市生活的瞬間。布列松將抓拍與優(yōu)雅結(jié)合在一起,將自己對城市題材條件反射般的敏感與嚴謹?shù)臉?gòu)圖結(jié)合在一起。柯特茲也是這樣,他會用相對正式及略微抽象的方式來表現(xiàn)某些吸引人的場景。在一些作品中,柯特茲將德國現(xiàn)代攝影中建筑的拍攝手法與街頭攝影結(jié)合在一起,著名攝影師沃克 · 埃文斯也曾經(jīng)用到過這樣的手法。
“紐約派”的出現(xiàn)
眾所周知,在二戰(zhàn)以后的數(shù)十年里,布列松成為了美國和歐洲街頭攝影的標志人b916a922c456eb9df8abd5512bb533e9物。他影響了20世紀四五十年代大量的攝影師及他們拍攝的關(guān)于法國巴黎的照片。巴黎被稱為“街頭攝影的搖籃”,在世界大戰(zhàn)前,包括布列松本人在內(nèi)的許多攝影師都拍攝過這座城市。戰(zhàn)后,巴黎的街頭生活也成為了大量攝影書籍的主題。布列松還影響了藝術(shù)策劃人簡 · 利文斯頓,后者在她的研究著作中把1936年至1963年間姿態(tài)各異的美國攝影師統(tǒng)稱為“紐約派”,只因他們大多以紐約為根據(jù)地。以席德 · 克勞斯曼、埃里克西 · 布羅迪維奇、 黛安 · 阿勃絲為代表的“紐約派”攝影師拍攝了紐約貧民區(qū)、曼哈頓下東城區(qū),以及光怪陸離的時代廣場等許多地方人們的生活。這些作品不僅表現(xiàn)了如荷蘭建筑師雷姆 · 庫哈斯所說的“具有擁擠文化的曼哈頓風格”,也呈現(xiàn)出許多紀實新聞攝影的慣用手法,如使用小型相機、利用現(xiàn)場光、漫游者視角和偷拍等等。所有這些攝影師也注重作品中的人文內(nèi)涵。他們拍攝的題材主要是人們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而非空蕩蕩的城市景觀。當時,大多數(shù)攝影師使用35毫米相機來進行街頭攝影,追求照片能展現(xiàn)出某個獨特瞬間。受當時存在主義及文化環(huán)境的影響,這些作品主要反映了城市生活的忙碌和變遷。雖然他們受布列松影響很多,但是他們也會使用非傳統(tǒng)的構(gòu)圖、傾斜的拍攝角度及夸張等拍攝手法。其中,奧地利裔攝影師莉賽特 · 莫戴爾為了展示城市生活的繁忙,將相機放在離地面很近的位置,拍攝過往人群的腳。這樣的拍攝角度讓人看照片時覺得當時的街道是如此擁擠,以至于攝影師都被擠倒了。
與當年展現(xiàn)巴黎生活的街頭攝影作品相比,“紐約派”攝影師的都市攝影作品風格更加體現(xiàn)了緊張和快節(jié)奏的特點。在維加(阿瑟 · 費利格)、 弗蘭克 · 奧斯卡 · 朗森和威廉姆 · 克萊因的作品中,街道不是人們友好交往的地方,而是充滿冷漠和異化的地方。“紐約派”攝影師的這種特點在20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受到蓋瑞 · 維諾格蘭德和黛安 · 阿勃絲的推崇。維諾格蘭德的整個攝影生涯都在苦苦琢磨人的面部表情、動作和周圍環(huán)境的構(gòu)圖。他魯莽地拍攝在公開場合的某個人或某對夫婦,但又讓他們顯得與周圍人不那么合群。他并不樂于拍美的事物,而是更喜歡拍攝戲劇性的場景、富有張力的矛盾和有故事性的畫面。事實上,他似乎以拍攝讓觀眾覺得不舒服的東西為樂。在他的照片里,經(jīng)常可以看到一種玩世不恭和反嚴肅的黑色幽默。構(gòu)圖也總是顯得隨意而無規(guī)律,水平線常常是歪的,而且通常用廣角鏡頭(但他從沒用過超過21毫米的超廣角)從平視角度拍攝。這種風格的照片表現(xiàn)出的人與城市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與五十年代的昏暗風格不同,前者犀利、直接,后者則傾向于用霓虹燈、反光或者糟糕的天氣來烘托氣氛。維諾格蘭德強調(diào)自然的現(xiàn)場,與黛安 · 阿勃絲一樣,他利用了近似偷拍的方式。不同的是,戴安 · 阿勃絲選擇正視城市社會中那些被遺棄的人。
逆城市化下的街頭攝影
維諾格蘭德和阿勃絲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此類街頭攝影登峰造極的代表,同時又可以被看作是此類街頭攝影的終結(jié)。隨著城市的發(fā)展,空間在變化,社會也在變革,這給街頭攝影帶來了改變。隨著郊區(qū)的發(fā)展,逆城市化現(xiàn)象開始出現(xiàn)。到了20世紀晚期,城市和其周邊地區(qū)的環(huán)境已經(jīng)沒有太多差別。在城市擴張的時代,城市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地點,而是一種生活環(huán)境。原來城市中的街道和公共場所——曾經(jīng)街頭攝影師的熱門拍攝區(qū)域——漸漸地被郊區(qū)化、逆城市化和城市改造所改變。自20世紀五十年代末期起,由于街道的變遷和街頭生活的變化,街頭攝影也漸漸失去了其原本的味道。攝影師伊奇斯鏡頭下的巴黎塞納河畔,河堤已經(jīng)被公路所占據(jù),碼頭上也滿是旅游者和流浪漢。工人一度是巴黎街頭攝影作品的主角,他們也慢慢地離開城市,前往郊區(qū)去建設(shè)新的房屋。布列松,維利 · 羅尼以及羅伯特 · 杜瓦諾曾嘗試著去追逐工人的腳步,前往郊區(qū)拍攝,然而令他們驚訝的是,原本在街頭拍照時,人們與周圍環(huán)境能夠互相融合;而在現(xiàn)代郊區(qū),人作為個體常常在巨大的新建筑或者大片荒蕪的土地前顯得渺小異常。
這樣的變化,使六七十年代末的街頭攝影喪失了其象征性和代表性。街頭攝影所關(guān)注的市井生活隨著城市的變化而改變。人們在空間意識逐漸增強的同時也更加注重自己的隱私,因此在20世紀九十年代,一些街頭攝影師不得不將目光轉(zhuǎn)向了主題公園和旅游景點。
除此之外,城市居民多樣化帶來的多元文化群體也在不斷影響著傳統(tǒng)的城市社區(qū)和公共場所。城市逐漸成為求同存異的地方。不同民族、國家的人在這里融合。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一批街頭攝影師開始拍攝這些多元題材下的城市生活。他們打破了固有的價值觀,開始關(guān)注犯罪、金融危機、種族矛盾以及個體家庭的困惑。受到阿勃絲、弗瑞德蘭德和維諾格蘭德等人的影響,一些攝影師如布魯斯 · 達維森、拉里 · 克拉克、南 · 戈爾丁拍攝了許多風格怪誕、寓意深刻、甚至有些“極端”的題材。他們被這樣的題材深深吸引著,照片的主角經(jīng)常是受人忽視的弱勢群體或者社會的邊緣人物,然而他們卻忽視了整個城市的生活概況。可以說,一些紐約街頭攝影師如拉里 · 芬克、杰夫 · 墨梅斯坦、杰夫 · 杰克布森等人的作品展現(xiàn)的更多是曼哈頓區(qū)中具體的、私人的細節(jié),而傳統(tǒng)的、標志性的曼哈頓生活場景卻鮮有出現(xiàn)。照片里展現(xiàn)的城市不再是大都市,而是由許許多多細節(jié)碎片所拼湊起來的,時而殘酷、時而滑稽、時而古怪的城市。
傳統(tǒng)街頭攝影的終結(jié)
傳統(tǒng)街頭攝影的終結(jié)不僅僅是由社會和時間因素決定的,還涉及到新的攝影審美理論的發(fā)展和變化。一些觀念攝影師,如馬撒 · 羅斯勒、漢斯 · 哈克、阿蘭 · 賽庫拉否定了原來街頭攝影的漫游者視角,發(fā)明了新的攝影技法來展現(xiàn)塑造當今城市的社會機制。傳統(tǒng)街頭攝影對即時特點的推崇也受到了一些觀念攝影師甚至非專業(yè)攝影師的質(zhì)疑。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總體上來說城市攝影的重心從地域上的城市中心地區(qū)轉(zhuǎn)向郊區(qū)及其他周邊地區(qū)。同時期,攝影技術(shù)和攝影審美也在不斷變化。熱情洋溢的、所見即所得的街頭攝影風格與大畫幅的、全景展示郊區(qū)人口不那么密集的攝影相映成趣。過去四十年中,新的風格引領(lǐng)著城市攝影,如觀念藝術(shù),大場景攝影,新德國攝影等等,它們有時關(guān)注城市外貌,有時關(guān)注具體的建筑結(jié)構(gòu)。極簡主義手法也開始流行起來。近些年來,城市攝影師從傳統(tǒng)的關(guān)注城市生活的街頭攝影風格中跳了出來。
盡管如此,人們也將如今的城市攝影稱為街頭攝影。然而,這些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卻不在于如傳統(tǒng)街頭攝影一樣關(guān)注城市生活。相反,許多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城市攝影師拍攝的城市中的人物肖像缺少了很多傳統(tǒng)街頭攝影中最基本的元素:這些照片里并不展現(xiàn)紀實、瞬間的特征,不存在偷拍或者是旁觀的角度。相反,大量的街頭攝影師采用了大畫幅的城市景觀攝影技巧,喬爾 · 斯坦菲爾德、理查德 · 里納迪、弗朗西斯科 · 喬迪斯、橫溝靜、吉特卡 · 漢斯羅德拍攝的人物經(jīng)常是直視鏡頭。在另一些攝影師,如歐文 · 沃姆的作品中,人物則被拍得好像活著的雕塑。20世紀末期的街頭攝影還出現(xiàn)了畫面設(shè)計和圖像處理的熱潮。杰夫 · 沃爾的作品就充分利用了現(xiàn)代技術(shù)進行創(chuàng)作。因此,追求街頭攝影的紀實性和瞬間性轉(zhuǎn)變?yōu)樽非笄捌谠O(shè)計和后期數(shù)碼處理。沃爾的作品也啟發(fā)了菲利浦-盧卡 · 迪克西亞,盡管后者的作品沒有擺拍,但是風格也與克萊恩和維諾格蘭德的傳統(tǒng)手法大相徑庭。他不使用袖珍便攜的徠卡相機,而是使用大畫幅相機,輔以許多強力的燈光設(shè)備來拍攝街頭的行人(行人走過,觸發(fā)傳感器,引起閃光)。這種燈光可以將現(xiàn)場營造出劇院的光線效果。相似的手法也被其他攝影師使用過,如妮基 · 李、哈娜 · 斯達克、蘇珊 · 拉封、比特 · 斯特羅伊里等等。這些攝影師用模擬的方式記錄街頭的現(xiàn)實感。這類照片的出現(xiàn),也暗示了傳統(tǒng)街頭攝影的自然性得到了突破。就像原本的城市街道被改變?yōu)橹黝}公園、露天博物館或者旅游景點一樣,沃爾和迪克西亞以及其他“反傳統(tǒng)街頭攝影師”對拍攝方式加以創(chuàng)新,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設(shè)計再現(xiàn)了街頭生活,也正反映了一個觀念,即如今人們生活的城市空間其實也是被設(shè)計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