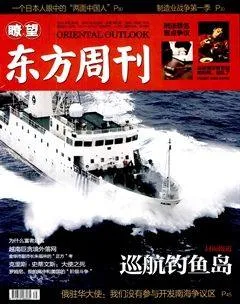羅姆尼、我的高中和美國的“階級斗爭”
這次《華盛頓郵報》揭露的可是羅姆尼和他的高中同學之間“不得不說的那點事”——沒錯,矛頭指向了我和羅姆尼共同的高中母校,密歇根州克蘭布魯克中學。
今年5月初,我所在高中的一位忠實的民主黨教師忽然給不少學生群發(fā)了一封標題為“米特羅姆尼,(曾經(jīng)的?)惡棍”的電子郵件,附著一個《華盛頓郵報》文章的鏈接。
原來又是一篇關(guān)于這位羅姆尼先生的文章。作為美國總統(tǒng)大選的共和黨候選人,他的前世今生、陳芝麻爛谷子都被媒體擺在光天化日之下,諸如政治立場多變、“見風使舵”之類。
而老師給我們發(fā)來的這篇文章卻與以往不同。這次《華盛頓郵報》揭露的可是羅姆尼和他的高中同學之間“不得不說的那點事”——沒錯,矛頭指向了我和羅姆尼共同的高中母校,密歇根州克蘭布魯克中學。
作為密歇根最好的學校之一,這所私立學校每年都有畢業(yè)生進入名校。學校在上世紀20年代由底特律的出版業(yè)大亨喬治·布茲出資創(chuàng)辦,高中只是其中一部分,整個克蘭布魯克教育社區(qū)還包括小學、初中、兩所博物館和一個全美排名前三的藝術(shù)學院。
我點開文章鏈接,對羅姆尼的一點好感迅疾灰飛煙滅。原來,他曾在高中生涯中多次欺辱同學,甚至糾結(jié)同伴強行剪掉了一名男同學偏長的頭發(fā),只因為他認為這位同學是同性戀。
氣憤過后,我又回頭仔細地看了看那篇文章,除了揭發(fā)羅姆尼曾經(jīng)的惡棍行徑,文章對我的中學也頗費筆墨。配圖中,學校典雅的庭院、無處不在的青銅雕塑和裝飾華麗的學生休息室一一亮相。這些景物每天我都能看到,從來沒覺得有照片上那般富麗堂皇,其實,那些用了幾十年的沙發(fā)已經(jīng)布滿斑駁的裂紋。再看文章,作者極言學校的“貴族化”,卻沒有提及學校的財政緊張、每年提供給貧困學生的高額助學金,以及現(xiàn)有31%有色人種學生的事實。
看來,這篇文章除了“揭黑”,又再重復“階級斗爭”的老調(diào)——作為官二代、富二代(其父親曾任密歇根州州長、美國汽車公司總裁)的羅姆尼,曾因自稱“中產(chǎn)階級”和大眾套近乎而受盡媒體的冷嘲熱諷。
盡管我的高中同學和老師大多是民主黨奧巴馬的支持者,這下卻也在美國自經(jīng)濟危機以來愈演愈烈的“階級斗爭”中躺著也中槍。“米特,求求你別再給學校丟人了!”一位同學看完這篇報道后譏嘲道。
近幾年,美國政壇中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了“他們”與“我們”的話語方式,窮人也越來越多地把富人看作抽象的敵人。近期最受關(guān)注的美國階級問題恐怕就是“占領(lǐng)華爾街”這個極端事件了。我的學校的校報就曾報道今年5月發(fā)生在學校附近小鎮(zhèn)的“占領(lǐng)”活動,參加示威的有痛恨大資本家貪婪的老年人,也有考上大學卻沒錢上的年輕人。
示威活動無處不在,“階級斗爭”的語言也成了流行詞。一次課上我的一個同學就曾開玩笑對老師說要“占領(lǐng)”教師辦公室,搶走專供那些“1%特權(quán)者”的咖啡、熱巧克力和糖果。
階級間不信任甚至互相痛恨的語言不光被我們用在了日常玩笑里,更成了政治家的口頭禪。奧巴馬就曾使用過“占領(lǐng)”活動中興起的流行詞“1%”,許多媒體也稱羅姆尼為“1%”的一員。一個月前,《華盛頓郵報》的一位寫手也在網(wǎng)站上發(fā)表了“奧巴馬和羅姆尼:美國階級斗爭的兩元大帥”的文章。
的確,美國的貧富差距問題今日已十分嚴重。根據(jù)美國民間組織經(jīng)濟政策研究所的一篇報道,美國最富有的1%享有三分之一的財富。而佩爾研究中心的報道說,美國85%的中產(chǎn)階級覺得保持以前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難,底層人民總要面對交不起賬單、小孩上不起大學等各種困境。
美國何去何從?是繼續(xù)選擇尋求大政府、為窮人提供安全網(wǎng)的奧巴馬,還是換上為富人減稅以“解放資本創(chuàng)造就業(yè)”的羅姆尼?對于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來說,這次總統(tǒng)大選不光要考慮誰更有能力,也要考慮“誰能代表我階級的利益”。
而我所在中學的管理者們,則早已悄悄起草了一封措辭小心的公開聲明,發(fā)到了官方網(wǎng)站上。聲明說,學校對于校友羅姆尼的競選并無太多了解,對其是否參選成功也不做希望與預測,為保護學生隱私也不愿向媒體開放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