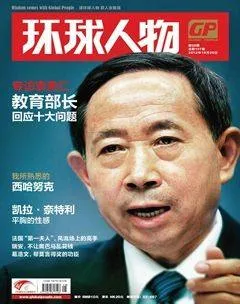花3年拍農民工的回家路
2012-12-31 00:00:00范立欣田亮
環球人物 2012年28期

智利著名紀錄片導演顧茲曼說:“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我們國家現在處在紀錄片大發展的時代,不乏關注歷史、動物、地理方面的優秀作品,但有一點遺憾——我們有相冊了,但相冊里裝的都是“風景照”,不是“家庭照”。等我們的孩子懂事了,看到這個家傳的相冊,發現里面全是《故宮》、《舌尖上的中國》……過300年再拍這些,它依然在那。但農民工、“80后”、“90后”、富二代等,就這個時代有,這就需要紀錄片體現它的力量和價值。
被三組鏡頭觸動
上世紀末,我在電視臺工作,常扛著攝像機外出拍攝。那時正是DV(數碼攝像機)和紀錄片風潮興起的年代,我從小到大一直都在城里,很想知道這個國家最貼近土地的那一層——農村,到底在經歷什么樣的變革,便總拿著DV去拍與農村相關的素材。
我拍的第一個完整紀錄片講的是一個農民工,他就住我家旁邊,靠蹬三輪車掙錢。由于是黑車,他的車兩三個月就會被沒收一次。他整天擔驚受怕,但沒辦法,因為要寄錢回家養兩個孩子。我拍了一年,然后剪輯成25分鐘的短片,那是我跟紀錄片的第一次“戀愛”。這部片子大概只有五六個人看過。
2003年12月,欄目組派我去拍春運的新聞。在整理素材時,3組鏡頭觸動了我:一組是好多農民工在月臺上從車窗爬進火車;另一組是南下的火車,畫面上都是青山綠水;還有一組是北上的列車,看到的則是林海雪原。當時我就覺得身體好像被電擊了一樣——這些農民工從城市奔向四面八方,不久又要回來繼續付出,為的就是一年之后能夠再次踏上列車回家看望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城里人對他們則是一種漠然的態度,甚至鄙夷他們:嫌農民工隨地吐痰,把城市的環境弄臟了;當他們一上公共汽車,城里人就躲得遠遠的……我想,必須要替這些回家的農民工喊出聲音,必須有一個故事是關于他們的。
經過兩年多的準備,2006年8月,已經辭掉電視臺工作的我,一個人跑到廣州,每天早上從廣州東邊坐地鐵到西邊的工廠區,一個工廠一個工廠地找故事、找人物。
我想找的是來自偏遠山區的農民,回家光坐火車還不夠,還要轉汽車、三輪;上有老下有小,孩子最好十四五歲,即將選擇是繼續上學,還是輟學打工。20多天過去了,我終于找到一對夫婦,男的叫張昌華,女的叫陳素琴,來自四川廣安市大安鎮回龍村。他們有一個16歲的女兒,叫張麗琴;還有一個兒子,都在老家讀書。
最開始,張昌華夫婦很害怕,擔心我是騙子,問我要不要錢,我說:“不收錢,但也不會給你們錢,這個故事雖然講的是你們,但折射的是整個農民工的生存狀況。”他們這才答應讓我跟拍。
張昌華很少說話,但自尊心很強。他不愛和我們一起吃飯,雖然每次都是我請客,而且吃的只是簡單的街邊小炒,他也覺得奢侈。不管我怎么跟他說,他還是會和我保持距離。整個拍攝過程中,不管自己的生活遇到多大困難,他從來沒有張口向我尋求過幫助。
是它駕馭我,而不是我駕馭它
很快,第一個春節拍完了,我東拼西湊準備的30多萬元也花光了。2007年年底,我找到了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一位女制片人,她愿意投資,但開出了條件:投資30萬元,要一半版權。我沒有同意。她說:“你若無法同意,我只能不投資。”聽完這句話,我聲淚俱下:“那個農民工的女兒,已經輟學去廣州打工了。農民工夫婦心急如焚,他們送孩子上大學的夢想就要破滅了。我砸鍋賣鐵也得把片子拍下去,等不了,錯過這個時間,故事就沒有了,前邊的付出全部白費,我對不起這個故事。”這位制片人最后還是心軟了:“那好,我私人借給你20萬元,因為我看你這個小伙子是在認真地對待這個事情。”
有了這筆錢,我們順利拍完了2008年春節。對于所有在廣州經歷春運的人來說,那都是一段刻骨難忘的記憶。那一年,南方遭受大雪災,沒有火車進站,幾萬人滯留廣州。張昌華一家三口在站里等了4天4夜,誰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回家。無意當中,我聽到張昌華和一個警察吵了起來。警察說:“你們這些外地人,都跑到我們廣州來干什么呀?”原本安靜的張昌華一下子爆發了:“我在你們廣州打了十幾年工,你們廣州人對我們一點都不好。要不是我們廣安的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廣州現在說不定還不如我們四川好呢!”警察啞口無言。很可惜,由于技術問題,這個場面沒有保留下來。
第二天,我和攝影師跑到廣場邊的高架橋上拍火車站全景,看到的全是人頭。跟著張昌華一家,他們的艱難、苦楚我們都看在眼里,能夠體會一個農民工為孩子和家庭要付出多大代價,忍受多少委屈,而在這一刻,在這個鏡頭里,哪一個人又不是這樣呢?我的心酸一下子乘了幾萬倍。跳出廣州站,中國幾億農民工,哪一個又不是這樣呢?如果再乘以幾億,這種酸楚已不是一個人的心能夠承受得了的。我深刻地感受到,這個故事已經不是我的作品了——是它駕馭我,而不是我駕馭它。
火車站那一幕讓我感覺到的是心酸,張昌華女兒的問題則讓我感到了心痛。
“90后”張麗琴是一個十分叛逆的女孩。她最喜歡外公,2003年外公去世后,她更叛逆了。張麗琴初三畢業那年,張昌華夫婦回老家,她都不喊爸爸、媽媽,僅用“你、我、他(她)”代替。這次來廣州打工,也刻意和自己的同學在一個工廠,避開父母。
回到四川后,張昌華想讓她留下繼續上學,她不愿意,還挑戰父親的權威,甚至在父親面前自稱“老子”。張昌華動手打了她。那個場景反射出很多社會問題:留守兒童、教育、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割裂和矛盾等。它讓你不得不感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讓上億農民進到城里,他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做出巨大犧牲,想換來下一代人社會地位的上升。但是,這種犧牲恰恰不能被留守的孩子所認可。這到底是誰的錯?
人的境遇要能反射時代的精神和紋理
《歸途列車》除了得到艾美獎最佳紀錄片獎,還得到了最佳商業報道獎。外國觀眾可能覺得這個片子反映了一個很深刻的全球化矛盾——東西方發展不平衡。發達國家奉行消費主義,然而他們消費的廉價產品凝聚著發展中國家勞動者的汗水、淚水。我在國外放映時也談過:“你身上穿的牛仔褲是幾十、幾百個終年見不到自己孩子的人做出來的,你覺得它真的只值30美元(約合187元人民幣)嗎?”“如果我們不反思、不改變,依然是買件衣服穿不了幾天就扔掉,那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體制的幫兇,而且自己都沒有覺察到。”
好的紀錄片看重的是人性的價值,人的境遇要能反射時代的精神和紋理。一個導演應該是細膩的人,對生活保持好奇心,很細致地觀察到整天出現但會被所有人忽視的細節。還要放得下很多普通人非常看重的東西,比如名利。接下來,我想拍一部“農二代”的片子,看他們能不能融入城市。可能拍攝過程又是一個3年,但無論付出多少,都值得。
編輯|王晶晶 美編|陳思璐 圖編|傅聰 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