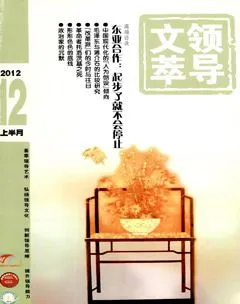中國現代化的“人為創設”傾向
面對當前的經濟困局,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都引起了對國家角色的討論與爭議。經濟學家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里有個觀點:現代化是自發的社會秩序。他批評了建構理性主義,認為理智的人傾向于過高地估計理智,傾向于認為我們必須把自己的文明所提供的優勢和機會,一概歸功于特意的設計而不是對傳統規則的遵從。這種傾向會讓人不由自主地贊成對經濟進行集中計劃和管制。
那么,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是什么樣的?觀察中國近代歷史,就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從19世紀中期,中國的現代化就是一個“理性建構”“人為創設”的過程。
首先,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如果按照中國傳統文明的內在邏輯發展,中國不可能走上現代化道路。因為中國的傳統對于現代化來講,是阻力而非助力,與現代化同步的是對傳統的解構與批判。但是現代化沒有純粹自發,即使是最具原發型的現代國家——英國,也不例外。英國在崛起過程中也滲透著很強的國家印跡。所以,筆者不贊同自由知識分子絕對反對“理性建構”的傾向,因為那樣就會斷絕中國現代化的可能性。
其二,對于后發現代化國家來說,現代化絕不能被認為是某個主體自覺設計、“理性自負”的結果。一個國家在崛起過程中往往會借助于國家力量,但經濟一旦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出現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斯所謂的“國家難題”:國家代表了秩序,只有秩序或可使國家擺脫貧困,但真正達到現代層面的繁榮,則需要另一要素——自由。哈耶克也一再強調,他和社會主義者的分歧并不是出于意識形態或價值選擇的對立,而是由于事實判斷上的不同——問題不在于計劃所設定的目標在道德上是否可取,而是用它所倡導的辦法能否達到目標。
最后,必須承認,自發社會秩序不是盡善完美,甚至會失效,但這種自發秩序的大多數缺陷和失效,多是因為有人試圖干涉甚至阻止它的機制運行,或是想改進它的具體結果。
中國的現代化經驗表明,對物質界面的追求始終是啟動現代化的最根本動力;現代化只是作為一個強國夢的手段,而非目的;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的精英層絕大部分都沒有無條件接受現代化內含的價值理念和制度安排,而是對其進行功能性的選擇和認同。
過去30年的市場經濟改革,中國在計劃與市場之間逐漸偏向于后者。但近幾年尤其在全球通脹的背景下,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存在倒退的危險傾向,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行政干預、經濟管制現象。換言之,就是中國現代化過程存在極度“理性建構”的趨向。
吊詭的是中國老百姓大多歡迎這種政府介入干預,一個顯著的現象——中國的老百姓不大相信“市場”(原因很復雜,最主要是在中國畸形的市場里,尋租、不公現象嚴重),這從一些主張自由市場的中國經濟學家不斷被罵,便略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管制的對象多是外資、民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很少涉及國有壟斷性企業。方便面價格不讓漲,而油價卻在瘋漲(在中國大凡壟斷性行業,談成本是沒有意義的),就是最明顯的例證。這樣的后果便是,大量民間財富向國家壟斷轉移。人為拉大的貧富差距,會進一步造成民間“仇官”“仇富”情緒的蔓延,乃至進一步的社會心態失衡。
“市場里的政府”命題告訴我們,沒有無政府的市場。現代化不可避免理性化的設計,但是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存在著極度的“理性建構”“人為創設”傾向。無論是對于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世界認同,還是國家內部經濟的包容性增長,這都會是一個巨大障礙,值得警惕。
(摘自《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