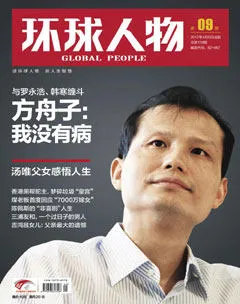陳佩斯的“非喜劇”人生
2012-12-31 00:00:00楊東張卓
環球人物 2012年9期

28年前的春晚舞臺上,憑借和朱時茂搭檔的《吃面條》,陳佩斯成為中國最炙手可熱的笑星,那時他還有稀稀落落的頭發,不過都罩在一頂土黃色的有檐帽子里。1985年,陳佩斯徹底剃了頭發,那頂光亮的腦袋從此成為他最顯著的標志。2012年3月,環球人物雜志特約記者見到58歲的陳佩斯時,他依舊是光頭,胡子有些花白,穿著一年四季不離身的馬褂,腳下一雙懶漢鞋。和他在人們心目中最經典的流里流氣、賊眉鼠眼的“小人物”形象不同,如今的他顯得很深沉,所關注的話題也很嚴肅。
過有底線的生活
陳佩斯最近在忙著“招生”。他所籌建的大道喜劇院喜劇表演培訓中心已進入招生階段,不久之后即將正式開班。“我已經在喜劇的門里了,品到了許多經驗和教訓,而很多熱愛喜劇的人卻還沒摸到門兒,應該把他們領進來,讓他們少走一些彎路。”
說到彎路,陳佩斯自己入喜劇這行也不是很容易。他的父親是著名表演藝術家陳強。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大哥出生時,父親陳強正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訪問,北京來報:老婆生了一個兒子。陳強說:“那就叫布達吧,如果再有第二個孩子,就叫佩斯。”
兒時的陳佩斯不愛學習,成績不好,經常打架。15歲時,他被送到內蒙古下鄉,每日耕作勞動。他回憶:“我半年沒吃過肉,讓父親給我寄錢,父親不給。后來,還是母親給我寄錢了。”為了返城,陳佩斯跟父親學起了表演,吊嗓子,走臺步,這樣才能進文工團,而文工團是當時唯一能調動戶口的地方。不過,去考北京軍區文工團、總政話劇團時,陳佩斯都被刷下來,那個年代,文工團偏愛招收的是唐國強那樣的英俊小生。陳強找到了八一電影制片廠的老朋友田華幫忙,八一電影制片廠答復:“我們這里正缺演匪兵、流氓、地痞的演員,如果他愿意演就來。”
父親陳強回憶:“到第三次考八一電影制片廠時,我才覺得,這個孩子在表演上確實是有才華的。”
后來八一電影制片廠拍《瞧這一家子》,陳佩斯還是沾了父親的光,首度擔綱主演。演完之后的成功是轟動性的,父子倆的對手戲“教英文”成為中國影視喜劇史上的經典橋段。
春晚舞臺,更為徹底地改變了陳佩斯的命運。從1984年到1998年,陳佩斯為春晚貢獻了15個小品。作家史航曾說過:“陳佩斯的小品很少怯口(說方言),不拿殘疾人開玩笑,基本不出現女角。他一直扮演的是不斷變遷的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命運格局。細想起來,這些小品很高級。”1998年的小品《王爺與郵差》是陳佩斯在春晚舞臺上的最后一個作品:郵差陳佩斯梳著馬辮,涂著紅彤彤的臉蛋,興高采烈地拉著王爺朱時茂下臺,那是他在那個舞臺留下的最后一個背影。
自此,陳佩斯告別春晚。在日后接受采訪時,他最不愛多談的也是這個話題。其實內情并不復雜——他跟春晚較真兒,想演些自己的東西;跟央視較真兒,狀告央視出售春晚光盤侵犯他的著作權。
新世紀,陳佩斯自組劇團,投身話劇,制作出《托兒》、《親戚朋友好算賬》、《陽臺》等優秀劇目,并把它們推向二、三線城市,為后來者趟開了路子。有人說,陳佩斯跟《茶館》里的常四爺很像,“都是掙有數的錢,過有底線的生活”。
喜劇是一種人生態度
環球人物雜志:我發現您幾乎涉足過所有的戲劇形式,電影、小品、電視劇、話劇,去年您還演出歌劇《蝙蝠》,客串過梨園戲《董生與李氏》,但所有您演過的劇目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是喜劇。喜劇對您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陳佩斯:它的平民化,喜劇屬于平民。
環球人物雜志:怎么理解?
陳佩斯:喜劇是最接近人的,它和人是零距離的。從藝術形式上,它也是最具人性的。它直接表現人的生命,表現生命的需求。悲劇表現死;而喜劇表現的是生。悲劇一定要摧毀,才能體現出悲情;而喜劇則是建立一個新東西。
環球人物雜志:可以把喜劇理解成一種人生態度嗎?
陳佩斯:可以。古代把喜劇稱滑稽。滑稽本身就是一種態度。按我的理解,“稽”由“禾”、“尤”、“匕”、“日”構成,“尤”是“犬”的變形,“匕”是“人”的變形,“日”代表沼澤。前有狼,旁有禾,后有沼澤,人在其中茫然四顧,往哪走?無處可去,就是困境。滑由“水”和“骨”構成,像洗排骨一樣,骨頭是滑的,但又是硬的。有態度、不妥協,同時又能化解這個困境,這就是滑稽的會意。這兩個字非常準確。
卓別林總結說,所有的喜劇最終都要給角色制造窘境,這是不錯的。但為什么困境就是喜劇呢?其實在創造困境和解脫困境的同時,觀眾從中得到了優越感,獲得了生命的快樂。
環球人物雜志:除了通過觀看喜劇獲得快樂,人們也需要以喜劇的精神來面對生活。
陳佩斯:對,當代人尤其需要這種精神。多少年來,觀眾對悲情戲已經習慣了,只要音樂一慢下來,主持人的調門往下一降,大家都進入悲情的節奏了。其實好的心態,是可以培養的,可是我們往往忽略了。一個社會需要多種心態,最起碼需要兩種,一種是積蓄能量的,一種是釋放能量的。喜劇精神屬于后者,它能夠幫人建立一個基本的思想方法——每個生命都會遇到困境,遇到困境怎么去解脫?怎么去化解?好的喜劇能提供這種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講,喜劇精神能夠彌合很多社會矛盾。
還沒有喜劇這門課
環球人物雜志:有一種觀點,認為文化藝術與物質生產不同,是“妙手偶得”,說“套路”就俗了,但您似乎很強調喜劇的“套路”?
陳佩斯:經驗完全可以變成科學的認識,藝術的規律也是可以認知的。就像聲樂里的中央C,選擇這個頻率作為中央C是有道理的:這個振蕩頻率會促成人體細胞的舒適感。它是有能量的,喜劇不也是這樣?人物關系形成之后,就產生了勢能,這種能量是可以被認知的,能用物理的方法測出來,那就是觀眾回饋的笑聲。喜劇節奏的快慢直接影響觀眾的笑聲,這就是規律。
把一個悲情的人變成一個快樂的人,相當于平白無故把溫度從0度一下子升到100度,這是需要能量的。喜劇也是,用正確的方法,讓觀眾的心理溫度從0度升到100度。喜劇演員要了解這套方法,也需要積淀、培養、訓練。
環球人物雜志:您這個說法很有意思。這些理論是您自己琢磨出來的,還是看書看出來的?
陳佩斯:都有,你不看書怎么行呢?不看書怎么知道細胞的振蕩頻率是怎么回事呢?
環球人物雜志:您說過,現在是一個半娛樂化的時代,什么都要調侃一下,什么都要輕松地去面對,但另一方面,喜劇這個藝術形式的發展,好像又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陳佩斯:對,現在可以說,對喜劇連基本的認識都沒有。它處于朦朦朧朧的一個狀態,就是大家知道這個東西挺好玩,但是誰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們舞臺排練的時候,往往是觀念上的問題把你絆住了,讓你進行不下去。我們的正規院校不培養喜劇人才,也沒有喜劇這門課。
環球人物雜志:您覺得喜劇跟逗樂、搞笑一樣嗎?
陳佩斯:一樣啊,逗樂是最基礎的,就像人走路,腳往外一邁,你得邁出這一步啊,每邁一步都是在搞笑。一出喜劇的過程,不也是逗樂、搞笑的過程嗎?這個沒有矛盾,是一個組成的關系。
環球人物雜志: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陳佩斯:把我的很多想法總結一下,再把它細化。用培訓的方法把它傳給后面的人。
和陳佩斯對話,很難想象他只讀過5年書。近幾年來,陳佩斯開始系統研究莎士比亞、莫里哀等喜劇大師的作品。在網絡文化泛濫和各類純搞笑話劇的沖擊下,他堅持自我耕種,不可憐巴巴地、無原則地向網絡乞討笑料。他的偶像是卓別林——那個給全世界帶來快樂、自己卻得了抑郁癥的偉大演員。他最經常說的一句話是:“這行太苦,我的每一步都是煎熬過來的。”
編輯:王晶晶 美編:王迪偲 編審:張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