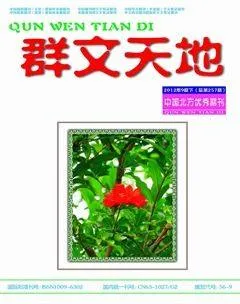試析孔子的中庸之道與亞里士多德的中道觀之異同
摘要: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觀在很多方面有著共通點,但由于兩人所處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不同,因而這兩種思想也相應的體現出許多不同之處。本文就兩者的根本精神、方法論、出發(fā)點和達到的境界、獲得的途徑以及政治主張方面進行了比較分析。
關鍵詞:孔子;亞里士多德;中庸之道;中道觀;比較
一、引言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和亞里士多德(前384-322年),一個是中華民族的“至圣先師”,對中國乃至整個東方的思想和文化造成了長達數千年的歷史影響,另一個則被馬克思、恩格斯稱為“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最博學的人物”,在西方思想界也產生了無與倫比的重要影響。巧合的是,這兩位思想大師都不約而同提出過以“中”為善的倫理觀,孔子提倡中庸之道,“過猶不及”,亞里士多德認為中道是一種美德,同時也是一種幸福。這兩種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有著相通之處,當然,由于東西方的社會文化背景不同,它們也都有各自的獨特之處。
二、孔子中庸之道的基本內容
中庸之道是由孔子首倡的,《論語》載:“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孔子認為“過”和“不及”是相反的兩個極端,都不是理想狀態(tài),惟有無過無不及才是具有理性精神的“中庸之道”。
在論述“君子”這種理想人格時,孔子也把中庸之道視作評判的標準。君子必須“尚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他強調君子必須自覺的保持中庸,即無過無不及的中立狀態(tài),而小人則無所顧忌,不能達到中庸的標準,所以他們也無法具備理想的人格。
而要做到中庸,孔子認為應當“執(zhí)兩用中”,必須把握住“過”與“不及”兩種傾向使之不走向極端,保持“中”這種平衡的狀態(tài),就能讓事物自然、和諧地發(fā)展。除了“執(zhí)中”外,要做到中庸,孔子還提倡“時中”,即“隨時以處中”,也就是說“中”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具有不確定性的、隨時而變的動態(tài)的“中”端。“時中”即要根據不同的地點、時間和條件進行不同的調整,因地制宜、因事而異,“無可無不可”,通權達變。孟子便曾說過:“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對一切事,只要以“中”為原則,力求適中、合宜即可。即使有時不得中,稍有狂狷,亦無不可。所以孔子的中庸之道包含著發(fā)展變化的道理。因材施教就是其具體運用的體現。
概括起來,孔子的中庸之道在《禮記·中庸》篇里得到了精確的闡述:“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主張人們把自己的感情、欲望、思想、行動控制在道德允許的范圍之內,使之恰到好處,同時又強調權變發(fā)展,這樣萬事萬物也會和諧統(tǒng)一地發(fā)育、成長和繁榮。
三、亞里士多德中道觀的基本內容
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主要集中于著作《尼各馬可倫理學》之中,是他政治哲學思想的核心和理論基礎。所謂“中道”就是強調適度、適中的意思,亞里士多德強調適度、過、不及三種狀態(tài)。他認為存在著三種性格,兩種是惡的,其一是過度,其一是不及,只有適度的中道才是美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他舉了很多具體的例子來進行適度、過和不及三種狀態(tài)的對照。例如,勇敢是莽撞與怯懦之間的中道,節(jié)制是放蕩和麻木的中道等等。至于人們應該如何形成和掌握“中道”的道德行為和標準,亞里士多德認為要靠后天實踐訓練,它或是“由于訓練而產生和增長的”,或是由于“習慣的結果”,是后天形成的。
其次,亞里士多德指出,萬物皆以某種“好”為目的,人類也都在追求“好”。這里的“好”便是指幸福。所以“中道”的目的亦為人生的最終目的,即幸福。言行中道的目的是幸福的生活,幸福是“好好地生活,好好地行事”。所以幸福生活和有德生活是統(tǒng)一的。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亞里士多德提倡的是具有相對意義的“中”,即“適當”。“只有在適當的時間和機會,對于適當的人和對象,持適當的態(tài)度去處理,才是中道,亦即是最好的中道。”所以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是因人而異的,是一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也不是一種折衷主義,不等于數學上的中點或平均數。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中道,就是根據具體情況正確選擇情感和行為的一種狀態(tài)和方法。
但是,亞里士多德的中道并非適用于萬事萬物,而是有其特定的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