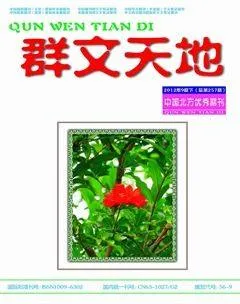《詩(shī)》《易》意象之實(shí)與虛
摘要:《詩(shī)》與《易》都是假象見義。其中象可分實(shí)象和假象。不論虛實(shí),象均是源自于現(xiàn)實(shí)世界。在象的構(gòu)建上,虛象比實(shí)象更難。虛構(gòu)是文學(xué)的本質(zhì)屬性之一,在考查中國(guó)文學(xué)實(shí)與虛的源流時(shí),不應(yīng)忽視《易》的影響。
關(guān)鍵詞:詩(shī)易; 虛構(gòu);征實(shí)
一、象分虛實(shí)
《文則》曰:“《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shī)》之有比,以達(dá)其情。”《易》與《詩(shī)》均是假象見義者。而所構(gòu)之象,又分實(shí)象與虛象。
論象之虛實(shí),肇始于《周易·乾卦·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qiáng)不息”條下孔穎達(dá)疏:“先儒云此等象辭,或有實(shí)象,或有假象。實(shí)象者,若‘地上有水,比也’;‘地中生木,升也’,皆非虛,故言實(shí)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風(fēng)自火出’,如此之類,假而見義,故謂之假象。”即指出實(shí)象與假象之別。
《詩(shī)》與《易》實(shí)象之平實(shí)樸素者,似述身邊常景。以狐這個(gè)意象為例。《易·解·九二》中有“田獲三狐”之辭。又有《易·未濟(jì)》,卦辭曰:“未濟(jì),亨,小狐汔濟(jì),濡其尾,無(wú)攸利。”是說(shuō)一只小狐過(guò)河,尾巴翹起,將要到河岸時(shí),尾巴突然垂下。暗指過(guò)河未遂。《詩(shī)經(jīng)》中提到狐的地方有九處,多是作為田獵的對(duì)象和穿戴的皮毛來(lái)描寫。《衛(wèi)風(fēng)·有狐》:“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wú)裳。”營(yíng)造漂泊孤單的的形象,以表達(dá)悲傷無(wú)依的情緒。《易》與《詩(shī)》中涉及的動(dòng)物,多是自然世界中的實(shí)在之物,神秘色彩十分淡薄,涉及場(chǎng)景亦非常生活化。
至于虛構(gòu)之假象,比如《詩(shī)·大雅·云漢》“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之句。《孟子·萬(wàn)章上》已有解釋:“說(shuō)詩(shī)者,不以文害辭……信斯言也,周無(wú)遺民也。”實(shí)際上,這句只是詩(shī)經(jīng)作者營(yíng)構(gòu)的亂世慘淡的景象而已,并不能篤信。意象之怪誕飄渺者,便如《易》之龍戰(zhàn)玄黃,張弧載鬼。無(wú)人見過(guò)此種奇景,種種幻想耳。《歸妹卦·九二》:爻辭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眇,亦目盲之義。目盲何能視物,假象也。
《詩(shī)》之興象,多草木蟲魚,風(fēng)雨云露。這些自然實(shí)物可觀可感,較為實(shí)在。《詩(shī)》之象,即使虛構(gòu),形象本身也多常見,不實(shí)之處在于其語(yǔ)境的不可實(shí)現(xiàn)。比如“周余黎民”,所言對(duì)象是確實(shí)存在,只是其情狀難以置信。《易》之象則常有虛象。且不僅是形象本身的虛構(gòu)性,比如神鬼之類,并且對(duì)象的狀態(tài)也多反常態(tài)。比如《震卦·九四》爻辭所敘之“震遂泥”,雷落入泥土的景象,則難以想見。從比例上說(shuō),《詩(shī)》實(shí)象多于《易》,《易》虛象富于《詩(shī)》。
二、意象源于征實(shí)
傳說(shuō)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作八卦。易學(xué)本源于自然,當(dāng)然有自然實(shí)象。《詩(shī)·國(guó)風(fēng)》本采自民間歌謠,民眾生活勞作,發(fā)而為歌,取諸近身之物,婉而成章。正暗合西方亞里士多德之模仿說(shuō),并馬克思之勞動(dòng)說(shuō)。
實(shí)象直接描摹自然,征實(shí)自不必說(shuō)。假象,其實(shí)也是對(duì)自然世界的變相觀照。無(wú)論實(shí)象或虛象,皆出于自然。《文史通義·易教》曰:“人心營(yíng)構(gòu)之象,……心之營(yíng)構(gòu),則情之變異為之也。情之變易,感于人世之接構(gòu)而乘于陰陽(yáng)倚伏為之也。是則人心營(yíng)構(gòu)之象,亦出于天地自然之象也。”
人存于世間,首先接觸的就是自然界,所思所感之素材,就是自然之物。一些自然之物,或有靈巧或有勇力,便被先民膜拜以為圖騰。神秘如龍者,也是馬首蛇尾,有跡可循,有型可依。至于鬼怪神靈,不過(guò)是如魯迅所言:“描神畫鬼,毫無(wú)對(duì)證,本來(lái)可以專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地?fù)]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lái)的,也不過(guò)是三只眼睛,長(zhǎng)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長(zhǎng)了頸子二三尺而已。”以自然之物為基,馳騁想象,組合創(chuàng)造,方有詭誕假象。
而《大畜卦·象傳》所說(shuō)“天在山中”,物雖實(shí)在,境卻難得。便是截取實(shí)物,嵌入奇景,騰挪幾分,交錯(cuò)一二,便有虛構(gòu)之象。
三、虛構(gòu)與文學(xué)
在論及文學(xué)之本質(zhì)時(shí),往往是將虛構(gòu)作為文學(xué)的重要屬性。韋勒克在《文學(xué)理論》中說(shuō):“文藝藝術(shù)的中心,顯然是在抒情詩(shī)、史詩(shī)和戲劇等傳統(tǒng)的文學(xué)類型上,他們處理的都是一個(gè)虛構(gòu)的、想象的世界。”這是西方文論對(duì)文學(xué)虛構(gòu)性的理解。中國(guó)傳統(tǒng)文論中,對(duì)于虛構(gòu)也非常重視。《文心雕龍·神思》系統(tǒng)地論述來(lái)文學(xué)與想象虛構(gòu)的關(guān)系。“思接千載”“視通萬(wàn)里”,無(wú)乃想象之力?想象即虛構(gòu)形象。運(yùn)用神思,開放想象,才能達(dá)到“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的境界。未有虛構(gòu),則難以稱其為文學(xué)。
象雖出于現(xiàn)實(shí),但是虛象往往比實(shí)象更難得。實(shí)象僅憑所見,忠實(shí)記錄即可。此法類史家。有“六經(jīng)皆史”之說(shuō)法,便是各經(jīng)中俱有寫實(shí)之筆的原因。孟子曰:“《詩(shī)》亡而后《春秋》作。”以《詩(shī)》與《春秋》同體。然文學(xué)與歷史,終究不同。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尚書》《春秋》之謂。僅僅直陳時(shí)事,便未得文學(xué)之旨?xì)w。用以記錄典章法紀(jì),國(guó)事人情,必用董狐之筆,則成征實(shí)之象。《易》以道陰陽(yáng),《詩(shī)》以言性情,諷喻婉轉(zhuǎn),苦慮勞情,近比遠(yuǎn)指,物貌心求,則成虛構(gòu)之象。劉熙載《藝概·賦概》說(shuō):“按實(shí)有象易,憑虛構(gòu)象難,能構(gòu)象,象乃生生不窮矣。”虛象之難,就在于需要作者將實(shí)物融匯而再創(chuàng)作。自然比直寫實(shí)象更考較作者功力。
對(duì)于中國(guó)文學(xué)的實(shí)與虛,或者說(shuō)寫實(shí)與想象方面的追溯,往往至詩(shī)、騷而止。其實(shí)《易》從實(shí)象與虛象的角度,對(du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虛與實(shí)傳統(tǒng)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而精微的影響。關(guān)于《易》的成書年代,《系辭》曰:“《易》之興也,當(dāng)殷之末世,周之圣德邪?”現(xiàn)在較為普遍的說(shuō)法是《易經(jīng)》成于商末周初。彖和象則可能成于戰(zhàn)國(guó)。《詩(shī)經(jīng)》則大致成書于春秋時(shí)期。很難說(shuō)《詩(shī)》沒(méi)有受過(guò)《易》的影響。在考查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源流時(shí),《易》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huán)。
參考文獻(xiàn):
[1]章學(xué)誠(chéng).文史通義[M].上海.上海世紀(j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