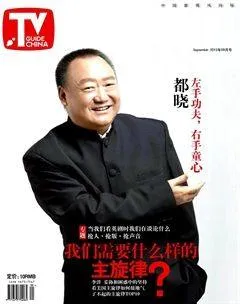我們需要什么樣的主旋律?
主旋律電視劇其實(shí)不分“時(shí)令”,作為中國電視劇市場上最主流的一道大餐,觀眾基本上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它。但相比之下,每年的下半年往往又是主旋律電視劇扎堆上市的時(shí)候;7月有建黨節(jié),8月有建軍節(jié),10月更是舉國歡慶,夾在中間的9月更熱鬧,前有中國抗日戰(zhàn)爭勝利紀(jì)念日,后有國際和平日,今年更特殊,因?yàn)橹泄惨匍_十八大——之后就是牽動(dòng)億萬人心的領(lǐng)導(dǎo)人換屆選舉——據(jù)我所知,今年許多影視公司手底下的主旋律電視劇,都在準(zhǔn)備 “獻(xiàn)禮”。由此可見,盡管全世界都有主旋律,但中國的主旋律似乎和政治的關(guān)系更緊密,也更曖昧一些。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主旋律呢?許多舶來的百科網(wǎng)站都沒有給出準(zhǔn)確的定義;而百度百科的解釋是,“符合統(tǒng)治階級(jí)利益的影視作品或其它文藝作品。通常由統(tǒng)治階級(jí)主導(dǎo)宣傳。就是要在建設(shè)有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導(dǎo)下,大力提倡一切有利于發(fā)揚(yáng)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huì)主義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導(dǎo)一切有利于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思想和精神,大力提供一切有利于民族團(tuán)結(jié)、社會(huì)進(jìn)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導(dǎo)一切用誠實(shí)勞動(dòng)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我之所以要強(qiáng)調(diào)“舶來”和“本土”的差異,其實(shí)正是為了撇清濾凈這一詞匯的政治含義,盡量地還原它本來的價(jià)值屬性。百度百科的解釋,還是強(qiáng)調(diào)和停留在具有中國國情的主旋律電視劇的解釋上;又或者說,政治屬性從來都是主旋律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上世紀(jì)的1958年,中國誕生了第一部電視劇《一口菜餅子》,之后還有《黨救活了他》、《合家歡》、《生活的贊歌》、《新的一代》、《劉學(xué)文》、《養(yǎng)豬姑娘》、《新來的保育員》、《真正的幫助》、《共同進(jìn)步》、《江姐》、《衛(wèi)生大演習(xí)》、《像他那樣生活》,《戰(zhàn)斗在頂天嶺上》、《活捉羅根元》……光聽名字,我們已經(jīng)大抵可以判斷,這些劇的內(nèi)容和主題。歌頌英雄人物,進(jìn)行革命傳統(tǒng)教育;贊美新人新事新生活,配合全黨全國中心任務(wù)。雖然也有少兒題材和民族故事,但基本上還是掙不開前面兩個(gè)意識(shí)形態(tài)的范疇。可是事實(shí)上,這是對(duì)主旋律的一種非常狹隘的,甚至是巧取豪奪式的理解;與弘揚(yáng)革命信仰和好人好事好領(lǐng)導(dǎo)相比,主旋律更應(yīng)該肩負(fù)起宣揚(yáng)真善美和普世價(jià)值的重任。遺憾的是,一直到今天,這種對(duì)意識(shí)形態(tài)濃墨重彩的“獻(xiàn)禮劇”仍舊是“主旋律”中不容忽略的大軍,以至于中國觀眾一提到主旋律便本能地和“紅色經(jīng)典”掛鉤。
如果說上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的主旋律苦于敘事技巧和拍攝條件的短缺使之沒有一部成為經(jīng)典得以流傳,那么今天我們對(duì)于意識(shí)形態(tài)刻舟求劍式的復(fù)制,則暴露了我們百分之百無添加的投機(jī)心態(tài)。人民日益增長的娛樂需求和審美意識(shí)同不思進(jìn)取的主旋律之間的矛盾遲早被激化。市場是公正的——今年7月,央視一套播出的某偉人傳記電視劇,其收視率慘絕人寰,一上來就創(chuàng)下年度最低,一路播下去,竟然跌到了新中國自從有了電視機(jī)以來的最低點(diǎn),輕易成為電視劇史上的“收視之罪”。
正如同我們無法叫醒一個(gè)裝睡的人,有些帶著“獻(xiàn)禮”性質(zhì)的主旋律之所以難看,原因正如尹力導(dǎo)演所言,“藝術(shù)片就是為電影節(jié)服務(wù),表達(dá)個(gè)人小我,主旋律電影就是政府買單,標(biāo)語口號(hào)說教。”這就好比一個(gè)諂媚之人為了個(gè)人利益而拍的馬屁——自己沉醉萬分,被拍的人可能也很受用——但觀眾看得那叫一個(gè)難受。《闖關(guān)東》之后,各地的地方政府紛紛搶拍“遷徙劇”,也不管當(dāng)?shù)厥欠裼羞^遷徙的歷史。某編劇曾經(jīng)被某海濱城市邀請(qǐng),寫一部反映當(dāng)?shù)孛褡逵⑿刍蝻L(fēng)土人情的電視劇,目的是為了讓這個(gè)城市出出名,在全國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力。待遇十分誘人:三百萬的預(yù)付稿酬和一套海景房,在做這期選題時(shí),我曾經(jīng)采訪了不少圈內(nèi)編劇和制片人,他們坦言寫主旋律電視劇的收入和其他題材相比并無差別。另外,據(jù)我所知,主旋律的電視劇大部分是被央視收購,而央視的收購價(jià)向來不高。那么“三百萬的預(yù)付稿酬和一套海景房”如果不是空頭支票和海市蜃樓,地方政府如何愿意做這個(gè)賠錢只賺吆喝的買賣?答案只有兩個(gè)字:政績!有了政績就能升遷,為了升遷不惜用納稅人的錢去拍一部注定收不回成本的電視劇。
美國主旋律在中國的軟著陸
既然中國的主旋律這么差勁,有不少年輕觀眾提出要中國影視從業(yè)者下課,大家都看好萊塢和美劇得了。這話其實(shí)側(cè)面反映了中國影視業(yè)和年輕觀眾之間的相互拋棄。很難想象,一個(gè)產(chǎn)業(yè)如果失去年輕受眾群,它的未來在哪里?
而如果我們只剩下美劇可以選擇呢?固然好萊塢有許多質(zhì)地精良的主旋律,幾乎每一部都在強(qiáng)調(diào)真善美——即使披著鋼鐵外殼的變形金剛和擁有超能力的蜘蛛俠亦不例外;而且必須要說明的是——好萊塢面向的是全球市場,面對(duì)不同文化習(xí)慣和傳統(tǒng),它竭力避免一切容易引發(fā)誤會(huì)和沖突的情節(jié)、細(xì)節(jié),乃至價(jià)值觀,它宣揚(yáng)的都是普世價(jià)值——所謂普世價(jià)值就是普天之下,各種膚色人人默認(rèn)的一種正面的價(jià)值觀。既然如此,我們還那么費(fèi)勁干嘛?中國影視業(yè)歇菜得了,何況中國影視產(chǎn)業(yè)對(duì)GDP也沒啥太大的貢獻(xiàn)。直接被好萊塢招安不就得了?
事實(shí)上,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一大批年輕觀眾被好萊塢完美征收。他們?cè)诒还噍敗罢嫔泼馈钡耐瑫r(shí),亦全面接受并認(rèn)同了美國的全部——包括粗話,這些觀眾即使在罵人的時(shí)候,不再像土著一樣問候?qū)Ψ降哪赣H,而是操著一口流利的帶著紐約下城口音的以S、F、B打頭的英語國罵;年輕人聚會(huì)不去茶館,而是星巴克或哈根達(dá)斯;一件標(biāo)價(jià)比同類產(chǎn)品貴出10倍的蒂梵尼鉆戒成為多少女人一生的夢(mèng)想與追求。美國電影中的消費(fèi)主義和對(duì)于地方本土品牌的大力贊揚(yáng),已經(jīng)完全俘虜中國年輕一代。美劇的教化功能早已無遠(yuǎn)弗屆了。
影評(píng)人毛尖說,“上世紀(jì)九十年代風(fēng)靡中國的《成長的煩惱》,我們看到人家父母面對(duì)孩子的第一次約會(huì),父母給的第一次性教育,簡直要熱淚盈眶。這一個(gè)熱淚盈眶不要緊,美國意識(shí)形態(tài)就軟著陸了。弄到現(xiàn)在,中國人搞戀愛,泡酒吧吃西餐,擺泰坦尼克的姿勢(shì),穿斯巴達(dá)克的衣裳,加上教堂、加上十字架,光看背影你能認(rèn)出是自己人算你識(shí)貨。不要以為愛國主義教育就是喊喊我愛你祖國,所謂管住男人先管住他的胃,愛國主義是具體的,包括愛祖國的風(fēng)土人情,愛祖國的吃喝玩樂。美劇中,人家有吃著我們的包子說我愛你嗎?美國人才不肯把這樣的好事給我們,可我們多幫襯人家啊,從西海岸到東海岸,美國一直在我們的影像中,漢堡比包子多,酒吧比茶館多,美劇的愛‘美’教育叫一個(gè)潤物細(xì)無聲啊。”
如果你以為以上只是消費(fèi)主義和物質(zhì)主義借著影像的東風(fēng)隨風(fēng)潛入夜,那么你真是大錯(cuò)特粗了,因?yàn)椴还苁请娨晞∵€是電影,終究還是一個(gè)精神屬性的物質(zhì)。南京大屠殺能拍成《南京!南京!》,就是好萊塢人道主義的勝利,活生生把一場帝國主義的侵略戰(zhàn)爭拍成一場人類的弱點(diǎn)之戰(zhàn),不僅為鬼子做影像粉飾,還為他們做哲學(xué)超度——這也是為什么好萊塢的編劇大師麥基盛贊這部電影的原因——好萊塢和美劇早已滲透到我們的一線人士,遑論其他?
犬儒和功利之外的信仰之美
現(xiàn)在,我再來問你,到底什么是主旋律?你會(huì)不會(huì)更茫然,但思考卻變得更審慎?還是聽聽編劇劉恒的說法,“主旋律除了要征服觀眾和征服自己以外,我以為一個(gè)更大的目的是征服敵人,這個(gè)敵人是廣義的敵人,包括意識(shí)形態(tài)的敵人。我們要對(duì)他們說,你說你們的價(jià)值觀不錯(cuò),我說我們的價(jià)值觀也不差。”
劉恒說“我們的價(jià)值觀也不差”,但語氣還是軟了點(diǎn)。不過,通俗地說,表現(xiàn)我們的主流價(jià)值觀,表現(xiàn)我們價(jià)值觀的導(dǎo)向,或者說期望,統(tǒng)統(tǒng)屬于主旋律。主旋律電視劇和社會(huì)主義、革命信仰的關(guān)聯(lián),本來就是應(yīng)有之義,但不是說,社會(huì)主義、革命信仰等等就是主旋律電視劇的全部內(nèi)容。我們的價(jià)值觀可以上通社會(huì)主義,下接人民美食——今年最火的紀(jì)錄片《舌尖上的中國》,不知道讓多少國人在為中華源遠(yuǎn)流長的飲食文化自豪的同時(shí),也因其影像記錄中對(duì)于食材的艱難采集而加倍珍惜自己嘴下的食物,這比“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式的填鴨教育輸入,要有趣得多,也有用得多。
主旋律電視劇的類型還有很多,事實(shí)上,我們確實(shí)也生產(chǎn)了不少品質(zhì)優(yōu)良的主旋律作品。說到這里,我先扯一段八卦,中戲和北電的96級(jí)明星班在坊間早已傳為神話,人們喜歡樂此不疲地從網(wǎng)上各種流傳的模糊不清的畢業(yè)照里數(shù)星星,卻很少有人理性地想過為什么神話偏偏降臨96級(jí)?雖然一個(gè)明星的走紅是變幻莫測(cè),說也說不清的,但集體走紅的背后必然有一定的內(nèi)在邏輯和外部聯(lián)系。背后的秘密,其實(shí)說來也簡單,那就是——民營影視業(yè)的崛起。
你可能有所不知,我國一直到1997年以后,伴隨著中國影視業(yè)改革的腳步,民營企業(yè)才在影視行業(yè)逐漸取得了制片、發(fā)行、院線等各條產(chǎn)業(yè)鏈上的“準(zhǔn)入證”。攜體制、資本、專業(yè)市場運(yùn)作技能、人才等方面的諸多優(yōu)勢(shì),民營影視企業(yè)迅速走向成熟與壯大,并逐漸成為中國影視市場的中流砥柱。具體到民營影視對(duì)中國主旋律的貢獻(xiàn),正在于資金的獨(dú)立和完整使之完全脫離政府買單模式;市場化的需求又逼得民營影視公司追求最大程度上的娛樂性和觀賞性。
我們印象中好看的主旋律差不多均出自民營公司之手。比如講述個(gè)人成長與勵(lì)志的《士兵突擊》,強(qiáng)調(diào)家和萬事興的《媳婦的美好時(shí)代》,歌頌真愛至上的《山楂樹之戀》,反映一代遺民抗日的《闖關(guān)東》,還有直接拿中共歷史開刀的《走向共和》和《人間正道是滄桑》……最好的例子是20年前的《渴望》,超過70%的收視率使之成為“歷史之最”——同樣都是主旋律,一個(gè)是君住長江頭,一個(gè)是我墊長江底。為什么差別這么大?
《渴望》不講革命,也不跟你談?wù)危@然是不折不扣的主旋律作品,在人物的家長里短和磕磕碰碰中展現(xiàn)了一個(gè)轉(zhuǎn)型社會(huì)的時(shí)代之痛和人心之美。誠如人制片人鄭曉龍所說,“文藝作品的主題就是傳播真善美,鞭笞假丑惡。”《渴望》沒有更高的主旋律,就是講述普通老百姓的善良和美麗,與群眾特別近。《渴望》之后,劇組當(dāng)時(shí)總結(jié)過三貼近:“貼近生活、貼近百姓、貼近觀眾”。這個(gè)三貼近,至今仍是電視劇取信觀眾的不二法門。值得一提的是,當(dāng)下成功的主旋律電視劇在“三貼近”的基礎(chǔ)之上,敏銳地觸及了當(dāng)下人們內(nèi)心深處對(duì)精神價(jià)值的渴望。主旋律電視劇的熱播,其實(shí)正是社會(huì)公眾集體心理的反映。如今我們已經(jīng)改革開放30年,尤其在最近幾年,飛快增長的GDP讓我們贏了很多,也失去很多,我們來不及思考和判斷,這其中不僅僅是經(jīng)濟(jì)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還有文化上的改革。在一個(gè)缺乏宗教傳統(tǒng)的國家和一個(gè)缺乏精神領(lǐng)袖的時(shí)代,經(jīng)濟(jì)的快速發(fā)展導(dǎo)致一些現(xiàn)實(shí)生活價(jià)值的缺失,一些老百姓開始重新思考信仰。因此,我們需要形成一種新的道德依據(jù)去引導(dǎo)人們的文化心理走向,而主旋律恰好是提供這種價(jià)值觀念的最好平臺(tái)。《士兵突擊》、《潛伏》、《人間正道是滄桑》這些電視劇,用拔尖的高音表現(xiàn)了我們?cè)缫讶笔У男叛觯绱思儍粲指呖旱谋磉_(dá)。在一個(gè)犬儒和功利盛行的年代,他們展示了什么叫做“信仰之美”;這種“信仰之美”并非曲高和寡,他們?cè)谀贻p人中間的認(rèn)知度亦是高居不下——《士兵突擊》中的一直把“不拋棄不放棄”掛在嘴邊的許三多不就被票選為當(dāng)年的“北京十大杰出青年”嗎?這象征了人們?cè)谕瞥缤稒C(jī)主義的現(xiàn)代社會(huì)里對(duì)傳統(tǒng)情義的熱切呼喚。一個(gè)虛擬的人物能在年輕人中產(chǎn)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成為我們這個(gè)國家青春氣質(zhì)的源頭。對(duì)此,誰還能否定主旋律的價(ji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