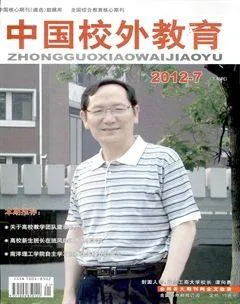淺論豫劇“豫西調”的生成及衍變
豫西調是怎樣生成的?它和祥符調是什么關系?長期以來,一直是困擾學界的一個麻煩問題。一方面,由于豫西調是豫劇的一個地方唱調,它和豫劇的其他唱調一樣,歷來都被視作俚俗不堪,鄙穢猥褻之劇,歷史上一直是被官方打壓的對象,很少受到上流社會和文人們的關顧,因此、它在生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沒有留下更多可以確認其身世的史料記載;另一方面,由于豫劇劇種的生成,自今還仍是見仁見智,各持一端。所以,豫西調的身世也就像亂麻一團,成了一本說不清理還亂,看似明白而又不太清楚的糊涂賬。
一、豫西調生成的有關歷史表述
豫西調是怎樣生成的?在以往的史料和記載中大體有以下幾種說法:其一,在贊同豫劇生成“西來說”的文章里,多認為它源于秦腔或同州梆子。如王鎮南在《關于豫劇的源流與發展》一文中說:“中國文化多是沿著黃河由西向東發展,梆子戲也是如此……入了河南省境,秦腔就變成了豫梆,即河南梆子。”他認為從秦腔發展為豫劇,首先是在豫西形成了豫西調,漸次向本省各地流布。他說“從豫西向東發展,以開封為中心,叫做祥符調;再向東以商丘為中心,叫做豫東調;從豫西有一支向黃河以北發展,現今在平原省南部(今新鄉一帶)還很盛行,特稱為大油梆;又有一支從豫西向南發展,現今南陽一帶尚有演唱者,但已不盛,特稱為南陽梆。”
其二,認為豫劇是由“靠山吼”發展起來的。如周貽白在《中國戲曲史發展綱要》中說:河南梆子初起時,僅在豫西幾縣的農村中,靠著山坳,隨便用木板搭上一個臺,就可以演唱,因此,當地或名之為“靠山吼”。以后一天天發展,由豫西流行到豫東,到了清代末年,則已遍及全省。辛亥革命后,漸由農村進入城市,而且因地區不同有了幾個派別:在閿鄉以東,以洛陽為中心者,名豫西調;洛陽往東,以開封為中心者,名祥符調;由開封再往東,以商丘為中心者,則名豫東調;其由豫西向北,接近河北地區的一派,則名大油梆;其由豫西向南,接近湖北地區的一派,則名南陽梆。
馮紀漢似贊同周貽白的說法,他在《豫劇源流初探》中說:“西府調是豫劇中的牡丹,它的光彩鮮艷奪目。它在東路秦腔和蒲劇的影響下,在洛陽一帶流行的靠山吼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但他又說:“豫劇中的五個流派,影響最大的是祥符調和西府調,豫東調、高調、沙河調都是從祥符調派生出來的。”這里他提出了一個新問題:“豫東調、高調、沙河調都是從祥符調派生出來的。”卻唯獨沒有說明西府調和祥符調的關系。很明顯,他既不贊同豫西調向東發展而生成祥符調的說法,因為,這與他在《初探》中提出的“豫劇最早形成于開封”的觀點相悖;又弄不準該如何對豫西調進行切合實際的解讀。之后,于林青在《豫劇源流考略》中,盡管明確主張豫劇生成的“本土說”,但卻在豫西調怎么生成的問題上,無奈地贊同了“西來說”的觀點。
其三,在贊同豫劇生成“本土說”的文章中,也有兩種說法:一是認為豫西調是祥符調流變的結果。如張鵬在《豫劇源流新探》中說:“祥符調流傳到豫西洛陽一帶,則由于當地語言發音上喉音和舌根音較重,音色深沉,在行腔上顯得深厚、寬展、有力,于是就形成了豫西調。”另一種,可能是因為史料的占有尚不夠充分,也只好如《初探》那樣,暫時采取了回避的態度。
還有一種說法,根據豫西民間流傳的順口溜和老藝人的回憶,認為豫西調是在早期戲曲青戲(弋陽腔)、皮黃腔、越調和羅戲的影響下,“胡亂套”它們的音樂唱腔形成的。如李振山在《豫劇豫西調的今昔》一文中說:有人說豫西梆子來自東路秦腔;有人說從洪洞縣移民把蒲劇帶到了豫西。豫西梆子確實受這兩劇種影響,但它的直系母親既不是秦腔,也不是蒲劇,而是羅戲、越調和(皮)黃戲。豫西民間很早就流傳了“一青二黃三越調,梆子戲是胡亂套。”和“羅戲窩兒,出粗梆;越調底兒,摻皮黃”等順口溜。”
二、豫西調解讀中的幾種誤區
據已知的有關史料和藝人們的回憶,應該可以確認豫西調是祥符調流變的結果,它也應和豫劇的其他地域唱調一樣,都屬于祥符調的子系統的唱調。為了說明這一論點,這里需要先排除幾種對于確認豫西調身份的誤區:一是所謂弦索腔對豫劇生成的影響。我們在以往對豫劇源流的研究中,過分強調了弦索腔的作用。實際上,我國曲藝和戲曲音樂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至少從北宋的唱賺開始,其音樂一直是沿著纏令和纏達兩條線發展的。聯曲結構的纏令和弦索腔影響了以后的曲牌體戲曲,而主調變奏的纏達則直接促成了板腔體戲曲音樂的生成。在河南的曲藝和戲曲里,如南陽大調曲、大弦戲、柳子戲、羅戲等都和弦索腔一脈相承,至今仍保留著曲牌體的音樂體制結構;而大鼓書、三弦書、墜子和各種梆子戲,則都是纏達音樂體制的直接延續,都屬于主調變奏的音樂結構形制。比對豫劇的唱腔和音樂,屬于弦索腔的【山坡羊】、【駐云飛】等曲牌,進入豫劇已有數百年了,但它們的所謂影響,最多也不過是早期曾經作為曲牌演唱過。而當豫劇的板式規范形成后,特別是豫劇的音樂逐漸走向成熟并越來越豐富之后,它們最多也只是作為配樂使用了。然而,像【山坡羊】、【駐云飛】這些曲牌在曲牌體的大弦戲等劇種里,不僅數百年來一直作為演唱曲牌使用,而且,還衍生出了多種變體牌子。充分說明曲牌體制的弦索腔,很難化作板腔體的板式。實踐證明,主要影響和衍生豫劇音樂的不是什么女兒腔,或河南調,或弦索腔,而正是早期流行于河南地方的,唱詞為齊言對仗句式,音樂屬于主調變奏性質,而且是上、下句結構的曲藝音樂。
二是所謂秦腔的影響:研究豫劇源流的初始階段,人們多依據凡梆子腔劇種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先的理念,又根據明傳奇《缽中蓮》中關于“西秦腔犯”的記載,把秦腔認作梆子腔的鼻祖,意想出梆子腔由西向東發展的路線圖。其實,劇種的生成是一個順其自然而又相當復雜的問題,比對豫劇和秦腔的音樂唱腔,除了都屬于板眼變化的聲腔構成體制外,沒有發現因相互衍生而應有的共同生命基因和血緣關系。
三是最具忽悠力,也是最能讓人迷惑的一個誤區,即祥符調的上五音和豫西調下五音的不同音調形態。由于以“5”為主音的祥符調和以“1”為主音的豫西調,所形成的不同調式、旋律,以及藝術形象和風格的鮮明對比,人們怎么也不會相信它們原是本源于一個家族,從而會比較輕易地順從于豫劇生成的西來說。其實,關于祥符調和豫西調的關系,有不少史論文章都有表述,如《豫劇源流初探》中對豫西調的解讀:“它的板路、唱腔表演,基本上和祥符調相同……也用艷腔拉腔,路子和祥符調大致上一樣,”說明了早期豫西調和祥符調大體相同。而今天學界在理論上把豫西調定位為下五音,則是后來豫西調發展中的一種創新和異變。這一點《初探》也講的非常清楚:豫西調“原來也不唱下五音,在光緒末年才改唱下五音,不用艷腔拉腔了。現在西府調的老藝人王才(小旦)、郭大孬(丑),已年近八十,他們在小時候學戲時,還沒有下五音,唱法還和祥符調近似。據西府調老藝人地牤牛(賈寶須)、周海水等人說,是在六十年前,由名旦紀喜來(藝名烏木桿)、名生楊小德(藝名戲狀元)等人,在唱腔上進行了藝術改革,才開始唱下五音。”
這里還有幾個問題需要搞清楚:一是所謂上五音和下五音的區分,是學界對祥符調和豫西調唱腔藝術的理論總結,那只是說明了它們最為常見的一種唱法,并非沒有其他唱法;如李振山在《豫劇豫西調的今昔》中提供的崔大照等老輩藝人的喊腔唱法:“前三皇后五帝年深久遠,有堯舜和禹湯四大名賢……”是一段早期演員和科班學藝常用的練唱教材。無論是曲調、過門,還是假聲唱法都和祥符調近似。同樣,祥符調也絕非僅有上五音一種唱法,在孫延德傳給陳素真的《吵宮》的唱腔中,(見范立方《豫劇音樂通論》)原本就有以“1”音為主音的所謂下五音唱法。而且,祥符調里經常使用的“醒夢曲”:如“昏昏沉沉如在夢,不知南北與西東……”也是典型的以“1”為主音的下五音唱法。還有大家熟悉的祥符調名家王素君,它的唱腔幾乎全是下五音曲調,你能說他唱的是豫西調嗎?其二,鑒別某種唱調,所謂上五音和下五音只是其藝術元素之一,其他如語音、用字、用嗓以及音樂表現上的各種因素,也都非常重要。特別是地方語音和音樂構成是確定唱調屬性的更為重要的條件,如祥符調和豫東調、沙河調、高調等的區別,主要便是依據地方語音和音樂構成等因素來鑒別的。
三、豫西調的歷史衍變及基質解讀
豫西調的生成和衍變發展,大體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一是豫劇的早期形態——“土梆戲”階段。據有關史料記載,豫劇在開封一帶生成后,先是在開封周圍的“內十處”和“外八處”活動。關于內十處和外八處老藝人說法不一,大體上內十處即祥符、杞縣、陳留、尉氏、中牟、通許、儀封、蘭封、封丘、原武等縣;外八處是指鄢陵、扶溝、許昌、襄縣、郟縣、滎陽、汜水、密縣等,其中,涉及了開封以西的不少地方。另外,據同治年間為朱仙鎮《重修明皇宮碑》捐款的班社中,涉及豫西的就有洧川、滎陽、汜水、密縣、新鄭、長葛、登封、鞏縣等。張鵬在《豫劇源流新探》中說:“在同治年間(1862—1874年),豫劇的傳播已從內十處、外八處擴大到更遠的地方,西邊到了鞏縣,北邊到了長垣,東邊到了蘭考,南邊到了太康。”說明“土梆戲”很早就在豫西流行了。
二是多劇種相互交溶階段。據史料記載,清道光二十一年黃河決口以后,差不多與蔣扎子把豫劇帶到商丘一帶的相同時期,在豫西大地上,正處于多劇種相互交流融合的時期。洛陽古為河南府,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積淀非常厚重的地方。歷史上很多古老的戲曲劇種,如弋陽腔、皮黃腔、羅卷戲、越調和秦腔、蒲劇等,都曾在這里交匯流傳。據李振山在《豫劇豫西調今昔》一文里介紹:“豫西梆子到底是怎樣‘胡亂套’呢?據說它是從幾個劇種里攝取了些東西套在一起。”“第一個劇種是曾經活動在中原一帶的很古老的清(青)戲。”“第二個劇種是(皮)黃戲,從襄樊一帶傳到豫西。”“第三個劇種是我省土生土長的較早的越調。”崔大照還說:“梆子腔是熱沾皮,胃口很大,見啥吸收啥。”豫西梆子名旦張慶冠,名老生賈寶須(地牤牛)也都說:“豫西梆子的調門是四下湊來的,武打來自皮黃戲,引子、曲牌和道白來自羅戲。”李振山認為:“這許多胡亂套來的東西,在吸收融化過程中,結合了豫西地方的語言……終于形成了一個生氣勃勃的新劇種——豫西梆子。”
另據有關史料和藝人們回憶,這一時期在河南各地出現了多個劇種同臺演出的現象,如梆羅卷同臺,梆羅或羅卷同臺,也有皮黃、越調和梆子等合演的情況,人們稱之為“兩下鍋”或“三下鍋”。還常有演員在演出中臨時改唱別的劇種唱調的情況。如上世紀二十年代,戲狀元楊小德常常正唱著梆子,轉板就唱皮黃戲;被稱作豫西旦角的總師傅的燕小庚,也曾與皮黃戲藝人配演《二進宮》。三十年代末,梆子戲《長坂坡》里還唱有皮黃戲的原板。四十年代鄭州梆子戲科班里還教唱皮黃戲的調門和節目;皮黃戲中的京胡,曾有很長一段時間擔任梆子戲的主奏樂器。還有史料中常常提到的,洛陽城西、南各縣山區的“靠山黃”,它就是因為靠山搭臺又夾唱皮黃戲調門而得名。從開封傳來的被稱作河南謳的土梆戲,到了豫西山區,即變成了“靠山吼”,也稱“靠山黃”。由于史料表述的不太清楚,只能說“靠山吼”有可能是梆子,而“靠山黃”很可能是皮黃,或梆子摻皮黃的“兩下鍋”了。
三是豫西調的成熟階段。進入上世紀三十年代,一方面,“熱沾皮”的豫西梆子,在與其他劇種的長期合作演出中,逐漸變大變強。按《豫西調的今昔》一文中的說法:“梆子腔起初只是羅戲班里的附屬小技……久之,梆子節目竟然喧賓奪主在羅戲班里占據了主要地位,群眾也稱羅戲班為梆子班了。原是羅戲本行的節目反變成帶搭兼演了。”說明豫西調在藝術上已經超越了同臺演出的其他劇種,受到了廣大觀眾的特別喜愛,它才能在眾多劇種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并一枝獨秀。另一方面,戲曲聲腔成熟的重要標志是聲腔規范的形成。有史料表明,祥符調傳入豫西以后,因受到豫西地方文化的影響,接受并學習了好多早期戲曲劇種的藝術成就,特別是吸納和融化了它們優秀音樂藝術元素,走了一條與豫劇其他地域唱調不同的發展道路,由是形成了自身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個性特色。
審視豫西調的生命密碼,我們不難發現,它之所以形成了既和祥符調有著明顯差別,又有別于豫東、沙河、高調等子系統唱調,有著獨特的另類的風格和形貌特征,和它的生命基質和構成元素密切相關。構成豫西調藝術的基質和元素主要有如下幾種:
其一,源于祥符調的母性基質。如前所說,早期豫西調曾被叫做豫西梆子,而且,它還是以梆子的名份和身份與其他劇種合作演出的,這些記載和回憶,不僅歷史地見證了它和河南梆子的血脈聯系,也昭示了它的身份的標識。再從它的聲腔形貌來看,盡管經歷了長期的傳承和變革,但體現河南梆子生命基質的核,卻仍和祥符調及其他唱調基本相同,特別是聲腔的構成,各種板式的結構規范以及演唱及樂隊伴奏的藝術等等,處處都彰顯了河南梆子劇種的“種”和“根”的特性,表明了它本源于河南梆子家族的正宗血統的史實。
其二,早期戲曲劇種的影響。豫西民間的很多順口溜,不僅見證了豫西梆子和其他劇種同臺演出和豫西調的生成歷史。從豫西調的藝術特征中,也處處顯示了它“胡亂套”用其他劇種藝術的痕跡。一是在對豫西調曲牌音樂的多次搜集普查中,發現屬于豫劇自己的音樂牌子并不多見,常見的則是其他劇種的曲牌;二是豫西調中最富特色的下五音曲調,明顯是在祥符調的基礎上,受到了豫西越調和豫西民間曲藝的更多影響形成的。前述藝人回憶“豫西梆子的調門是四下湊來的,武打來自皮黃戲,引子、曲牌和道白來自羅戲。”說明它吸納了皮黃的武打,羅戲的引子、曲牌和道白,而調門是四下湊來的。
其三,豫西獨特的地方語音和地域文化的影響。常言說語音是聲腔之根,豫西獨特的地方語音,無疑對豫西調的藝術特征有著重大影響。豫西的地域文化,包括它的地理、地形、地貌和氣候環境條件,對當地人們的性格特征有著重大的影響,諸如豫西人的生活習性,情感取向,審美追求等都是鑄就豫西調藝術特征的重要因素。
豫西調是豫西人民群眾和世代藝人智慧創造的結晶,它不僅真實體現了豫西人民的情感、精神,保留了豫西人民生活和文化創造的歷史記憶;而且,有人常把豫西調比作陰,把祥符調視為陽,祥符調的陽剛華美,豫西調的陰柔深沉,陰陽互補,相輔相成,極大地豐富了豫劇藝術的戲劇表現力。豫劇的發展歷史表明,由于豫西調的生成和成熟,它那獨特的藝術色彩和個性特征,不僅體現了人類文化創造的多樣性,也為后來豫劇的走向全國,并創造豫劇發展的歷史輝煌發揮了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紀漢.豫劇源流初探.奔流,1963,(5-6)
\\[2\\]鵬.豫劇源流新探.河南戲曲藝術,1981,(3-4).
\\[3\\]英.豫劇探源.豫劇源流考論,中國民族音樂集成河南省編輯辦公室.
\\[4\\]振山.豫劇豫西調的今昔.豫劇源流考論,中國民族音樂集成河南省編輯辦公室.
\\[5\\]立方.豫劇音樂通論.中國戲劇出版社.
\\[6\\]鎮南.關于豫劇的源流和發展.豫劇源流考論,中國民族音樂集成河南省編輯辦公室.
\\[7\\]林青.豫劇源流考略.豫劇源流考論,中國民族音樂集成河南省編輯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