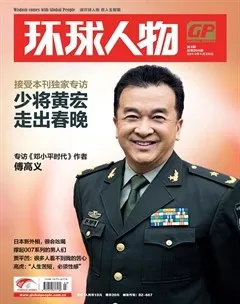“環境問題最可怕的就是不承認”


近日來,中國中東部大部分地區持續遭遇霧霾天氣,造成嚴重空氣污染,多地PM2.5(可入肺顆粒物)監測值瀕臨“爆表”。北京的PM2.5值一度逼近1000,是國務院2012年公布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日平均濃度的30倍,民眾不得不戴上口罩,網友調侃為:自強不“吸”。1月13日,北京發布當地氣象史上首個霾橙色預警。
但對更多城市的民眾而言,當地的PM2.5值是多少,他們無從知曉。因為沒有人去檢測,更無從公布這樣的數字。這時,很多人想到了馮永鋒——早在2011年12月PM2.5剛剛成為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時,馮永鋒就發起“我為祖國測空氣”活動,不僅為上海、廣州、溫州、武漢等城市募集了便攜式PM2.5檢測儀,而且直接推動了當地PM2.5的監測及發布。2013年1月12日,他通過微博呼吁:“讓這些儀器飄流給更需要使用的地方。”
1月13日,馮永鋒又發布微博號召各地環保組織、公益組織給執勤者送口罩。1月16日,已有環保組織在北京發放了近2000個口罩。在馮永鋒的推動下,每一次行動都能收獲相對理想的效果,因為這位環保先鋒和他創辦的公益環保組織已在環保界積聚了很高的人氣,也正在獲得更多人的信任。
賠錢出書
今年42歲的馮永鋒,出生于福建北部的一個小山村,那里的森林覆蓋率在全國排名靠前。1995年,他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看上去與環保并不相干。隨后,馮永鋒去西藏日報社當了一名記者。在那里,他了解了另一種生活方式以及思考方法。“當地藏民最大的智慧在于責己和助人,遇到問題永遠認為是自己過去犯的錯誤;他們的信仰不是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子孫,而是為了整個自然界。”
1998年回到北京,馮永鋒在光明日報科技部任職,繼續當記者。真正踏入環保領域,是在2003年。“當時,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讓我參加‘可持續能源記者俱樂部’的培訓;同時,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又帶我去觀鳥。”從那時起,馮永鋒就沒離開過環保領域。
有一次去蘭州出差,黃河兩岸的十幾個排污口令馮永鋒觸目驚心,它們直接將污水排入黃河,兩岸居民甚至直接把廁所架在黃河上面,垃圾也直接倒到黃河里;去四川時,他往窗外一看,發現“森林怎么碎了”, 因濫砍亂伐而裸露出的土地,讓森林看起來像得了皮膚病一樣……
一篇篇稿件,讓馮永鋒的思想有了轉變:“為什么非要等別人給你命令、給你經費、給你許可才能做事?”2005年,馮永鋒“冒著被開除的危險”自己出錢跑到云南做調查。第二年,處女作《拯救云南》完稿。為把書傳播出去,馮永鋒想了個招:給朋友們寫信,希望他們出300塊錢買10本;后來,他把書寄過去,并告訴他們,愿意給錢就給,不愿意給就算了;再后來,他又附上了一封信,叫討錢信。幾個回合下來,馮永鋒“討”回來5萬元左右——相對7萬元的成本,虧了2萬元。
馮永鋒寫書很快,自處女作問世之后,他又通過先調查再寫作的方式陸續出版了《不要指責環保局長》、《環保——向極端發展主義宣戰》、《沒有大樹的國家》、《邊做環保邊撒謊》、《為民間環保力量吶喊》、《狼無圖騰——草原在哪里》、《教你如何做環保》、《別給環保一點機會》、《做環保,要趁早》9部作品。目前,他正在撰寫與中國水危機有關的著作。
對環保更深的介入,始于2007年發起創建“自然大學”。自然大學有水學院、草木學院、健康學院、山川學院、鳥獸學院、垃圾學院等,每個學院有不同的課題。比如2007年,馮永鋒組織各地開展“城市樂水行”活動,志愿者們沿河而行檢測水質。后來,“樂水行”逐漸演變為自然大學水學院。自然大學在全國各地都有“分校”,學生都是環保志愿者,自愿報名上課,“課堂”就設在大自然中。自然大學成立近6年來,馮永鋒已發起“讓候鳥飛”等數十個活動。馮永鋒倡導當地人在當地做環保,“他們更了解當地的情況,環保效率會更高。可以主動發現環境中的問題,及早解決,不用等政府亡羊補牢。”
2011年12月,當時國內鮮有PM2.5檢測設備,馮永鋒創建的另一家環保組織“達爾問自然求知社”,發起了“我為祖國測空氣”活動。他還在微博上發出號召,向網友籌集資金購買儀器,檢測PM2.5含量。20天后,5萬元籌集到位,2臺便攜式激光粉塵檢測儀被先行送往上海和廣州,隨后溫州、武漢等城市也有了檢測儀。馮永鋒告訴記者,PM2.5檢測項目仍在繼續,因為“每個環保項目都只有開始,沒有結束”。
污染不僅僅是環境問題
從最初的沙塵、揚塵,到現在的霧霾,空氣污染對人身健康的危害,已從明槍易躲發展到暗箭難防。在不清楚這種細小的顆粒物到底會產生什么危害的情況下,人們只是本能地意識到,把口罩戴上就好。但以后還會不會有類似污染發生——口罩后面的每個面孔都充滿憂慮和不安。馮永鋒則直截了當地告訴記者,問題沒有這么簡單,霧霾只是冰山一角。
環球人物雜志:什么造成了這種惡劣天氣?官方的說法是污染物排放量過大。
馮永鋒:是的。很多人以為把東西燒了,它就沒有了。其實,固體物質燃燒后進入空氣中,體量會增長幾千倍。比如說,垃圾如果被焚燒了,它并不會消失,我們只是把垃圾扔到了空中。
環球人物雜志:此前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2012年北京、上海、廣州、西安4城市因PM2.5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數高達8572人。你怎么看這個數字?
馮永鋒:真實的數據可能比這還高。但我想,更嚴重的問題不是死去的人,而是那些沒死去的人——每天都活在污染恐懼之中,承受污染這個慢性病的折磨。
環球人物雜志:會不會有下一次?
馮永鋒:如果沒有有效的治理,未來10年內,會有不止一次。
環球人物雜志:很多人都很疑惑:從2008年開始實施的“藍天計劃”到底有沒有用?
馮永鋒:每個城市的“藍天計劃”進度不同,我覺得各地多少都有些進展,但進展最差的是信息公開。一個城市是生活在這里的人的城市,不是政府的城市,因此,決策過程應當由公眾來參與,決策的結果更應當讓公眾知情。
環球人物雜志:看來空氣污染不僅僅是個環境問題。
馮永鋒:這是一心以為經濟發展就能過上好日子的社會,必然要遭遇的宿命。在這個過程中,真正需要檢討的是政府和企業。中國的污染問題,很多是政府縱容企業導致的。
環球人物雜志:倫敦和洛杉磯等國際大都市在上世紀也都面臨嚴重的空氣污染,后通過立法、執法、改進設備等得以治理。
馮永鋒:它們的經驗可能不適用于我們。我覺得,現在政府首先得做到反應迅速,而我們還在將信將疑,還在拖延,期待大風把污染吹走。
癥結是公眾的權益被剝奪
1月16日晚上,馮永鋒在河南南陽的一家快捷酒店給環球人物記者打電話,語調中帶著淡淡的憂傷。他在調查當地的林木狀況時,發現很多人在偷樹。“好的時候跟村長說一聲,給村長一點錢,就把樹砍倒拉走;不好的時候就直接在月黑風高夜行動,很多樹都是在那d035ff7db17c1755b82718f3cccc11f41dd5912a842d4bd3ab55f5d8638be060里生活了上百年的土著居民。”
環球人物雜志:你現在最關注的中國環保問題是哪方面?
馮永鋒:環境污染尚未退去,生態傷害變本加厲。舉個例子,我們說多植樹可能對凈化空氣有用處。于是,我們就大膽地污染空氣,以為有人植樹能幫助吸附。一些人為了政績,或干脆為了滿足自己的種樹欲,就把天然森林砍掉,然后種上幾棵同樣的樹,還以為自己給祖國披上了綠裝。其實,天然森林是最好的森林。他們這種做法是對自然生態的巨大破壞,因為樹林或森林并不單純是多少棵樹,更是一個生態系統。
現在更可怕的是天然生態系統的“空心化”:濕地生態系統里的物種被捕捉凈盡,河流生態系統里的物種被捕捉凈盡,森林、草原甚至荒漠生態系統的物種,也都被捕捉凈盡。再這樣下去,中國的生態系統將瀕臨崩潰。
環球人物雜志:其實保護環境的道理現在大家都明白,但仍有人受經濟利益驅動,破壞生態環境;還有人以為我知道哪些東西不好,我不用就行了。
馮永鋒:想象一下,你通過污染環境生產出了一種有毒有害的產品,將它賣給別人,自己不用。可同時,別人也在做類似的事。其實這就等于你生活中所有的物品,你生產的、消費的這些物品都是有毒有害的,你自然也就受到了毒害。再想象一下,你把污水排到河中,以為水不會流回來。可是,空氣和水,土壤和陽光,其實都是互通的。我們其實是在享受自己的污染。錢是個非常虛幻的東西,與其說我們獲得了資金上的利益,不如說我們獲得了污染的“利益”,心靈惡化的“利益”。
環球人物雜志:經濟增長和環境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嗎?一兩百年來,幾乎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伴隨了環境問題。
馮永鋒:各國確實都產生過環境問題,但可以看到,很多國家出了問題,會馬上反省,會迅速跟進新的法律來改善。最糟糕的是,出了幾十年的問題,還不承認。我認為,我們在環境問題上最可怕的錯誤就是不承認。
環球人物雜志:那在你看來,環境問題的癥結究竟是什么?
馮永鋒:癥結是公眾的權益被剝奪。喪失了權利的公眾會通過欺壓、掠奪環境權益來獲得自身的尊嚴。也就是說,環境成了公眾任意踐踏的最后的犧牲品。打個比方,最近發生在湖南東洞庭湖的小天鵝被毒殺事件,人們可能第一反應是毒鳥的人最殘忍。可是,這些毒鳥的人,很可能是生活無著的人,權利受到侵害的弱勢人群。如果我們再向前追溯,那些收購的人、制作的人、拿小天鵝當禮品的行賄者以及受賄者、法律賦予了他們神圣的執法權卻從不認真執行的人,是不是該得到更加嚴厲的處罰?
環球人物雜志:你認為解決中國環境問題的根本之道是什么?
馮永鋒:公眾參與,把保護環境的權利交給公眾,他們可以做得更好。公眾可以通過立法,把職責委托給政府。政府如果正當地執行這些法律,很多事情就可以避免。公眾還可以把一些未知領域的探索,委托給環保組織。環保組織與政府的職責是不一樣的。政府應當在法律框架內完成使命,而環保組織恰恰是探索當前法律或者說社會意識中尚未清晰、明確,甚至未察覺的邊緣問題,然后通過持續的啟蒙和倡導,將其逐步推進成社會公共意識,成為日常執守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