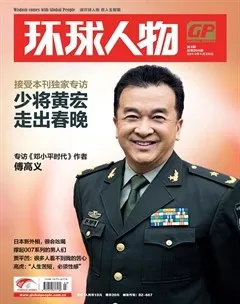賈平凹:“很多人根本看不到我的苦心”

北京霧霾最嚴重的那天,賈平凹在亮馬橋附近一家賓館接受了環球人物雜志記者的采訪。本來身體就不好的他有了點感冒的征兆,他用沙啞的嗓音,不緊不慢地跟記者聊著。
此次來京,賈平凹是為了參加全國圖書訂貨會。他的新作《帶燈》適時出版,成為訂貨會上的一個亮點。36萬字,賈平凹忙了3年,寫了3稿。它以一個在鄉鎮工作的綜合治理辦公室女主任“帶燈”為主角,講述她每天處理的鄉村糾紛和上訪事件,最終,帶燈在一次惡性事件中受到精神刺激,以悲劇結尾收場。“她是現世中的螢火蟲,帶著一盞燈在黑夜中巡行。”書的扉頁中如此寫道。
從1987年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浮躁》開始,賈平凹就一直在關注農村,關注當下社會。《浮躁》寫改革開放之初農村發生的潛移默化的變化;《高興》寫進了城的農民;《秦腔》再現社會大轉型給農村帶來的激烈沖擊和變化;《古爐》追憶“文革”時代的農村……但《帶燈》與他以往的那些長篇小說都不同。
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前社長潘凱雄等評論家看來,這部作品開創了賈平凹“個人寫作的很多個第一”:“這是他長篇小說里最貼近現實的一部,他原來作品中所有的魔幻、變形、夸張都沒有了,只有近距離的寫實”;“這是他第一次以女性為主人公,讓其他人物都圍著一個女人轉”……
“在農村自在得很”
賈平凹到今天連電腦都沒有買,一直過著潛心寫作的生活。他住在西安,離家不遠處有一個專門的工作室。每天早上,他老婆都會開車把他送到工作室,然后他一待就是一整天,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去。天天如此,年年如此,連春節也不例外。“所以嚴格意義上講,我不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有時候和孩子10多天誰也見不著誰,頭一天晚上回去孩子睡了,第二天早上起來孩子走了。”
在那間堆滿了各種書、資料的工作室里,賈平凹一寫就是半天,吃飯也是自己下面條、餃子,買個熟食之類;晚上和幾個好友散散步,邊走邊說話。“這樣生活久了,現在就變得不愛見人,也不愿意讓誰到我的房子來。反正我又不怕孤單,不怕寂寞,只要有吃有喝有煙就行了。”
賈平凹唯一的愛好就是往農村跑。“有空就出去跑跑。在農村自在得很,沒應酬,也沒人管你,想看啥就看啥。有的地方或許還有個親戚、作家朋友,可以告訴你很多情況。”在過去的兩三年時間里,賈平凹去了陜南十來個縣、渭北幾個縣、咸陽北邊、河南、甘肅,“跑了好多貧困地方,收獲還是大。你能看到農村真實的生活,我想一般領導肯定是看不到的。”
帶燈的原型就是賈平凹在一次下鄉中認識的。“她算是鄉政府的小干部吧,那地方都是山,她就把我帶著滿山跑,今天跑這家,明天跑那家,聊聊天,吃也在人家家里。”在賈平凹眼里,帶燈的原型是“鄉政府里的一個異類”。“她是當地人,畢業后就分配到那里,也沒有其它地方可去。她讀書多,算是知識分子,和周圍同事的關系并不好,她根本看不上那伙人。鄉政府那些人,成天喝喝酒呀、打打牌呀,‘帶燈’卻每天埋頭讀書,或者向往啥東西,有點小資情調。雖然掙不到3000塊錢,但手上也算有個小權力,到村子里去農民還聽她的,對她也好,有的也怕她,讓她挺滿足。她有智慧得很,口才好,碰著胡攪蠻纏的人,她纏得比你還厲害,一般人還說不過她。她也會用非正常的手段辦事,哄哄領導呀、對老百姓軟硬兼施呀,基層干部當得時間長了,她也有‘變態’的地方,但基調是善良,就是這樣一個人。”
認識“帶燈”后,賈平凹每天都能收到她發來的短信,“今天開會哩,學啥文件哩,明天誰檢查工作哩,鄉上怎么想辦法,她都告訴我。有的領導講話、工作措施,她甚至都會發給我。差不多有兩年時間。”直到現在,賈平凹的手機中,還保存著大量“帶燈”發給他的短信。
《帶燈》這本小說,雖然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實際上卻是在寫整個基層政府的日常工作。“一般人不了解基層,把書一看,哎呀,中國最基層的政府就是那樣。現實就是很殘酷的。有時候,真是觸目驚心。”在賈平凹看來,寫作是作家的一種責任,“現在社會上的問題一邊解決著一邊又大量積壓,體制、道德、法制、信仰、生態環境,等等。一些朋友說,你干啥的就是干啥的,自己賣著蒸饃卻管別人蓋樓。我說:不能女媧補天,也得杞人憂天么。”
“水吧,你看著平平靜靜,但一進去,就把人淹死了”
環球人物雜志:《帶燈》這本書,寫法和以前不太一樣。比如章節上,全是用關鍵詞串起來,有的兩三行就是一個章節。這是出于什么考慮?
賈平凹:這確實不是傳統的分法。這次主要是寫一個人,不像《古爐》、《秦腔》,一大堆人。《帶燈》的線條有點單,就想把它分成一個一個,把它搖開。分得多了以后,空白處留下的那種氣息,會讓文字背后、讓段與段之間有張力。這個我有點借鑒《圣經》。它也是這種分法。
這算是變換個形式,有時候形式也起點作用。看起來有意思,也好閱讀。
環球人物雜志:您在書的后記中也說了,在這本書中有意在學習西漢品格。
賈平凹:我以前喜歡明清的文章,覺得它們寫得很優美、靈秀、有味道,但是那些文章里裝飾性的東西多,適合寫個小感悟呀、小風景呀。兩漢的更有力量,它有史詩的效果,敘述過程中沒有更多的修飾,是啥就是啥。尤其寫帶燈的日常工作時更是如此,很真實。我做得不一定好,但起碼有這個意識,想增加文章的力度吧。
我老家在陜西商洛,這個地方屬于“秦頭楚尾”,它有秦文化的厚重,也有楚文化的浪漫和靈秀。我的“品種”里有柔的成分,加上長期以來愛好明清文字,不免有些輕佻油滑的跡象,這讓我警覺。
環球人物雜志:小說里,您用了大量的隱喻。連“帶燈”這個名字其實也是有寓意的。她原來叫螢,剛參加工作時跟著去強制計劃生育,完事后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了螢火蟲,但查到“螢生于腐草”,覺得意義不好,就給自己改了名。其實是想保存心里的光亮吧?好像很多人都在讓您解釋這些隱喻,但您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們一看書,就知道了,不必明說”。
賈平凹:確實有隱喻在里面,現實很殘酷,環境就那么惡劣,她還得干,但想潔身自好呀,自己要堅持下去,那就自身帶燈,自己給自己鼓勁么。螢火蟲也是自身帶燈,發出光亮,但螢火蟲也有狠毒的一面……這都是有隱喻在里面的。
有的人寫作,特別刺激、激烈,很尖銳。而我的寫作風格,表面上看著很淡,其實里面包含的東西很多。
環球人物雜志:綿里藏針?
賈平凹:對。就像水和火。有的人的東西你一看,老遠就覺得光亮,而且烤得人不能進去。水吧,你看著平平靜靜,但一進去,就把人淹死了。
環球人物雜志:在寫帶燈的時候,您是不是也從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帶燈有時候辦的事,比如去查縣志看歷代興亡,不像一個有小資情調的女人喜歡做的。
賈平凹:每個作家在寫任何作品的時候,實際上好多東西都是自己的觀點,肯定都要滲透作者的意思。
啥叫智慧,我理解的智慧就是生活中你感悟的東西,積累著,出來以后就是智慧。處理事情,把事情看透了,舉一反三能想到別的道理。帶燈的生活也是這樣。當然帶燈處理那些事情時,不管她咋做,我寫出來以后就是我假借她做的、說的。
環球人物雜志:現實生活中,帶燈的原型給您發短信。書里面,帶燈給“元天亮”(省委秘書)這個人物寫情書。好像小說最后也沒有出現元天亮對帶燈的回應?
賈平凹:寫小說的最怕人對號入座了(笑)。里面有真的也有假的,還有別的地方發生的事。所以我為啥不說帶燈是哪個地方的什么人,要保護原型呀。
元天亮要回應就麻煩了,這書就寫成愛情小說了。情書只是想表達帶燈的一種傾訴、追求,是作為帶燈的一種理想來處理的。她需要這些。另外,如果只寫工作、殘酷的現實,讀者也不愛看。
“我并不是想去維護什么或否定什么,而只是想呈現問題”
環球人物雜志:您也接觸了大量的基層工作人員,對基層問題是否有自己的思考?
賈平凹:好多問題我其實也寫過。現在鄉政府的工作,一個是尋找經濟增長點,領導必須給地方上招商引資。其次就是大量的維穩工作。多少年了,一直在堵、截,就害怕上訪的跑了,為啥我寫這個東西,就是對現實有感而發。
以前社會有好幾條管理渠道:一個是行政管理,比如說鄉政府,有村長、村支書這些;二是法律渠道,有派出所等;三是宗教,過去個個村里都有廟,咱不行到廟里燒個香發個誓,就不敢胡來;最后還有宗族這條線,幾個德高望重的長輩,都可以幫著處理問題。是用各種線把你這個人網住,但現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廟、宗族都沒有了,行政也成了虛的,僅僅是把人管住,也不指導生產了。而且現在農村發展得和城里一樣,互相之間誰也不理誰,人和人之間特別陌生,也沒有那種鄉情了。
說是有法制,可法制又不健全。為什么總告狀?告狀的人腦子里面還是人治的思維,他想著總有一個人能說了起作用。
環球人物雜志:您說過:“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責任”。寫出這些問題,算是您的責任吧?
賈平凹:也不是說咱責任心有多大,畢竟受過傳統教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你是這里的人,當然會為這里的安穩操心。其實咱也是白操心(笑)。所以只好把自己在基層看到的東西、悟出來的東西呈現出來。
當然,作家不是開藥方的,他也解決不了,也不執行具體政策,只能寫出來引起社會重視。
環球人物雜志:您已經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現在城市的問題也很多,為什么這種對農村的情懷卻在您的這些作品中越來越強烈?
賈平凹:我是從農村出來的,血液里還是對農村有感情,進城后這條線也一直沒斷過。農村年年發生啥事,不停地會有人跟我說,尤其我們那個村子里的事。雖然父母不在了,但祖墳還在,逢年過節還要回去祭墳。這是一個生命和靈魂連接的東西。
另外,農村豐富得很。中國現在雖然實行城鎮化,但畢竟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村面積大,比重也特別大,農民問題解決了,我覺得別的問題才能徹底解決。關心農村、關心農民其實是在關心整個中國的進展。城市里我只對文化圈熟悉,寫起來會顯得單調一點。
現在更多年輕作家寫城市里的社會問題,住房、醫療,等等,我覺得我還是寫農村吧,因為那些東西越來越沒人寫了。我們熟悉的農村也在一步步消亡,或者在發生質的變化。既然我知道,就要把這一段寫出來。
當下生活很難寫,你不能胡寫,穿啥喝啥做啥,別人一看就知道你寫得對不對。我要是寫清朝的、明朝的,由我哩。“畫鬼容易畫人難”,畫鬼咋都行,你畫人,敢把鼻子安錯地方嗎?
環球人物雜志:這是您耗費了3年心血的作品。您期望它有什么樣的讀者?
賈平凹:中國有中國的文化背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任何事情和解決這個事情的辦法,都帶有獨特性。有時候讓外國人沒法理解,連中國人也覺得很荒謬,但確實存在。
中國現在分左派右派,水火不相容。左派就說,你寫的這些問題,都是改革開放鬧的,原來多好呀。右派就說,這是現在體制不行,要換一種體制。從我的本意上來說,我并不是想去維護什么或否定什么,而只是想呈現問題,讓有識之士思考解決方法,給世界提供一份中國經驗。好多人根本看不到我的苦心,寫作很容易就變成政治之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