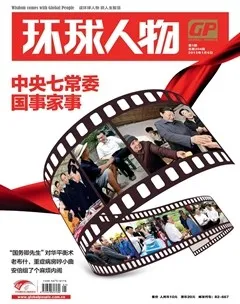靠掙錢提升幸福是幻覺

在眾多媒體記者與中國“粉絲”苦苦等候了兩個小時之后,一頭銀發的馬丁·塞利格曼終于出現在他的新書《持續的幸福》發布會現場。發布會當天,這本書就被讀者搶購一空,可見塞利格曼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
塞利格曼被譽為“積極心理學之父”,他不只關注傳統心理學注重的“如何減輕人們的痛苦”,而是更專注于研究如何建立人們的幸福感,并讓幸福感持續下去。
幸福是教育的本質
“我要發起一場世界教育的革命。除了工作技能,年輕人還應該學習幸福的技能——如何獲得更多的積極情緒、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意義、更好的關系和更積極的成就。”塞利格曼在接受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專訪時,一再強調積極心理學對于人生的意義。
“父母希望孩子得到的,往往是自信、善良、健康等,簡言之,就是幸福;而學校最希望孩子學會的,則往往是考試、工作、成就等,簡言之,就是成功的方法。這兩者其實互不相干。”塞利格曼提出,應該在學校教“幸福”這一課程,“傳統教育的目標是學習,而更高的幸福感能提升學習能力。事實上,教育的本質,就是讓人擁有幸福。”
2008年1月,塞利格曼飛往澳大利亞,為澳大利亞最古老的貴族學校——吉朗學院的100名老師進行關于積極心理學的培訓。“第一天,校長史蒂芬·米克毫無表情、冷冰冰地致了歡迎詞,毫不掩飾他對積極心理學的懷疑;第二天,他就被培訓內容打動了;到了第九天,他以一個英國人難得的熱情擁抱了我的部下,還說,這是學校歷史上的第四大事件,而之前的3件,都是關乎學校發展的大事。”
“過去近一個世紀,心理學主要研究人心理方面的問題,憂郁、焦慮、痛苦等等,但并不能幫助人真正實現幸福。而我發現,積極的心理不僅有助于認識快樂,還能激發人的力量。積極心理學有3項使命:一是研究消極心理,治療精神疾病;二是讓所有人生活得更加充實、有意義,身體更健康,工作更出色,心靈更平和;三是鑒別和培養天才。”在塞利格曼看來,心理學提供的并不只是對失敗者的救助功能,還可以幫助你挖掘出你的正能量。
中了心理學的暗箭
“積極心理學教育是非常有用的。比如,從前的我脾氣不好,經常朝孩子發脾氣,但現在,我的性格變得更積極向上,與孩子的關系也更好。”塞利格曼坦率地告訴記者。
塞利格曼1942年出生于美國紐約州首府奧爾巴尼,兒時的他貪玩好動。13歲時,他偶然讀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它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塞利格曼一直認為,他跟積極心理學有某種宿命的淵源。“1961年,我懷著改變世界的夢想進入了普林斯頓大學。我被心理學吸引,它像一支暗箭射中了我,那種感覺太微妙了。”
后來,塞利格曼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實驗心理學碩士、博士。“我讀博士時研究的是小白鼠,我發現,不可預測的電擊比可預測的電擊更讓它們害怕,因為它們不知道什么時候安全,不可預知的災難讓小白鼠始終處于悲觀的狀態,失去了生存的快樂。”由此,他認識到:人或動物因為不可控事件而不斷遭受挫敗,便會感到自己對于一切都無能為力,進而絕望抑郁,這種無助感也成為許多心理和行為問題產生的根源——這就是轟動了心理學界的“習得性無助”理論。
1967年,塞利格曼辭去了他在康奈爾大學的副教授職位,回到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系。一天,他偶遇精神病學教授阿倫·貝克。“馬丁,如果你還繼續做與動物打交道的實驗心理學家,你就是在浪費生命。”貝克盯著塞利格曼說。“我一下震驚了,幾乎被口中的食物噎住。我意識到他是對的。于是,我成了一名應用心理學家,明確地以問題為目標。”
在經年累月的學習和研究之后,塞利格曼發現,“樂觀”可以通過后天的學習來獲得,他的研究方向從此由悲觀轉向了樂觀,由消極轉向了積極。
1998年,56歲的塞利格曼以歷史最高票當選美國心理協會主席。“我作為主席的第一項提議是以實證為基礎的心理治療,結果它胎死腹中。那時我才發現,因為我的研究方法與別人不同,其他應用心理學的專家與我的那些純粹的科學家同事們都認為我是一只披著羊皮的狼。”
“事實上,正是這次碰壁,讓我反思了心理學的本質問題,我堅信心理學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亡羊補牢,積極心理學就這樣誕生了。”塞利格曼說,“它的使命就是,將最新的研究和現實應用結合起來,讓人們更加快樂地生活。”
幸福是可以測量的
當今社會,很多人認為,成功是幸福的基礎,而成功又包括很多內容:賺更多的錢、受更好的教育、保持健康等等。但這些詞,并沒有出現在塞利格曼的幸福詞典里,取而代之的是:婚姻、朋友……
環球人物雜志:從您的經典著作《真實的幸福》到新書《持續的幸福》,積極心理學總是和幸福聯系在一起。在您看來,幸福和不幸福的人,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塞利格曼:大約9年之前,我開始探索非常幸福的人和其他人之間有什么不同。結果卻發現,這些幸福的人并不是有錢人,大多相貌平平,身材也很一般,也沒碰到過什么特別的好運,他們和別人不同的一點,是他們特別合群。他們較少時間獨處,大都處在一段戀情中,每個人都有很多朋友,因此他們感覺生活積極而快樂、充實而幸福。但是,注意了,這只是相關數據,不是因果關系。
環球人物雜志:但現在更多人會把幸福和錢聯系起來。
塞利格曼:其實,越看重錢的人對他的收入越不滿意,也就對他的生活越不滿意,越缺少幸福感。
我的團隊對40多個國家進行了生活滿意度或者說是幸福感的調查,我們發現:對貧窮國家而言,幸福感是和財富一起增長的,也就是說,人民越富裕,他們就越幸福。而一旦國民收入超過年人均8000美元(約合49875元人民幣),這個相關性就開始消失,財富的增長,哪怕是大幅增長,也不再能帶來更多幸福感。并且也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當一個國家變富時,抑郁癥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比例也隨著飆升。
環球人物雜志:通過您的研究,您認為什么才能算幸福?
塞利格曼:在我看來,幸福應該包含3個不同的概念,第一是愉快的生活,第二是充實的生活,第三是有意義的生活。
想要實現幸福人生應具有5個元素,我們稱它為PERMA:積極的情緒(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良好的人際關系(relationships),做有意義、有目的的事(meaning and purpose)以及成就感(accomplishment)。
環球人物雜志:中國這幾年也會發布“幸福指數”,但很多人都對此有疑問:幸福是可以測量的嗎?
塞利格曼:幸福是可以測量的,就像測量國民生產總值GDP一樣,一個國家的幸福程度可以用“蘇·于佩爾劍橋幸福量表”測量。這是劍橋大學幸福感研究所所長弗里西亞—于佩爾和他的學生蘇德中的研究所得。就是測量人們對工作的投入程度、人生意義、人際關系、有多少積極情緒以及做出了多少成就。從2002年開始,歐洲20多個國家每兩年都會進行一次幸福感社會調查。
環球人物雜志:您怎么看中國人的幸福指數?
塞利格曼:積極心理學有個最終目的:到2051年,51%的世界人口達到幸福的定義。中國現在約占全世界人口的1/4,顯然,除非中國能達到51%,不然全世界51%的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
中國在過去20年里創造了經濟奇跡,從一個窮國變成一個幾乎是富裕的國家,這是一個奇跡。然而在中國,經濟發展無論在個人還是社會的層面上,都有著更高的優先權,掙錢比提升幸福更重要,這是構建幸福的一大障礙。有人認為,錢是提升個人和國家PERMA的最好途徑,這種看法多半是陷阱和幻覺。一旦達到一定的生活水準,財富對于幸福的提升作用就會大幅減少。現在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中國是否愿意致力于提高國民的幸福感。我建議,政府——不僅是中國政府,而是所有政府——的作用,不僅是發展經濟,還應該提高人民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