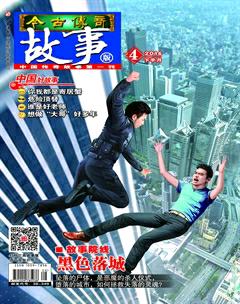你我都是寄居蟹
菊韻香
唐小飛的家距離海邊很近,是間帶院落的平房。那天是唐小飛14歲的生日,媽媽覃芬剛把蛋糕端上桌,就聽鐵皮大門被砸得“咣咣”響。
不一會兒,一個光頭便帶著兩個混混踹開院門直奔屋內。唐小飛不由得打了個寒戰(zhàn),本能地退到了媽媽覃芬的身后。
“你們是誰?想干啥?”覃芬忙護住唐小飛,壯著膽問。
“我姓鄭,你是唐長林的老婆吧?”光頭鄭從皮包里掏出一沓賣房合同!原來,唐小飛的爸爸唐長林因為賭博,輸光了存款,還欠下一屁股債。為籌錢翻本,他竟不顧老婆孩子的死活,把房子賣給了光頭鄭,并拿走了15萬全款。可他轉眼又將這些錢輸光了,為了躲債,他干脆玩起了人間蒸發(fā)!
覃芬悲憤到了極點,她當即下了逐客令:“他沒跟家里商量,這合同不算數(shù)。你們滾,再不滾我可要喊人了!”
光頭鄭怒道:“賴著不挪窩是吧?哼,那就別怪老子動粗開攆!”一旁的兩個混混當即伸胳膊挽袖子,架起覃芬就往院外拖。
“別碰我媽,快放開她!”唐小飛哭著叫道。
此刻,院子里已經(jīng)聚集了一堆看熱鬧的人,其中有個叫宋大胡子的魚販說道:“光哭有屁用?眼淚又淹不死人!”
唐小飛挨了嘲諷和激將,還真抹抹淚沖向了光頭鄭。光頭鄭塊頭大,胳膊粗,伸手一推就將唐小飛搡了個趔趄。
宋大胡子又說:“夠不著腦門是吧?那就踢他褲襠。”唐小飛依言照做,弓身彎腰,使足勁撞向光頭鄭的下三路。光頭鄭大為惱火,罵道:“宋大胡子,我招你惹你了?能不能閉上你那臭嘴?”
“嘿,敢罵我?”宋大胡子不緊不慢地接茬回道,“唐小飛過了今天才滿14歲。也就是說,今天打人不犯法,責任歸他那死老爸。聽清楚沒,再不抄鐵鍬掄他,還等啥?”
眼瞅唐小飛真去抄家伙玩狠的,光頭鄭落荒而逃。唐小飛緊跟著追出院,抱住媽媽覃芬哭在了一起:“媽,我把他們打跑了,全打跑了。以后我會好好保護你,不讓任何人欺負你!”
可是,哭不能解決問題,還是得給人家騰房子。說來也真夠應景的,門外的沙土路上,雨水洼里,出現(xiàn)了一只纖毛寄居蟹。它寄居的海螺殼破了,不得不臨時抓了只臟兮兮的瓶蓋,護住后背惶惶跑路,看起來格外心酸凄涼。
瞅著媽媽覃芬邊收拾東西邊暗暗掉眼淚,唐小飛感覺他們娘倆的處境像極了那只丟了殼的寄居蟹。好在傍晚時分,大門外響起了幾聲汽車鳴笛。與此同時,濃烈熏人的魚腥味也飄進了院。
單聞這股味,唐小飛就知道是宋大胡子。宋大胡子把頭探出車窗,說:“我要去外地給幾個客戶送海產(chǎn),來回至少得十天半個月。如果你們娘倆不嫌腥味重就去我家住吧,等租到房再搬走。”他說著扔給唐小飛一串鑰匙,說,“你也不小了,別總往你媽身后藏。”
說實話,唐小飛此前對宋大胡子并無多少好感,一個大老爺們,整日邋里邋遢、臭烘烘的。據(jù)傳,他老婆趙媚就是嫌他臭,在幾年前卷了他的積蓄跑了。可讓唐小飛稍感驚訝的是,他和媽媽走進宋大胡子住的那套兩室一廳的樓房時,居然沒聞到半絲怪味。
隨后兩個月,覃芬東奔西走,到處打聽唐小飛老爹的下落,可是沒有半點兒線索。
一轉眼,4年過去。同處一個屋檐下,盡管宋大胡子常逼唐小飛大口吃肉,偶爾哄他喝一口辣喉烈酒,還裸著膀子成筐成筐地扛魚,站在市場里扯著脖子討價還價,可唐小飛漸漸覺得這人除了嗓門大外,似乎并沒那么討人厭。
這天,媽媽覃芬紅著臉說想跟唐小飛商量個事,唐小飛立刻就明白了,他當即表了態(tài):我沒意見。于是,三口人兩個家,變成了一個家。原本以為,日子會就此安穩(wěn)地過下去,但讓唐小飛怎么也沒料到,一年后,失蹤5年的唐長林突然露面,找上了門!
一同來的還有一男一女兩個人。男的唐小飛認識,光頭鄭,如今開起了房屋中介公司;女的看上去40多歲,打扮有點妖。
“你們來干啥?我媽和宋叔都不在家。”唐小飛說。唐長林囁嚅道:“兒子,爸爸想你了——”
“別拐彎抹角的。”女人搶過話頭,對唐小飛說,“這可是我家,你算哪根蔥啊?”
這個女人是宋大胡子的前妻趙媚!唐小飛稍一愣怔,反唇相譏:“你不是跟人跑了嗎?”
“甭管跑不跑,反正我和老宋沒離婚。”趙媚環(huán)顧四周,陰陽怪氣地回道,“小子,你和你媽也看上這房子了吧?”
明擺著,趙媚是沖房子來的。最近幾年,這座臨海小城大搞旅游開發(fā),房價自然噌噌上漲,較趙媚與人私奔時已翻了數(shù)倍。光頭鄭里外走上一圈,也估了一個市場參考價——80萬。
“你也是為了房子來的吧?”唐小飛盯著爸爸唐長林問。
“兒子,你聽我說。”唐長林觍著臉說,“趙媚找我,是想讓我作個證,說我和你媽沒離婚。兩邊都沒離婚,那宋大胡子和你媽的結合就涉嫌重婚。而趙媚仍舊是原配,是這房子的女主人,自然有權分到這房子的一半,也就是40萬。”
唐小飛登時來了氣:“爸,你以前好賭,坑苦了我媽。現(xiàn)在又來坑她,你到底有沒有良心!”
唐長林急忙辯解:“只要你咬定是宋大胡子花言巧語騙了你媽,你媽就沒事兒。況且趙媚也許諾,只要咱爺倆幫忙,一人兩萬好處費。嘖嘖,這錢可是白撿的。”
“你走,走啊!”唐小飛憤怒地打斷了唐長林,“我決不會幫你干這種卑鄙的事,你滾!”
趙媚沒再理睬唐小飛,她沖進宋大胡子的臥室,見啥翻啥,逮啥扔啥。最后,她翻出了一個木盒,里面竟然是覃芬和宋大胡子的結婚證!
“兩邊都沒離婚,他倆咋能結婚?這肯定是假的!”趙媚一氣之下準備將證件撕了,卻被唐小飛劈手搶了去。趙媚又抓起一份材料,展開一看,發(fā)現(xiàn)是法院下達的判決書。上面寫得清清楚楚,趙媚攜款失蹤,宋大胡子向法院提出了離婚訴訟。法院用公告方式送達起訴書等法律文書60日后,依法宣判準予離婚。同樣,在木盒里,唐長林也看到了覃芬和他的離婚判決書。
“這不是假的,也不是花錢辦的吧?要沒啥疑問,請你們馬上走,馬上離開我家!”唐小飛向三人發(fā)出了逐客令。
趙媚沒理他,接著又翻開了一本證件。她看完后,突然渾身一顫,像發(fā)瘋的母夜叉般撲向唐小飛,張牙舞爪連喊帶罵:“小混蛋,小王八犢子,都是你壞了姑奶奶的好事!”
唐小飛往后退了幾步,一不小心絆了一跤。趙媚瘋狂地扼住他的脖子拼命往死里掐。關鍵當口,只聽“咚”的一聲悶響,趙媚立馬倒了下去。
倉皇出手的,是唐小飛的老爹唐長林。唐長林隨手亂劃拉,抓起只花瓶砸中了趙媚的頭,接著也如注射了雞血般亢奮大叫:“哈哈,我兒子發(fā)了,發(fā)了!”
時間過得真快,轉瞬又是半年。這天,宋大胡子匆匆回了家:“小飛,我覺得,你應該去看看他。”
宋大胡子口中的他,是唐小飛的父親唐長林。那天,他把趙媚打得顱腦受損差點變成植物人。接下來,警方介入,唐長林因犯賭博罪和傷害罪被判刑,鋃鐺入獄;光頭鄭也牽涉其中,因開設地下賭場、組織賭博罪落入法網(wǎng)。
“他救我,是看到了房產(chǎn)證。”唐小飛說。
沒錯,趙媚形同中邪,是因為她最后翻開的那本是房產(chǎn)證。別說她,就連唐小飛都沒想到,宋大胡子早把房子過戶到了他的名下!也難怪唐長林一瞄見房產(chǎn)證上的名字,會那般亢奮失態(tài)。
而媽媽覃芬說,當光頭鄭要房、唐小飛瞅著那只丟了殼的寄居蟹默默流淚的時候,宋大胡子就動了要給他一個家的念頭。覃芬不同意,可宋大胡子說:“其實,我們都是寄居蟹,一輩子忙忙活活,為的就是找一個殼。殼里有人,人心有愛,才會溫暖,才叫家。不然,那只是個冷冰冰的殼。”
聽到這兒,唐小飛沖宋大胡子點點頭,說:“我會去看他,也會用愛幫他戒掉賭癮,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