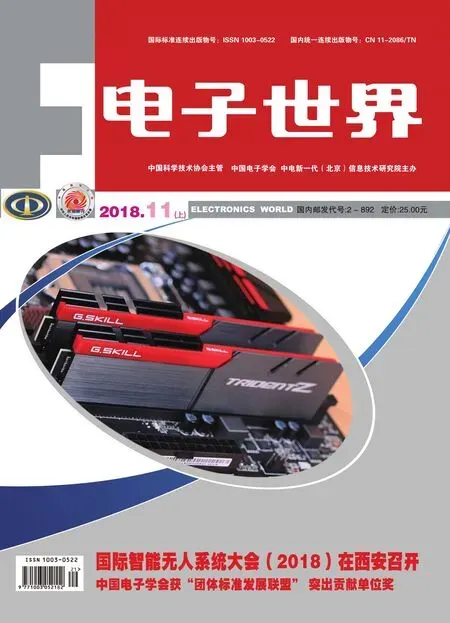針對鐵路10kV配電所綜合自動化設計的研究
中國鐵建電氣化局集團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余經華
在鐵路工程施工建設中,電氣化已經成為主流建造理念,由于鐵路工程自身有著線路長、所處環境條件差等特點,促使鐵路電氣配電網也有著線路冗長、電力設備及線路運行穩定性較高等特性。在鐵路電力系統中,10kV配電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0kV配電所能夠對鐵路沿線提供良好的電能供應,保證鐵路各個部門之間的通信質量,各個隧道、橋梁等關鍵部位的監控持續性等等。從目前來看,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的提升促進了鐵路工程電氣化、自動化建設速度,相應的要求也在逐漸提高,這種現狀要求10kV配電所必須要進一步加強綜合自動化設計水準,保證鐵路各個設施、設備以及列車能夠在高質量電能供應基礎上穩定、可靠、安全的運行。
一、引言
在鐵路工程中,配電所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其能夠為列車和鐵路設施設備的正常運行提供基礎電力保障,如果配電所存在故障問題的話,就會嚴重影響鐵路運輸的正常運行,為社會和人們的出行造成阻礙。10kV配電所是鐵路電力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承載著大部分列車及設備、設施的電力供應工作,在信息化時代下,各種高新技術不斷發明和應用,促使鐵路相關部門必須要針對10kV配電所進行科學的設計和完善,尤其是其中的自動化設計工作。鐵路10kV配電所的自動化設計能夠有效提高鐵路部門工作效率,降低人力成本的投入,提高電力供應穩定性,為列車運行及相關設施設備的正常運轉創造了更好的基礎條件。下文就是針對鐵路10kV配電所綜合自動化設計進行簡要的分析和研究,并加以敘述。
二、鐵路10kV配電所綜合自動化的設計思路與比較
鐵路10kV配電所綜合自動化在進行設計的過程中,相關技術人員就是將計算機系統、網絡信息技術、數據庫等等先進的技術融合在一起,之后再根據配電所的實際需求進行重新劃分、設計,進而獲得一個全新的、對配電所全部電氣設施、設備、線路等能夠自動化管理、控制、保護的系統。總之,鐵路10kV配電所綜合自動化系統就是一個具有全面監管和控制功能的大型計算機網絡系統。
配電所綜合自動化系統的結構分為3個層,分別為站控層-調度端、當地監控單元;網絡層-雙環光纖網、以太網以及通信單元;間隔層-保護測控裝置、同時交直流系統等智能設備通過通用通信裝置納入配電所的綜合自動化系統中。變配電所自動化系統一般采用由間隔層和站控層組成的系統結構。間隔層裝置面向一次設備完成數據采集、保護與監控功能,而站控層采用通信處理機裝置與工業PC機完成與上級調度自動化主站通信及當地監控功能。
配電所自動化系統既可集中組屏,亦可分散布置。本文主要就集中布置結構和分布分散布置結構進行分析、闡述。集中式系統結構的特點是結構較為緊湊,實用性好。不過其存在調試繁瑣、運行過程中不直觀,檢修和維護不方便,施工任務量及難度都較大等缺點。采用集中式結構是將測控、保護裝置設置在控制室集中組屏后,在保護屏對相應回路實現各種模擬量、開關量采集,完成配電所的數據采集和實時監控和保護等功能。各開關柜與控制屏需要通過二次電纜相連接,測控、保護裝置至后臺主機通過通信電纜連接。
分布分散式結構的特點是按照配電所的元件、斷路器間隔進行設計,間隔級控制單元的自動化、標準化使系統使用率更高。此結構是將配電所一個斷路器間隔所需的全部數據采集、保護和控制功能集中由一個或幾個智能化的測控單元完成。測控單元可以直接安裝在高壓柜上,相互之間用光纖或特殊通訊電纜連接,減少了電纜傳送信息的電磁干擾,且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方便維護和擴展,大量現場工作可一次性在設備制造廠由廠家來完成。分散保護直接將需要進行保護的單元設置在高壓開關柜上就地保護,僅僅通過通信光纜將其連接,不需要大量的二次電纜,這將降低工程投資,減少設備安裝調試的工作量,降低運行維護人員的工作強度,發生故障便于查找,會大大縮短故障處理時間。
三、鐵路10kV配電所綜合自動化的應用分析
1、案例概述
某鐵路10kV配電所中設置有26個高壓柜、2路電源進線、17個斷路器,該配電所的綜合自動化系統布置的是分布式結構,設計及施工完成后,實際使用效果非常好,相比于集中式結構有著更好的特性,下文對幾點特性進行簡要分析。
2、施工方面
通過分布式結構對施工人員的平均工程量起到了降低作用,在進行線路連接的過程中,也省去了幾個步驟,減少了施工時間,節省了施工材料,從而加強了企業對成本的控制效果。其次,使整個工程的施工建設更加方便、容易,提高了施工速度,這對于企業綜合效益的提高有著很好的促進作用。第三,因為分布式結構中所需的電氣設備有所減少,促使10kV配電所二次設備的調校更加便捷,總空間面積也有所降低。第四,通過對分布式結構的科學應用,與集中式結構比較的話,會在很大程度上節約施工建設及設備購買的綜合成本。
2、場地實際應用
因為分布式結構的多個優點,促使鐵路10kV配電所各個設備、線路的檢修維護人員工作量大大降低,同時也可以相應減少工作人員的數量。分布式結構應用的分散保護方式非常科學,這種方式能夠更好的完成自動化設計動作,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配電所的整體運行穩定性和可靠性,在最大程度上減輕工作人員的負擔。在分布式結構之中,采取的保護動作都是獨立進行的,這樣就能夠在進行維修和養護的過程中對故障及問題的源頭更加明確,避免出現誤操作,影響配電所的運行質量,同時,也能夠有效降低故障發生幾率,積極、及時采取保護動作。此外,如果配電所相關設施設備出現故障問題,分布式結構保護措施也能夠迅速的找到故障原因,并向維修人員作出提示。
四、綜合自動化設計中存在問題及處理策略分析
1、微機保護裝置過壓
這個故障出現的次數比較少,造成該故障產生的重要因素就是雷擊,夏季出現的情況相對較多,北方秋季和冬季不會出現該故障,南方各個城市出現該故障的較多,引起故障的原因是雷電擊中線路母線或擊中信息數據傳送線路。處理辦法包括以下幾種:首先,應針對線路及重要設施設備進行雷電保護;其次,加裝浪涌保護設施,增加接地處理;最后,應在數據傳輸及線路中安裝避雷針等防雷設施。
2、保護裝置的集中和分散
在鐵路10kV配電所中,保護裝置的設置非常必要,在關鍵時刻,保護裝置能夠對各個設備及線路進行有效的保護,防止由于其它設備出現故障問題而受到影響和損壞。集中保護就是把高壓開關柜中可能受到危害的單位安置在控制室保屏上,這樣就實現了集中保護;分散保護就是說對高壓開關等需要被保護的裝置、設施等直接進行單一保護。集中和分散保護模式在原理上存在不一致性,促使所實現的功能性也不同,兩者存在較大的差異性。比如說,在使用集中保護裝置時,因為所有設施設備的保護是統一在一起的,容易造成一個設備損壞影響其它設備、線路等也出現一定的損傷,甚至發生嚴重事故,而且,設備、設施的集中保護方式要使用更多的線纜,而且工程量非常大,鐵路部門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都比較高,同時,也容易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
3、組網方式選擇
在對組網方式進行選擇時,可以采用485總網線、現場總網線以及工業以太網三種,筆者在下面對這三種組網方式進行簡要分析。首先,485總網線的使用范圍較窄,一般都是應用于信息收集和傳輸量低、運行穩定性要求小和設施距離較遠的條件下。其次,現場總網線一般情況下不建議使用,因為該網線線路市場參標參差不齊,雖然其有著良好的穩定性和信息傳送質量,但是并不推薦使用。最后,工業以太網在三者中屬于非常先進的,而且在目前鐵路配電所電氣自動化系統中的應用也非常廣泛,因為其具備統一規范標準,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其也會占據主要市場。
4、加設備用電源自動投入裝置
在現階段,我國的社會發展建設速度如此之快,促使鐵路工程也在大力發展建設,從目前來看,鐵路工程為適應社會及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已經逐漸使用雙電源模式,這樣就能夠確保在主電源發生故障時,備用電源能夠接續上,從而保證鐵路運輸工作的安全、穩定、持續運行。除此之外,如果鐵路工程施工建設的過程中,由于電力問題而造成停工,必然會影響鐵路部門的綜合效益,而加設備用電源后,則能夠確保不會出現因為電力問題造成的停工等影響。
5、增設并完善消防系統
在鐵路10kV配電所保護控制設備分散布置的高壓室中應對消防系統進行加裝或進一步完善,其能夠根據設備的實際運行狀況進行自動調整保護措施和動作,一旦出現故障或問題,消防系統首先介入采取保護動作,防止其它設施設備遭受損害。
6、防雷接地保護
因為鐵路沿線比較長,雷電災害又無法進行控制,這就造成鐵路線路及沿線電力設施、設備等常常會受到雷擊故障,針對該問題,鐵路部門也采取了幾種科學的處理策略,那就是避雷針、避雷器以及防雷保護三種。這三種方法都能夠對雷電進行科學的預防,10kV變電所在容易受到雷電傷害的區域應設置防雷設施,從而提高配電所的運行質量和穩定性。
五、結語
在當代社會中,鐵路運輸對于人們的生活有著重要意義,其也能夠有效促進各個城市之間的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溝通交流,由此可見,鐵路運輸對人類及社會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在鐵路工程中,10kV配電所是鐵路電力系統非常關鍵的組成部分,其運行穩定性及先進性能夠直接對列車及相關設施設備安全運行產生影響,隨著自動化技術在各個領域中的應用取得顯著的效果,10kV配電所也逐漸進行綜合自動化設計及改造。通過綜合自動化對10kV配電所設計能夠有效減少鐵路電力系統故障問題的發生概率,能夠減少人員的投入,提高電力系統工作效率,是一舉多得的重要手段,綜合自動化設計也是鐵路10kV配電所今后發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