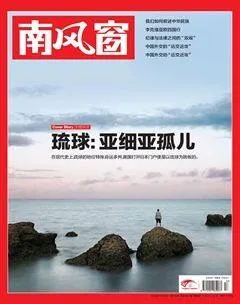新加坡法治的源頭
王江雨
新加坡作為一個華人社會不同于傳統中國社會(如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最大特征是它的法治,這一點新加坡自身深以為傲,也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李光耀曾經指出,新加坡成功的關鍵是法治(rule of law),以法律在今日新加坡社會至高無上的地位來看,可以說這一點并非虛言。
對于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華人社會而言,新加坡能建成一個法治社會確實令人興奮。很多觀察者認為,以儒家文化為根基的華人社會,具有和現代法治相沖突的內在因素,所以華人社會不能建成法治社會。新加坡法治建設成功的例子至少表明,“華人社會無法治”并不是一種宿命,只要某些條件具備(如領導者的政治意愿和民眾的參與),華人社會也可以依法而治。
我們當然必須認識到,新加坡法治的成功有其自身的起始條件和路徑依賴過程,不可能被其他社會照搬。盡管如此,從這個前殖民地國家的法治經驗中還是能提煉出來一些對中國有意義的啟示。
鑒于新加坡廣為人知的“嚴刑峻法”,國內很多評論者津津樂道于“新加坡是法家治國”的典范,認為新加坡社會的井然有序是藉由法家所主張的嚴密的社會控制與刑罰的威懾手段所造成的。然而這種看法頗為一廂情愿。新加坡的法律制度雖然暗合了法家的不少主張,但法家并不是新加坡法治的思想源頭。說實話,幾乎完全由英文教育的精英所統治的新加坡,恐怕在成為法治國家以后也不會有什么人懂得或有興趣去了解何為“法家思想”。建國之父李光耀雖是華人,但生長于一個極度西化的殖民地華人家庭,本人從未受過中國古典文化的教育,30多歲以前都不會說華語,不可能從中國法家思想中汲取任何治國經驗。
大體而言,新加坡法治的制度和思想源頭,一是英國的法治傳統,二是李光耀個人在日本占領新加坡時代的切身經驗。
在新加坡1965年獨立之前,它已經實行了將近150年的英國普通法制度。新加坡獨立后,雖然在某些方面根據本國情況作了靈活調整,但大體上沒有改變通行于新加坡的英國法律傳統。事實上,新加坡1994年才廢除本地案件向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上訴的條例,在此之前管轄新加坡的最高司法機構一直是英國樞密院。根據1993年的《英國法適用法令》,英國普通法在新加坡繼續保持效力,除非經過本地法令的特別修改。
英美普通法并非完美,但卻有一些能夠保障民權的核心要素,只要是成功實施普通法的國家,不管政府如何覺得不方便,都不能完全廢棄這些要素,否則就會毀壞普通法體系的基礎。要素之一是對個人自由的重視,二是對私人財產權的保護,三是程序規則至上,“程序優先于實體權利”。新加坡普遍繼受英國普通法體系,即使沒有普通法母國英國那樣完善的權利保障制度,也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貫徹這些法治原則。換言之,現代法治一經貫徹實施,法治在一定程度上就按照其自身規則至上的慣性運行,而不再可以把法律作為統治手段并可以隨時棄如敝屣。
但是新加坡的嚴刑峻法、重刑重罰的法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李光耀在日本占領軍統治時期的切身經驗。1942年2月,日軍擊潰守衛東南亞的英軍,占領新加坡,將之更名為“昭南島”。李光耀在日本占領之下生活了3個月,親身經歷了日本如何統治被占領區,本人也差點被屠殺。他后來在回憶錄里對日軍暴行痛加譴責,但也不諱言對他們鐵腕手段的欣賞。李光耀稱,“日治時期的3年零6個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它讓我有機會把人的行為、人類社會以及人的動機和沖動看得一清二楚”。尤其是,“嚴懲不貸使犯罪活動幾乎絕跡”,故而,“在物資匱乏、人們半餓不飽的情況下,可以夜不閉戶,犯罪率之低叫人驚奇”。李光耀由此而領會到的經驗是,“有人主張對待和懲罰犯罪應該從寬,認為刑罰減少不了犯罪,我從不相信這一套,這不符合我在戰前、日治時期和戰后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