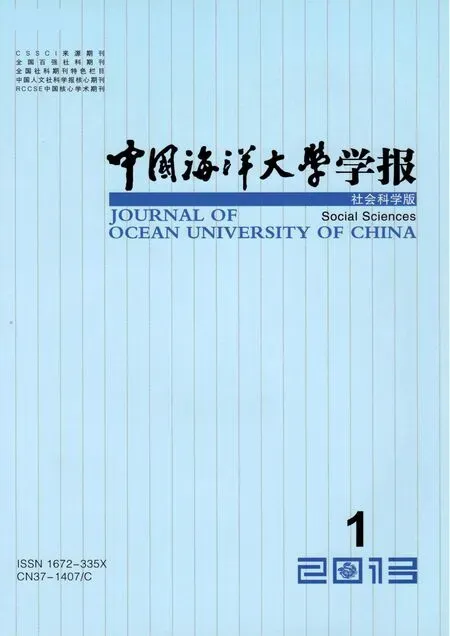國際投資條約中的“利益拒絕”條款研究*
馬 迅
(重慶工商大學 法學院,重慶 400067)
國際投資條約中的“利益拒絕”條款研究*
馬 迅
(重慶工商大學 法學院,重慶 400067)
國際投資條約中的“利益拒絕”條款的目的在于確保投資條約不被第三國投資者控制的所謂“郵箱公司”所利用。近年來該條款成為國際投資仲裁中爭議較大的條款之一。該條款的適用條件具有模糊性,而其到底針對管轄權問題還是實體問題、如何具體實施該條款以及該條款的實施是否具有溯及力都具有較大的爭議。對于這些爭議,一方面由于不同條約的具體表述不同,因此仍需要進行個案分析,另一方面,由于相關案例尚不十分豐富,因此某些仲裁庭也不能給出十分準確解釋。因此,對于該條款的研究有助于日后相關條約的立法,也有利于仲裁員正確理解該條款。
國際投資條約;利益拒絕條款;郵箱公司;能源憲章條約
近年來,隨著國際投資仲裁案例的不斷增多,在國際投資條約中的某些以往不被關注的條款開始引起東道國及投資者的重視。而仲裁庭通過其仲裁活動,則對于這些條款進行了解釋和運用,但這些解釋和適用是否符合締約國的本意,往往引起較大爭議。比如,許多國際投資條約中都具有的“利益拒絕”條款(denial of benefits clause)就是一例。這一條款的主要目的在于確保投資條約不被第三國投資者控制的所謂“郵箱公司”所利用。[1]以往該條款極少引起當事人的重視,然而近年來已經有好幾例投資案例涉及到這一條款的解釋,在某些案例中還成為當事人雙方爭議的核心問題。
一、投資條約中的“利益拒絕”條款概述
從國際投資法歷史的角度來看,“利益拒絕”條款的主要目的是排除第三方獲得條約的利益而不承擔條約義務,尤其是直接針對所謂的“敵國公司”。而且,最初“利益拒絕”條款主要用于拒絕外交保護,其后才被逐漸引入專門的投資保護條約。
在國際投資法的歷史上,最早引入“利益拒絕”條款的似乎是美國1945年之后簽訂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FCN條約)。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46年美國與我國(中華民國政府)簽訂的FCN條約。其第26條第5款規定:“締約此方保留權利,得拒絕以本約所給予之權利及優例,給予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所設立或組織而以多數股份所有權或以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為任何第三國或數國之國民、法人或團體所有,或所管理之任何法人或團體。”*《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簽署于1946年11月4日,1948年11月30日生效,參見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6127.htm。與此類似,美國與泰國1966年簽訂的友好與經濟關系條約也規定,對于直接或間接由第三國控制或擁有的公司,締約國有權拒絕給予條約中的利益,但是這種拒絕不得包括承認其法律地位以及尊重其向法院或行政法庭尋求救濟的權利。對于這種FCN條約中的“利益拒絕”條款,當時的學者已經意識到,該條款可以作為防止“免費搭車者”的安全閥,對于締約國來說具有“潛在的”保護性,[2]但是該條款并不影響該公司的國籍,也不影響該公司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
之后,“利益拒絕”條款被引入了雙邊投資協定(BIT)。在較早的一些BIT中,“利益拒絕”條款被放在“定義”條款中。比如1993年美國-吉爾吉斯BIT第1條中關于投資的定義的第二段實際上就是“利益拒絕”條款的內容。但是,現代絕大多數包含該條款的BIT都將其作為一個獨立的條款。比如美國1994年BIT范本和2004年BIT范本都是如此。
1994年之后美國在自由貿易協定中的投資條款中也納入了利益拒絕條款,而且其規定比1994年BIT范本更加詳細和明確,這種規定后來也被2004年BIT范本所采納。在2004年BIT范本中,在三種情況下締約一方可以拒絕給予利益:(1)締約另一方的投資者被第三國投資者所擁有或控制,而第三國與締約一方沒有外交關系;或者(2)締約一方正對該第三國進行經濟制裁,而給予條約下的利益將會違反這些制裁措施;或者(3)締約另一方的投資者被第三國或締約一方投資者所控制,而在締約另一方境內沒有實質性商業活動。
當然,“利益拒絕”條款不僅僅只存在于美國簽訂的雙邊貿易協定或投資條約中,現在許多國家的雙邊投資條約或自由貿易條約中的投資章節都存在著類似條款。比如,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的相關規定幾乎與美國2004年BIT范本的規定完全一致,而墨西哥、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家簽訂的BIT或自由貿易協定也都有類似“利益拒絕”條款。我國的BIT中以前從未出現過該條款,但是2008年與墨西哥簽訂的BIT卻出現了該條款。該BIT第三十一條“拒絕授予利益”規定:“締約雙方可以共同磋商決定拒絕將本協定之利益授予締約另一方之企業及其投資,如果該企業系由非締約方之自然人或企業擁有或控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墨西哥合眾國政府關于促進和相互保護投資的協定》,來自于中國投資指南網,http://www.fdi.gov.cn/pub/FDI/zcfg/law_ch_info.jsp?docid=96534。另外,中國與東盟之間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政府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投資協議》第十五條“利益的拒絕”也規定:
經事先通知及磋商,一方可拒絕將本協議的利益給予:
(一)另一方投資者,如果該投資是由非締約方的人擁有或控制的法人進行的,且該法人在另一方境內未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或者
(二)另一方投資者,如果該投資是由拒絕給予利益一方的人擁有或控制的法人進行的。
除了雙邊條約之外,“利益拒絕”條款也被引入了一些區域性條約或多邊條約。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第11章第1113條就規定了該條款,而其具體內容與美國2004年BIT的規定基本一致。另外,NAFTA第1113條還特別規定,拒絕給予利益必須事先通知該投資者的母國。
從前述的例子來看,“利益拒絕”條款的內容有兩種不同情況:一種是除了針對那些在締約國沒有實質性經濟活動“郵箱公司”之外,還用于針對與締約國不具有正常經濟關系或外交關系的投資者控制的公司,如ECT、美國以及加拿大的BIT、FTA等;第二種是只針對在締約國沒有實質性經濟活動“郵箱公司”,如中墨BIT以及中國-東盟投資協議。鑒于目前在投資仲裁中爭議較大的是關于該條款對沒有實質性經濟活動“郵箱公司”的適用問題。本文接下來的主要內容也只針對這一問題。
二、“利益拒絕”條款的適用條件
針對在締約國沒有實質性經濟活動“郵箱公司”的“利益拒絕”條款,主要由兩個條件構成:一是沒有“真實的經濟活動”或“實質性商業活動”;二是“由第三國國民控制”。然而,對于這兩個要素,迄今為止筆者沒有發現任何一個國際投資協定對其下了定義,因此,國際仲裁庭在適用這一條款的時候無疑會遇到困難。
(一)實質性商業活動
所謂“實質性”或者“真實的”商業活動,筆者認為,應當是指那些依據法律要求最低的、僅僅維持該公司存在的商業行為之外的商業行為。比如,納稅、股東召開股東會等,均不能視為“實質性”商業行為,因為這些行為一般都是一個公司存在的法律最低要求。當然這里并沒有一個清晰的標準來判斷“實質性”和“非實質性”。
在BP et al.訴阿根廷案中,仲裁庭肯定了BP在美國有實質性商業活動,但是未作任何分析。當然,由于BP在美國有37000名雇員,在50個州都有辦公室,因此仲裁庭給出這樣的結論是很簡單的。而在涉及到ECT第17條的Plama訴保加利亞案中,原告自己承認,在其注冊成立地塞浦路斯,沒有重要的商業活動,而仲裁庭也相應地裁決原告在塞浦路斯“明顯”沒有“實質性”經濟活動。同樣涉及ECT第17條的Petrobart訴吉爾吉斯案中,仲裁庭同樣簡單地認定原告有“實質性”經濟活動,而沒有深入分析。
從前面的案例可以看出,至少目前來看,所謂“實質性”或者“真實的”商業活動,并沒有統一的判斷標準。很多案件中仲裁員都只是簡單而籠統地認定,對于其后案件的借鑒作用不大。因此,這一問題恐怕現在還只能依據個案來進行判斷。
(二)“由第三國國民控制”
“利益拒絕”條款的另一條件是,這一在其成立地沒有“實質性”商業活動的公司(實體)是由與該公司(實體)不同國籍的人控制或擁有的。
但是,這一要素在不同的國際投資協定中用詞有所不同,有的使用“公民”(citizens)、“國民”(nationals),也有的使用“投資者”(investors)。而且,許多投資協定都沒有明確指出協定中投資者的控制者或擁有者必須是自然人。這樣就很可能會導致這一問題:一家公司很可能是多層控制的,而多層的控制者來自不同的國家,那么,是否對每一層控制者都可以使用“利益拒絕”條款,還是說只能針對最終的控制者適用?
另外,在有些條約中使用的是“第三國”(a third country)國民,而有些條約使用的是“非締約方”(Non-Party)國民。這種區別,現在還沒有明確資料表明其是否有什么不同之處或者完全相同。當然,有一些條約的表述更加明確,比如美國2004年BIT范本使用的用詞是“締約另一方的投資者被第三國或締約一方投資者所控制”,這一表述顯然涵蓋的范圍更大。
當然,從總體來講,“利益拒絕”條款的這一要素的解釋,也要根據每個條約的具體用詞,結合上下文,并根據條約的宗旨和目的,進行個案解釋。
(三)“利益拒絕”條款適用條件的精確化問題
從前述分析來看,“利益拒絕”條款的適用條件顯然是比較簡單、模糊的;從BP et al.訴阿根廷案等涉及到該條款的案例來看,仲裁庭從該條款本身不能獲得更加詳細的適用引導,因而只能進行比較簡單的分析。因此,有學者提出,“利益拒絕”條款必須規定更加具體的適用標準。
與雙邊投資條約相比,在避免雙重征稅條約中,對于如何防止濫用稅收條約進行避稅則有著更加具體的規定,有利于更加嚴格的控制“挑選條約”(treaty shopping)的問題。總的來說,避免雙重征稅條約中對人的適用范圍的更加嚴格的規定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除了少數國家之間的雙邊投資條約以外,*比如1981年菲律賓-英國雙邊投資條約就規定受保護公司不僅應當是在締約國依據締約國的法律建立,而且還必須在締約國境內有“有效管理機構”并“實際從事商業活動”;又如1994年羅馬尼亞-菲律賓雙邊投資協定第1條(5)(a)規定,合格的羅馬尼亞公司是指“依據羅馬尼亞法律建立的位于羅馬尼亞境內,同時在羅馬尼亞境內有真正經濟活動的法律實體”。大多數投資條約中受保護的法人“投資者”一般只以其注冊成立地作為判斷標準。與之相比,國際稅法則采用“居民”這一概念來確定條約的適用對象,而國籍并不是條約適用的一個重要連結點。而作為法人的“居民”往往要求以實際控制和管理中心或者總機構所在地作為判斷標準,[3](P461)這種判斷標準本身就比注冊成立地更加強調該法人與締約國之間的實質性經濟聯系。
第二,在國際稅法中還常常使用“導管公司”(conduit company)和“受益所有人”(beneficial owner)術語。如果一家公司被認為僅具有利益輸送功能而構成“導管公司”,稅務機關可以直接排除稅收條約對其適用。而“受益所有人”術語的使用,也限制了稅收條約的適用主體范圍:針對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方面的濫用行為,“受益所有人”術語可以使稅務機關比較專斷地拒絕將稅收條約的利益給予不屬于該條約適用范圍內的或者企圖利用“挑選條約”避稅的當事人。同時,在許多稅收條約中(以OECD雙重稅收條約范本為例),在注釋中還規定了許多具體、明確的方法來阻止稅收協定的濫用,如透視法、排除法、征稅法、渠道法等等。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有學者提出,雙邊投資條約也許應向雙重征稅條約學習,采用“居民”、“導管公
司”以及“受益所有人”等術語或理論,以更精確地界定受保護的“投資者”的范圍。[4]
但是筆者認為,雙重征稅條約與雙邊投資條約的經濟原理可能未必相同,因此,將雙重征稅條約中某些具體的適用條件照抄過來并不具有可行性。而且,即便從這兩類條約的宗旨和目的來看,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雙重征稅條約的宗旨,以OECD范本為例,在2003年以前雖然從未正面直接肯定其宗旨之一在于反避稅,但也指出稅收協定不應幫助逃稅或避稅;而從2003年開始,OECD范本在注釋中明確提出“防止逃避稅也是協定的宗旨”。[5]而與此相反,雙邊投資條約則以促進與保護外國投資,發展締約國經濟為宗旨和目的,而避免條約濫用和“免費搭車”則從來都不是雙邊投資條約的宗旨之一。
當然,借鑒雙重征稅條約中某些利益限制的措施,無疑對投資條約中“利益拒絕”條款適用條件的精確化是有幫助的。
三、“利益拒絕”條款適用中的具體問題
(一)管轄權問題還是實體問題
Waste Management II v. Mexico案是NAFTA第1113條相關的案例。仲裁庭在分析原告的“投資者”地位時,提到了第1113條的“利益拒絕”條款。仲裁庭認為該條款的目的在于,如果外國人控制了一個NAFTA的“投資者”而在該國又沒有實質經濟活動,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經過事先通知和協商,NAFTA提供的保護可以被撤回。按照仲裁庭的觀點,該條款是投資者提起仲裁的一項前提條件。在BP et al.訴阿根廷案中,仲裁庭也是將“利益拒絕”條款作為仲裁庭對該案是否有管轄權的先決問題來看待的,在駁回了被告的初步反對意見后裁定仲裁庭有管轄權。在Generation Ukraine訴烏克蘭案中,也涉及到了這一條款的適用。該案所涉的美國-烏克蘭BIT與美國第一條第二款與美國1994BIT范本的“利益拒絕”條款基本相同。仲裁庭也是將這一問題作為先決問題來加以處理的。在Tokios Tokeles訴烏克蘭案中,烏克蘭提出原告不是真正的投資者,在其成立地立陶宛沒有實質性商業活動,控制者是烏克蘭國民,因此與立陶宛沒有“真實聯系”,進而主張仲裁庭無管轄權。然而,仲裁庭卻認為,立烏BIT沒有“利益拒絕”條款,這是締約雙方“故意的選擇”;而且,仲裁庭進一步指出:“仲裁庭不能對BITs的范圍施加條文中沒有的限制。……被限定了管轄權范圍的仲裁庭,不能超越界限行使管轄權。但是仲裁庭同樣應當行使,而且有義務行使其被賦予的管轄權”。*Tokios Tokelès,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pril 29, 2004), ICSID Case No.ARB/02/18, para. 36, available at http://icsid.worldbank.org/ICSID/FrontServlet?requestType=CasesRH&actionVal=showDoc&docId=DC639_En&caseId=C220.
顯然,“利益拒絕”條款的目的是排除那些與締約國沒有真實經濟聯系的投資者從投資條約獲得締約另一國的保護。從前述幾個案件仲裁庭的觀點來看,這一條款的適用是案件的先決問題,與案件的管轄權相關。
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與條約本身的用語有關。前述幾個涉及到BIT的案例,由于BIT的內容相對比較簡單,因此通常的規定——比如美國1994年BIT范本——都是:“締約各方保留拒絕給予另一締約方的公司本條約下的利益的權利,……”自然,這些利益,包括爭端解決程序的利益。而NAFTA第1113條則規定締約方可以拒絕給予“本章”(即第11章)的利益,而這顯然也包括了第11章B節——投資者與國家爭端解決程序——的利益。
與此相反,在其他的某些條約中,“利益拒絕”條款似乎與管轄權問題無關,其典型就是ECT第17條規定。該條規定:“締約方有權拒絕將本部分(指ECT第三部分“促進與保護投資”)利益授予:……”而在ECT的結構下,投資者-東道國爭議解決機制規定在ECT的第五部分“爭議解決”。因此,在Plama訴保加利亞案中,當被告提出依據ECT第17條(1),仲裁庭沒有管轄權時,仲裁庭就指出,“ECT第17條(1)不能用來拒絕本條約中受保護的投資者的所有利益,而只是局限在拒絕ECT第三部分中的利益”,而第26條投資者-東道國爭議解決機制規定在第五部分,根據條文本身的涵義以及條約目的和宗旨加以解釋,東道國不能運用第17條(1)來對抗仲裁庭的管轄權。應該說,Plama案仲裁庭的解釋是符合邏輯的。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認為這需要結合適用第26條投資者-國家爭議解決機制的條件來分析。根據第26條,適用這一爭議解決機制的條件之一是,締約國一方被宣稱違反了ECT第三部分的義務。那么是否意味著,如果締約方根據第17條(1)拒絕給予ECT第三部分的利益,那么締約方就根本不違反ECT第三部分的義務,進而該爭議就不滿足第26條的條件,因此仲裁庭也就無管轄權呢?由于仲裁庭的裁決并不具有判例法的作用,因此,未來的仲裁庭很可能也會對Plama案的裁決提出質疑。
總之,“利益拒絕”條款是否具有排除仲裁庭管轄權的作用,應當有具體的條約的用語。目前大多數投資條約的該條款具有排除仲裁庭管轄權。但是少數,如ECT,由于其條文的規定,很可能東道國能夠拒絕的利益僅限于實體利益。但是,無論是上述哪種情況,仲裁庭都有權就自己是否具有管轄權自行作出裁定。
(二)“利益拒絕”條款的具體實施方式
東道國如何具體實施該條款下拒絕給予利益的權利,也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在Plama訴保加利亞案中,保加利亞認為該權利是自動實施的,不需要東道國另行作出任何積極的行為。但是,Plama案的仲裁庭則反對這一觀點。仲裁庭認為,“拒絕利益”權利的存在和實施該權利是兩碼事。如果東道國要實現“利益拒絕”條款的效果,必須采取實施該權利的行動。仲裁庭指出:“在ECT第17條(1)的規定下,締約方有權拒絕給予一定范圍內投資者以第三部分中的利益;但它需要去實施這一權利;它也可以永遠不實施。”
應該說,從以《能源憲章條約》第17條(1)為代表的“利益拒絕”條款的用語來看,我們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締約國如果要拒絕給予利益,必須采取積極行動。實際上,從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在FCN條約中引入該條款的目的來看,Plama仲裁庭的這一結論也是正確的。當時,相關學者就已經作出了論述:“需要注意的是,這項保留并非為公司規定一項享受條約權利的自動的前提條件;相反,它是一個潛在的保護性條款,當締約方希望啟用它時可以使用。”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究竟哪些具體的行動才構成締約國具體的實施該“利益拒絕”權利的行為?在Plama案中,仲裁庭認為:“這種實施必須具有公開性或者采取其他通知的形式,以便使其能夠合理地被投資者及其顧問所獲知。為此,在一個締約國官方公報中的聲明即可,或者締約國的投資法或其他法律中的法定條文,甚至或者與特定某一個或某一類投資者之間的互換信函也可……ECT第17條(1)自己最多只能算是半個通知,如果東道國沒有進一步實施其進一步合理的通知,其條款沒有告訴投資者多少東西;為了具體實現其目的,必須采取更多措施。”
根據Plama案仲裁庭的這一裁決,有學者提出,只要東道國在其國內立法中制定了一個概括性的利益拒絕條款就可被視為實施了條約中的利益拒絕權利。[6]但另有學者認為,利益的拒絕只能在個案分析的基礎上對特定投資者實施;國內立法中的概括性利益拒絕條款,并不能構成對特定投資者的拒絕利益的具體實施行為。[7]
筆者認為,東道國政府對于某一個或某一類特定的投資者通過非規范性法律文件甚至交換信函等方式進行的具體的拒絕,肯定可以構成“利益拒絕”權利的實施。然而,對于國內法中的“利益拒絕”條文,則要具體分析。如果在國內法中的“利益拒絕”條文是概括性的,筆者認為不能構成東道國權利的實施。首先,從“利益拒絕”的條件來看,“實質性商業活動”和“第三國國民控制”(尤其是前者)的判斷都是建立在個案分析的基礎上;第二,在采用并入制的國家,國際條約中的條款在國內同樣具有法律效力,在國內制定一個概括性的“利益拒絕”條款并無必要,即使制定了其效力與條約中的條款也沒有太大區別。與此相反,如果在國內法中能夠制定非常明確具體拒絕給予利益的標準,該條文不論是屬于法律、法規還是規章,也可以成為拒絕利益權利的實施方式。當然,要對“實質性商業活動”確定一個明確具體的標準肯定是非常困難的。總之,筆者認為,判斷東道國是否具體實施了“利益拒絕”的權利,其關鍵不在于其行為的外在表現方式,而在于其行為是否明確、無任何彈性地表示除了其拒絕利益的意愿。
另外,“利益拒絕”權利的實施,某些投資條約中也有更為具體的表述。比如中國-東盟投資協定就規定,拒絕給予該協定下的利益的前提條件是“經事先通知及磋商”。根據這一規定,筆者認為,該協定下的“利益拒絕”條款不能經由在國內立法中加入相關條文來實施,而必須針對特定投資者進行具體通知并磋商后才能實施。與此類似的還有NAFTA1113條第2款。根據該款,東道國基于投資者在其成立的締約國沒有實質性商業活動而拒絕給予利益,必須事先通知投資者母國并與該國磋商(投資者母國也有義務提供相關信息)。尤其需要將該款與1113條第1款對比:第1款規定的是針對那些實際上由與東道國沒有外交關系或處于經濟制裁中的國家的投資者所控制公司,東道國拒絕給予利益的情況,而在這一款中,就沒有事先通知和磋商的前提條件。對比這兩款,結合條約上下文進行分析,可以明顯看出,NAFTA第1113條第2款是締約國有意為之,根據該款,基于投資者沒有實質性商業活動的利益拒絕,必須針對特定投資者,建立在個案分析的基礎上,予以實施,國內法中的條款不能構成“利益拒絕”權利的實施。
(三)“利益拒絕”條款適用的溯及力問題
如果東道國行使了“利益拒絕”的權利,那么這種“利益拒絕”的效果是否只對明確表示拒絕之后的投資利益有效?還是具有溯及力,即可以針對該投資者符合被“利益拒絕”的條件以來的一切利益?這一問題,在所有的條約中都沒有明確的說明,因此也成為頗有爭議的問題。
在ECT的Plama案中,仲裁庭首先承認了ECT對這一問題并無明確規定,進而基于條約的宗旨和目的解釋“利益拒絕”行為不具有溯及力。仲裁庭認為,ECT的宗旨和目的提到了“促進能源領域的長期合作”;如果東道國的“利益拒絕”權利實施的效果具有溯及力,那么投資者就不能對其“長期”投資進行規劃,這違反了投資者的“合理期待”,進而也違反了條約的宗旨和目的,不利于能源領域的長期合作。
但是,仲裁庭的這一分析遭到了很多學者的質疑。有學者認為,Plama案的仲裁庭并沒有全面的理解ECT的宗旨和目的,ECT第二條(條約的目的)強調了與《歐洲能源憲章》的目的和宗旨的一致,因此ECT的宗旨和目的應該充分考慮《歐洲能源憲章》以及相關一系列其他法律文件的目的和宗旨;而且,如果賦予東道國“利益拒絕”權利實施效果以溯及力,也會鼓勵投資者在所有權、控制權、國籍或公民身份等問題上保持誠實,進而有利于“能源領域的長期合作”。[8]還有學者認為,在東道國作為能源投資合同一方當事人,或者作為合同的擔保人的情況下,我們當然可以假定東道國知道投資者的實際控制者到底是誰,這時要求東道國及時表態是否行使“利益拒絕條款”的權利具有合理性;但實際上,能源投資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政府不可能對所有的投資進行一一審查,甚至政府有可能根本不知道一些小規模的投資的存在。這樣政府可能只有在爭議發生之時才有機會知道投資者的實際控制人并行使第17條(1)的拒絕利益的權利,然而按照Plama案仲裁庭的觀點,那時為時已晚。另外,即使東道國存在能源投資審查,并且會審查投資者的實際控制人,但是眾所周知,公司的股東可能隨時發生變化,股份有限公司尤其如此,那么東道國哪里有精力去隨時審查投資者的股東變化情況呢?況且ECT也沒有對投資者施加任何要求其披露實際控制人的義務。因此這種觀點認為,Plama仲裁庭的結論實際上給締約國強加了額外的義務,使得“利益拒絕條款”幾乎沒有適用的空間,打破了投資者與東道國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并不符合締約國的真實意圖。[9]還有學者指出,“利益拒絕”條款本身存在,足以排除投資者有所謂“合理期待”,因此Plama案仲裁庭的解釋并不能讓人信服。[10]
筆者認為,對于“利益拒絕”條款的實施的效果是否具有溯及力這一問題,由于各條約中均無明確說明,相關案例也比較匱乏,因此尚不能得出確定的普遍性結論。未來可能也只能在個案的基礎上,通過對特定條約上下文的分析并結合條約的宗旨和目的加以解釋。至于Plama案中,仲裁庭的論述也僅是其一家之言,并不具有先例的作用。相反,筆者認為,許多批評Plama案裁決的觀點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值得未來仲裁員或立法者參考。尤其是,由于許多國家并不實行投資審查制,對于一項境內投資的實際控制人不可能了如指掌,如果按照Plama案的解釋,東道國在發生糾紛時再行使其利益拒絕權可能已經為時已晚,這可能使東道國不得不強化其投資審查,這一結果與西方國家倡導的投資自由化也是相抵觸的。因此,筆者認為,如果投資條約中對“利益拒絕”的溯及力未作明確規定,仲裁庭將這種“利益拒絕”解釋為具有溯及力可能更加符合“善意”解釋的原則,——雖然我們仍然要考慮每一條約的宗旨和目的。
四、在中國的投資條約中納入“利益拒絕”條款的問題
從以上分析可見,“利益拒絕”條款對于防止某些國家的投資者“免費搭車”具有一定意義。
如前所述,中國只有極少數投資條約納入了“利益拒絕”條款,如中墨BIT和中國-東盟投資協議。
從“利益拒絕”條款的必要性來看,一方面,外國投資者到中國來投資,一般都是看重中國良好的投資環境,而并非是為了獲得中國與第三國之間簽訂的投資條約中的利益,而且從中國對待外資的態度來看,我國目前對外資在經營管理階段基本上已經實行國民待遇,而在投資準入階段即使在投資條約中也并未放開,因此外國投資者直接到我國投資和通過與中國有投資協定的國家到我國投資在實體待遇上基本沒有差別;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由于投資條約將締約國的義務上升到國際義務的層面,而且還提供了投資者-東道國仲裁這一強有力的保護機制,因此,也不排除某些與中國并無投資條約國家的投資者可能利用在第三國的“郵箱公司”向我國投資,以獲得我國與第三國之間投資條約中投資者-東道國仲裁機制的保護。因此,在投資條約中納入“利益拒絕”條款仍有一定意義。
從“利益拒絕”條款的具體規定來看,中墨BIT和中國-東盟投資協議都要求“利益拒絕”條款的適用以雙方磋商為前提條件,這極大地減少了拒絕利益的隨意性,也體現出“利益拒絕”條款僅是投資者保護的例外,這種做法應當堅持。但是中墨BIT和中國-東盟投資協議中的“利益拒絕”條款仍有一定的模糊性,尤其是在適用的條件“實質性商業活動”和“利益拒絕”條款適用的溯及力上,都沒有任何說明。這給國際仲裁庭解釋該條款留下了太大的空間,也不利于締約雙方的磋商。因此,如果未來中國的投資條約納入“利益拒絕”條款,宜在上述兩個問題上進一步細化。
[1] Loukas A. Mistelis & Crina Mihaela Baltag, Denial of Benefits and Article 17 of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Penn State Law Review, Vol. 113:4, p.1302.
[2] Herman Walker Jr., Provisions on Companies in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Treaties, 50 AM. J. INT'L L. 373, 388 (1956).
[3] 余勁松,吳志攀.國際經濟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 Richard Happ & Ulrich Klemm, Considerations of denial of benefit clauses and other mechanisms that limit the scope of BIT for investor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ationality of Investors under Investment Protection Treaties: A Preliminary Report, by ILA German Branch Working Group, p.57, available at http://telc.jura.uni-halle.de/sites/default/files/BeitraegeTWR/Heft%20106.pdf.
[5] 陳延忠.國內反避稅法與稅收協定相容性問題分析[J].國際經濟法學刊,2007,(2):285.
[6] H. Essig, Balancing Investors’ Interests and State Sovereignty: The ICSID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Plama Consortium Ltd. v. Republic of Bulgaria, 5 Oil, Gas & Energy L. Intelligence, April 2007, 10.
[7] Stephen Jagusch & Anthony Sinclair, The Limits of Protection for Investments and Investors Under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edited by Clarisse Ribeiro, Juris Publishing Inc., June 2006, p.73.
[8] James Chalker, Making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Too Investor Friendly:PlamaConsortiumLimitedv.TheRepublicofBulgaria, (2006) 3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TDM) 1, pp.16-19.
[9] Stephen Jagusch & Anthony Sinclair, The Limits of Protection for Investments and Investors Under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edited by Clarisse Ribeiro, Juris Publishing Inc., June 2006, p.101.
[10] Laurence Shore, The Jurisdiction Problem in Energy Charter Treaty Claims, IALR 2007, 58(64).
AStudyontheDenialofBenefitsClauseinInternationalInvestmentTreaties
Ma Xun
(Law School,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The purpose of the denial of benefits claus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y is to preclude the abusive use of the treaty by a mailbox company controlled by a third party's investor. This clause has been a quite controversial on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ases in recent years. Its applicable conditions are ambiguous. And there is also a controversy over the jurisdiction or merits, the exercise of the clause and its retrospective effect. These controversies, on the one hand, need to be analyzed case by case due to the different texts of different treaties; on the other hand, some arbitration tribunals cannot give accurate interpretations because of the inadequate quantity of relevant cases. Therefore, the study on this clause is helpful to the future legislation on relevant treaties and to the arbitrators'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i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y; denial of benefits clause; mailbox company; ECT
D996.1
A
1672-335X(2013)01-0099-06
責任編輯:周延云
2012-03-06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能源憲章條約》與國際投資法的發展——兼論我國的應對策略”(09YJC820130)的研究成果之一
馬迅(1977- ),男,重慶人,重慶工商大學法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國際經濟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