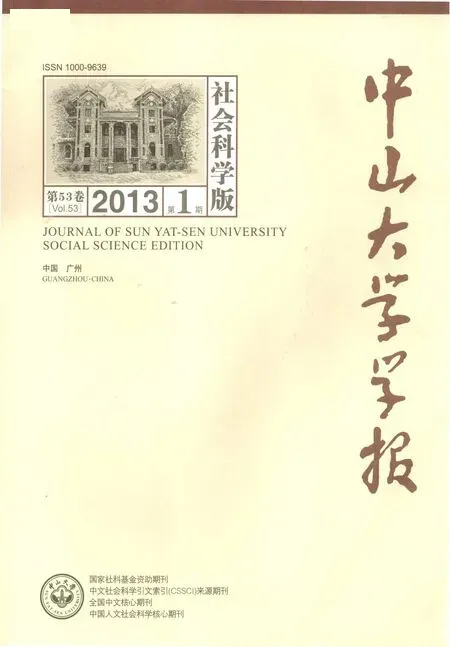論王安憶小說的“四不”敘事追求*
顏湘茹
王安憶是當代文壇的重要作家,其小說創作既有鮮明的個人特色,又可被視作新時期文學的見證。研究者認為她能“以最極端真實的材料去描寫最極端虛無的東西”①王德威:《虛構與紀實——王安憶的〈天香〉》,《揚子江評論》2011年第2期。,走上了“智、史、詩”平衡的新的小說敘事美學探索之路②姚娜:《王安憶小說敘事研究》,山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其小說是女性主義浸潤和本土文化的整合③彭珺潔:《王安憶小說的女性意識及敘事策略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她的敘事申明使研究者紛紛關注其敘事追求:有的認為王安憶繼承了中國傳統“戲劇式”敘事模式,形成形散神不散的“散文式”敘事結構④李舒悅:《王安憶小說的敘事特征》,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有的認為其經歷了紀實—虛構—紀實與虛構三階段⑤王星虎:《紀實與虛構的二元關系轉換——王安憶的小說敘事策略》,貴州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還有的認為王安憶敘事觀念貫穿作品,相對固定又自由的敘事視角、流動又富邏輯的敘事結構、從具體走向抽象的敘事語言、日常和詩意的敘事意象,構成她不要獨特性的“獨特性”⑥曹愛華:《試論王安憶小說的敘事智慧》,江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上述研究從不同角度論述了王安憶的小說敘事,但未系統論述她的敘事“四不”追求及其特殊意義。“四不”即王安憶在1988年用4個否定句描述的小說寫作理想:1.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2.不要材料太多;3.不要語言的風格化;4.不要獨特性⑦王安憶:《小說的物質部分》,《王安憶自選集之四·漂泊的語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330—332頁。(為行文方便簡稱為“四不”)。1988年至今,“四不”與她的創作道路相伴隨。而其后的理論闡釋是完善了自己的觀念還是更改了某些關鍵詞句,小說實踐是否實現了其“四不”理想,它對于小說敘事,尤其是長篇小說敘事是否具有某些啟迪,將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一、王安憶的小說敘事理論
1988年成為專業作家后,王安憶寫下系列文章,闡述小說創作理念,主要集中在作家自我與小說創造者、敘述的重要性、邏輯力量與小說語言四個方面。
(一)從自我到小說創造者
王安憶認為作家自我“是第一重要的,是創作的第一人物。這人物總是改頭換面登場,萬變不離其宗”①王安憶:《女作家的自我》,《王安憶自選集之四·漂泊的語言》,第416,420頁。。但在真實的自我與提高的自我之間應有理性距離:“如不與自身以外廣闊的世界及人生聯系起來,對自我的判斷也會墮入謬誤。在一方面是對自我真實的體察與體驗,在另一方面又對身外世界與人性作廣博了解與研究,便可達成真實的自我與提高的自我間審美距離,理性和批判距離。在自我面前,要有另一個自我的觀照。觀照的自我站得越高,本體的自我便更真實清晰。而觀照的自我的提高,有待于理性活動的步驟。”②王安憶:《女作家的自我》,《王安憶自選集之四·漂泊的語言》,第416,420頁。
王安憶所說“本體的自我”指的是作家,即真實作者,而“觀照的自我”實指隱含作者,常被稱為“作者的第二自我”③[以色列]里蒙·凱南著,姚錦清等譯:《敘事虛構作品》,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第157,169頁。:“隱含的作者和敘述者不同,他什么也不能告訴我們。他,或更確切地說,它,沒有聲音,沒有直接進行交流的工具。它通過作品的整體設計,借助所有的聲音,依靠它為了讓我們理解而選用的一切手段,無聲地指導著我們。”④[以色列]里蒙·凱南著,姚錦清等譯:《敘事虛構作品》,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第576頁。當王安憶提出真實自我與觀照自我可通過對世界人生進行深思并拉開批判的距離時,她為自己敘事作品中的敘述者,構建出理性廣博的隱含作者。
1997年她在《心靈世界》里說,小說這個心靈世界和現實世界保持距離,獨立存在,它的創造者往往由邊緣人擔任,他們很難立足社會中心位置,應具有敏銳的感受能力,從人群中脫離出來。創作對本體的要求嚴格,包括理性和心理承受能力⑤王安憶:《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35—357,371,261頁。。而她認為好的情感應該經歷理性磨煉,鍛造出哲學果實⑥王安憶:《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35—357,371,261頁。。由此可見,經過近10年的探索,她對小說的創造者有了新看法,但貫穿其中的關鍵始終是獨立理性。
(二)邏輯是小說的物質部分
1.小說創作是物質勞動、技術活。為了創作,王安憶開始尋找“形式”并求助于“結構”,將之稱為“小說的物質部分”。1988年在《我看長篇小說》中,王安憶說中國人寫小說是“詩言志”“文載道”,是個人情感宣泄需要,是社會責任感使然,屬于有話要說有感而發。但藝術應該是為了創造,由它創造出的東西徹底獨立;承認藝術是創造就該承認創造含有科學意義的勞動,這勞動帶有機械性質具有無盡的推動力與構造力。現今文壇對小說的結構與語言的關注,是因為寫作已經職業化而失去了有感而發的環境,必須重新創造。因此小說創作也是一種物質勞動⑦王安憶:《我看長篇小說》,《王安憶自選集之四·漂泊的語言》,第366—370頁。。
1988年在《小說的物質部分》中,王安憶說:“也曾將生活與小說關系中思想的部分與物質的部分視為一體,將小說視為帶宿命意味的天然,將小說的完成視作一種感應的實現。當我比較順利地寫作了若干短篇、中篇,而終于寫作長篇不甚順利的時候,我幾乎是被迫地要尋得一種具有實體性、規范性的手段。我發現,小說是有科學性、機械、物質的部分。”⑧王安憶:《小說的物質部分》,《王安憶自選集之四·漂泊的語言》,第339頁。
1997年她聲明:“現代小說非常具有操作性,是一個科學性的過程,它把現實整理歸納,抽象出來,然后找到最具有表現力的情節再組成一個世界。”⑨王安憶:《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35—357,371,261頁。2007年她仍然強調:“寫作是特別技術性的問題。我特別像工匠,坐到書桌前開始寫作時,遇到的都是技術性問題。”⑩王安憶:《虛構與非虛構》,《天涯》2007年第5期。可見,從1988年至今,她都始終堅持小說創作的技術性。
2.小說物質部分即邏輯性情節。在1988年《故事不是什么》里,她認為閱歷艱深經驗豐富并非惟一擁有故事的途徑,經驗性傳說性的故事與小說構成性故事不同,關鍵在于情節不等于故事。情節往往提供“扣子”,承上啟下,但上下事件整體并無因果關系,缺乏強有力的推進或反推進。能促進事件上下因果推進的是邏輯,它才是構成的力量。邏輯相對獨立于思想內容,這可能就是小說構成的物質性存在①王安憶:《故事不是什么》,《王安憶自選集之四·漂泊的語言》,第345—355,356—366頁。。同年在《故事是什么》中,王安憶再次強調邏輯力量是小說構成意義上的“故事”區別于經驗性傳說性意義上的故事的關鍵②王安憶:《故事不是什么》 ,《王安憶自選集之 四·漂泊的語言》 ,第345—355,356—366頁。。
當王安憶突出小說的邏輯力量時,她其實強調的是“一種成熟的,成型的因而具有某種邏輯外觀的實實在在的思想”③陳思和、王安憶、郜元寶、張新穎、嚴鋒:《當前文學創作中的“輕”與“重”文學對話錄》,《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5期。。這種思想是她對人內心的追尋,她斷定在現代化都市無故事,因為“人們再不可能經歷一個過程,過程被分化瓦解了”④王安憶:《城市無故事》,《王安憶自選集之四·漂泊的語言》,第430頁。。只有在內心才保留了一個過程,它完整,能為人所了解,講故事的人只能走向他自己。
1997年,王安憶認為生活里的情節是“經驗性情節”,比較感性,有最直接的人生感受,甚至超過人的想像力,但缺乏有力的動機把事情推進下去,只有依靠“邏輯性情節”;而這來自后天的制作,經驗可供使用但必須嚴格整理,使它具有邏輯推理性⑤參見王安憶:《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第295—298,15頁。。
2007年,她在討論中談到:我們想象故事,去虛構,絕不是憑空而起,必須找到虛構的秩序和邏輯,這個邏輯一定是可能實現的⑥參見王安憶:《虛構與非虛構》,《天涯》2007年第5期。。可見,從1988年起,她就逐步將貫穿在敘事作品中的物質推進力歸納為邏輯,而這邏輯指向她所認定的心靈世界。
(三)敘述的重要性
1988年在《我的小說觀》中,王安憶認為小說的物質部分具體到寫作過程中,表現為敘述方式⑦王安憶:《我的小說觀》,《王安憶自選集之四·漂泊的語言》,第331頁。。在《故事和講故事》里,她說寫作開頭難是在于“尋找故事本來的模式,尋找故事與生俱來的講敘方式”。她發表小說是敘述藝術的見解,說:“現在和將來我都決定走敘述的道路了。”⑧王安憶:《故事與講故事》,《王安憶自選集之四·漂泊的語言》,第337頁。
純文學敘事指:用特定的言語方式敘述來表達一個故事。敘事學理論認為:“敘述為一個故事添加了描寫,人物的內心看法,以及時間的重新安排(時間重組),而故事不然的話是可以被戲劇式地呈現的。”⑨[美]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58頁。戲劇式呈現即場面與敘述(或稱概述),是兩種對立的講故事的方式。二者的最大區別在于,敘述總是提醒人們注意敘述者的在場。王安憶明確表示,不要以前那種寫人物對話時“她說……”、“他說……”照錄不誤的做法,盡量避免戲劇式呈現場面的小說寫法,轉而注重敘述。
1997年在《心靈世界》中,她仍然強調小說帶有很強的心靈特征,但首先“是以講故事為形式的”⑩參見王安憶:《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第295—298,15頁。。2003年在《好的故事本身就是好的形式》中,她提到:“如果說有一點成功的話,那便是終于接近了《小鮑莊》故事本來的形成構造和講敘方式。”?《好的故事本身就是好的形式——王安憶訪談錄》,《小說評論》2003年第3期。2010年她再次強調:“小說是時間的藝術,因為它是敘述性質的,敘述必須一句句話進行,所以是在一個時間流程里,我們要遵守我們的限制,將不可敘述的轉換為可敘述。”?王安憶:《小說的創作》,《東吳學術》2010年第2期。2012年她在講座中談到,小說強項就是描寫感情、心理、性格等主觀性對象,這才是小說的能耐,小說要做的就是敘述?王安憶:《小說創作——在常熟理工學院“東吳講堂”上的講演》,《東吳學術》2012年第2期。。可以說,她對敘述的重視一以貫之。
(四)抽象化小說語言
王安憶認為由敘述完成的小說,語言是關鍵。為找到適合的語言,王安憶轉向張愛玲,因為“她特別善于用實的來寫虛的”①王安憶:《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王安憶自選集之四·漂泊的語言》,第451—472頁。,并“自承多受張愛玲語言觀的教益:張是將這語言當作是無性材料,最終卻引起了意境”②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見傳人》,《讀書》1996年第6期。。
1997年,她清楚地定義這種語言為抽象化語言,完全沒有風土化、時代感和色彩性,所用的是語言中最基本的成分,動詞尤多。對話放棄個性,只用敘述來處理。這語言可用于各種類型的創作,是小說世界真正的建筑材料③參見王安憶:《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第312—318頁。。2012年,她強調語言是小說本質性條件,特質之一是狹隘,功能很有限,只能夠敘述④王安憶:《小說創作——在常熟理工學院“東吳講堂”上的講演》,《東吳學術》2012年第2期。。
在論述了隱含作者應該理性廣博、注重敘述并確立不帶風土化的抽象敘述語言之后,王安憶形成了一套屬于自己的小說敘事理念。1988年在《我的小說觀》里,她表述的小說的最高境界是:將從個人經驗與認識里得來的小說思想部分,與邏輯推動力量的敘述方式,即小說的物質部分二者融為一元,并用“四不”來概括。評論界認為她“看重小說總體性表達效果,自身即具有重大意義的情節,故事發展的內部動力,而對偶然性、趣味性、個人標記、寫作技巧等等的夸大使用持警惕和懷疑態度”⑤張新穎:《堅硬的河岸流動的水——〈紀實與虛構〉與王安憶的寫作理想》,《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5期。。
王安憶說:“有些事情要想明白了再做,另有些事情則是做起來才明白。所以,我就只有邊想邊做。”⑥王安憶:《我的小說觀》,《王安憶自選集之四·漂泊的語言》,第330—333頁。做得如何,是否實現她的理想,將是下文要探討的內容。
二、王安憶的小說敘事實踐
(一)相對統一的敘述者
1990年的《叔叔的故事》是王安憶近一年封筆之后的開筆作,她強調它是被敘述出來的,自己很滿意⑦王安憶、斯特凡亞、秦立德:《從現實人生的體驗到敘述策略的轉型》,《當代作家評論》1991年第6期。。而它與以往小說最大的區別在于,文中有“同故事”的敘述者。開篇就是:“我終于要來講一個故事了。”⑧王安憶:《叔叔的故事》,《王安憶自選集之三·香港的情與愛》,第1—78頁。以下關于《叔叔的故事》的引文,均據此書。理論上“不參與故事的敘述者叫‘異故事’的,參與故事的敘述者,至少就他的‘自我’的某些表現而言,是‘同故事’的”⑨[以色列]里蒙·凱南著,姚錦清等譯:《敘事虛構作品》,第171頁。。
敘述者對人物進行識別和判定:“他與我并無血緣關系,甚至連朋友都談不上,所以稱之為父兄,因為他是屬于我父兄那一輩的人。”“叔叔的審美從本質上說,是一位古典浪漫主義者。”叔叔沒有在文革中自殺,是因為“沒有將自己那顆敏感,嬌嫩,高傲,易受傷害的靈魂逼到絕路上,他讓它中途就開溜了,而人的肉體可說是百折不撓”。敘述者也評論故事的敘述,如:“我所掌握的講故事的材料不多且還真偽難辨……于是,這便是一個充滿主觀色彩的故事,一反我以往客觀寫實的特長;這還是一個充滿議論的故事,一反我向來注重細節的傾向。”并表示敘述者是“靠講故事度日的人”。敘述者平和口吻里流露出機智,既認真思考又有幾分調侃,顯然受過良好教育并有一定的閱歷。
《妙妙》中則有隱身敘述者,未參與故事,卻知道一切。如識別人物:“寶妹是七零年下鄉知青。”⑩王安憶:《妙妙》,《王安憶自選集之三·香港的情與愛》,第384—425頁。以下關于《妙妙》的引文,均據此書。描述情景:“從午后開始,招待所里就充滿了清脆響亮的北京話。”評論妙妙:“十六歲的妙妙野心很大,她從心底里就瞧不起頭鋪這地方,也瞧不起縣城,省城這樣的地方,或許還能將就將就,她只崇拜中國的三個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妙妙的這些苦惱,已不僅僅是有關服飾方面的具體問題,而是抽象到了一個理論的范疇,含有人的社會價值內容,人和世界的關系,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這些深刻的哲學命題在此都以一種極樸素的面目出現在妙妙的思索和斗爭中。”這顯然不是16歲未受過高等教育的小鎮姑娘所能說的,只能是敘述者的聲音。敘述者之所以發出這樣的聲音,是因為支配它的是對妙妙等人的價值問題有著深入思考的隱含作者。
無論對名人“叔叔”,還是小鎮“妙妙”,敘述者都既理解又批判:理解叔叔對崇高的渴望,又批判他內心的怯懦;理解妙妙的追求,又惋惜她未正確認識自身及環境。敘述者有著一致的特征:有知識、閱歷和同情心,善于深思并擅長文字工作。這個在王安憶1990年代的小說里開始出現并基本形象統一的深思悲憫的敘述者,成為其小說敘事追求的一個重要構成。
有論者認為“四不”里的“不要特殊人物”,即小說不要選擇特別的敘述者和人物①曹愛華:《試論王安憶的小說敘事觀》,《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本文則認為,王安憶的確說過不愿“將人物置于一個條件狹隘的特殊環境里,逼使表現出其與眾不同的個別的行為”②王安憶:《我的小說觀》,《王安憶自選集之四·漂泊的語言》,第331頁。,但所指的是通常意義上小說的典型環境典型人物,重點不在敘述者。其實三種敘述者——書中人物充當的、置身故事外無所不知的、不清楚是從故事內部還是外部講述故事的③[秘魯]巴·略薩著,趙德明譯:《中國套盒》,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37頁。——都屬于敘事作品中的重要人物。隨著敘事實踐,當小說中敘述者顯出一致的特征時,她的“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就出現了斷裂。不要特殊環境,所以小說故事千變萬化,但敘述者卻始終保持了較為一致的特征。
(二)選擇不同的“邏輯”推動故事
當表達人的內心世界、情緒體驗成了王安憶的創作意圖時,她為之套上邏輯外觀以推動小說,具化為敘事模式中的以對某種性格或者心態情結透視為主的情態模式和以情緒性體驗為主的情調模式④參見徐岱:《小說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254、263頁。。
1.選擇以性格、情結為主的情態模式推動故事。《長恨歌》中的王琦瑤被突出為具有韌性:“王琦瑤的形象就是我心目中的上海。在我眼中,上海是一個女性形象,她是中國近代誕生的奇人。”“上海的女性有一股永往直前的勁頭,更有一種韌性,沒有太高的升華,卻也沒有特別的淪落,她有一種平民精神。”⑤張新穎:《上海這個城市的精神就像上海的女性——王安憶談〈長恨歌〉》,《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1996年第1期。平民精神即王琦瑤性格核心,小說則以這種性格為邏輯力量推動《長恨歌》進程。
王琦瑤雖出自弄堂,卻不甘平庸,一旦有可能,就抓住機會上升:“上海小姐”第三名給了她希望,她甘做權貴李主任的外室。可時勢卻又讓她重歸平民:李主任死了,留給王琦瑤一盒金條和一個尷尬身份。面對困境,王琦瑤又從鄉下鄔橋回到上海,開始新的角逐。她始終向往生活和情感的燦爛,當一切都不可能時,就拿出平民韌性,抵抗命運磨難。故事借這種“韌”向前發展:她追求年輕時的富貴,身份莫名時的愛情,年老時的青春快樂。她的不斷追求與不斷喘息推動著故事:第一次追求留給她一盒金條,第二次追求給了她女兒,第三次追求則致她于死地。這些追求敷衍出跨越幾個時代的故事。
在《紀實與虛構》里,王安憶“竭力追求某種形式的東西……超出經驗的東西,直接地說,就是虛構和抽象的東西”,是人“在人世間走來走去無法為自己定位的那種存在的孤獨”,以及“如何在一切都將消失一切都不那么穩定的情況下努力把自己固定下來挽留下來的渴念”⑥陳思和、王安憶、郜元寶、張新穎、嚴鋒:《當前文學創作中的“輕”與“重”文學對話錄》,《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5期。。此即人類普遍存在的焦灼情結,對無根的恐慌和對虛無的恐懼,具有穩定性和普泛性,是個體行為重要的內在心理動因。
小說中追尋母族故事的“我”力圖織好證明“我”存在的人際關系網,說:“很久以來,我們在上海這個城市里,都像是個外來戶。”①王安憶:《紀實與虛構》,《王安憶自選集之五·米尼》,第149—433頁。以下關于《紀實與虛構》的引文,均據此書。“我從小就這樣熱衷于進入這個城市,這樣生怕落伍。”選擇以“我”的融入和尋找情結綴連故事,結構上開合自如,可任意處置材料,可在某處抒發感情,又可在某處插入小故事,實現故事整體的銜接與串聯。
2.以情緒性體驗為主的情調模式推動故事。在《傷心太平洋》中,王安憶調動時空對比,以通篇的傷痛情調表達對人類飄泊命運的悲憫。太平洋和新加坡島被賦予象征意味:“島嶼是多么危險的東西啊!它無時無刻不面對著沉沒與沖擊,它在波濤的喘息間歇中茍存。島嶼像一個孤兒,沒爹沒媽,沒有家園。太平洋上的島嶼,全有一種漂浮的形態,它們好像海水的泡沫似的,隨著波濤涌動。”②王安憶:《傷心太平洋》,《王安憶自選集之三·香港的情與愛》,第305—384頁。以下關于《傷心太平洋》的引文,均據此書。小說還選用大小事件的相同刻度,揭示亂世中個人遭際之微茫,營造無奈傷痛:“當我父親索索抖成一團,在小旅館里等待黎明和吳天的時候,關于日本進攻新加坡的計劃正在激烈而復雜的爭論之中。”“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三日,就是說日本進攻新加坡的第五日,也是英國人投降的前二天,英國人其實還具有極強大的戰爭實力。”
《紀實與虛構》和《傷心太平洋》被稱為王安憶對小說寫作的大型演練,是在創造某種神話并展示創造過程③陳思和、王安憶、郜元寶、張新穎、嚴鋒:《當前文學創作中的“輕”與“重”文學對話錄》,《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5期。,是“領悟小說本質虛構的表示”④李潔非:《王安憶的新神話——一個理論探討》,《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5期。。這些都與她選用的情態和情調敘事模式有關。
(四)從排比語段到直白抽象的敘述語言
在《香港的情與愛》中,王安憶特有的排比句式組合開始穩定。如描述逢佳:“她滿身都藍,她的妝也化得夠嗆,她的臉盤又大,頭發又濃,她的額角和臉頰是飽滿的,她的眼睛很大很亮,有一種無法言說的溫柔。”這種排比句式在《長恨歌》中發展到極致。如描寫靜物:“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種種聲色各異的……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膚之親似的。”描寫流言:“流言總是帶著陰沉之氣……流言總是鄙陋的……流言是混淆視聽的……流言的浪漫在于它無拘無束能上能下的想象力。”描寫活動:“他們在爐邊還做著一些簡單的游戲……他們還用頭發打一個結,他們有一個九連環,他們還有個七巧板,他們動足腦筋,多少小機巧和小聰敏在此生出,又湮滅。”
這種排比語段的基本模式是:用簡單排比句展示人物景物或活動;在語段結尾作結論,它們或是行動的理由,或是心理活動結束的提示。大量排比的判斷句形成一個個語段,使作品顯得流暢自信。它們無明顯的地域化,沒有特殊的語氣詞,遣詞造句都是普通的書面語,反映了王安憶敘事“不帶風土化”的要求。
在《天香》中,她將這種抽象敘述語言更推進一步,慣用的排比放棄了,多用四字句:“本朝開始,此地就起了造園的風氣。”“于是,學校林立,人才輩出,到此時,可說鼎盛。”“酒菜布好,人就都不見了。”⑤王安憶:《天香》,《收獲》2011年第1期。以下關于《天香》的引文,均據此書。至此,王安憶達到她對敘述語言追求的極致,無風土化、時代感、個性化和色彩性,精簡直白。如《天香》中說,刺繡像書畫的關鍵是“描”,這篇小說用的是語言“白描”。王安憶說自己向來注重語言,有過幾個從簡到繁從繁到簡的來回,為體現《天香》的時代特點,更在語言方面做了大功課,希望做到典麗。而四個字的句子的這種漢語骨架,她很高興被人夸獎在別的作家多不會用的情況下,自己還算會用⑥王安憶、鐘紅明:《訪問〈天香〉》,《上海文學》2011年第3期。。
三、與“四不”相對照的小說敘事風格
(一)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卻有特殊的敘述者
王安憶上世紀90年代以后小說中的敘述者都通達理智,有著悲憫情懷,這是其小說敘述者的獨特之處,這種獨特性來自隱含作者對世界及人性有廣博了解的追求。
當她追求敘述,決定不再用照錄人物對話的敘述方法時,未必想到文本的敘述者從此再不能退場。當對話不再揭示場景、交待故事時,所有責任只能由隱身或暴露的敘述者完成:“一旦你給了主角敘述者以文學才能,你就使讀者很難視他為性格獨特的人。”①蓋利肖:《小說寫作技巧二十講》,轉引自徐岱:《小說敘事學》,第205頁。在很多情況下,小說只能以犧牲敘述者的性格化來換取敘述話語的藝術化,用隱含作者的個性來限制敘述者的個性,所以小說敘述者在富有哲理的特點下存在著類型化的不足,難免雷同感。
(二)不要材料太多,逐漸純熟運用虛構
在“四不”當中,王安憶認為經驗性材料間不一定具備邏輯聯系,之所以宣稱不要材料太多,是因為她找到了邏輯推進的“虛構”。在小說中,她用人物韌性、追尋情結、傷痛情調、造園情結等邏輯力量為虛構武器。如果不要材料太多的“材料”專指“經驗性材料”,當她用情態、情調模式等邏輯推進長篇小說時,她確實做到了“四不”中的“不要材料太多”,并且“以虛擊實,甚至滋生比現實更深刻的東西”②王德威:《虛構與紀實——王安憶的〈天香〉》,《揚子江評論》2011年第2期。。
(三)不要語言的風格化,卻形成特定語言
在語言風格化方面,王安憶卻將風格與風俗混淆。對于小說,“風格是小說形式中的基本成分。沒有一個連貫而且必須的風格就不可能成為小說家”③[秘魯]巴·略薩著,趙德明譯:《中國套盒》,第26、33頁。。她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作品的確使用不帶風俗化的抽象書面語言表述了故事,但頻繁出現的排比句語段就是一種風格。《天香》雖然沒有成段排比,但四字句的頻頻使用也是一種風格。
王安憶的闡釋體(即提出概念再加闡釋)語言曾被不少評論者詬病,認為她“過于迷戀自己從容均速的敘事話語,沉醉其中,自得其樂,忘記其它存在”。評論者認為這種語言固然增加了敘述力度,但欠缺流動感④月斧:《挑戰與超越——〈長恨歌〉討論會札記》,《鐘山》1996年第1期。;或說她的句法“冗長雜沓,不夠精謹,意象視野流于浮露平板”⑤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見傳人》,《讀書》1996年第6期。,認為“讀過王安憶的小說之后,閱讀者會有一種漫長而纖細的疲憊之感,總是無法擺脫無處不在的作者意志”⑥李靜:《不冒險的旅程——論王安憶的寫作困境》,《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1期。。
(四)不要獨特性,卻有形象統一的敘述者和相對穩定的語言風格
如果說王安憶小說敘事理論是其敘事追求的思想部分,小說敘事創作實踐是其物質部分,二者合一即其小說敘事風格,包括:深思悲憫的敘述者,無特定地域風俗、抽象精簡卻又綿密如織的語言。這就是她的獨特性。
1997年,她在界定小說時認為:小說是另外決定的獨立存在,由它的原則去推動發展;而這世界由一個人創造,帶有很強的心靈特征,完全個人的精神特征,你是怎樣的人,怎樣的性情,都會在此有所表現,而且,絕對只是你個人的⑦王安憶:《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第13—14頁。。此時她從一個側面回應了自己1988年“四不”之“不要獨特性”,說明沒有獨特性的不可能。評論者認為其作品:“不論是景物描寫還是人物描寫,都充溢了王安憶小說敘事的那種舒緩節奏,敘述人無所不在的敏銳、細膩,以及多愁善感的女性化、感性化話語。”⑧韓蕾、劉旭:《王安憶小說的自訴型敘事方式分析》,《福建論壇》2007年第8期。
王安憶用“四不”表述的小說敘事理想,前兩點大部分都可以做到,而后兩點則不可能做到,其小說敘事風格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她成就斐然,《長恨歌》和《天香》分獲大獎,《天香》使她被評為“有能力、有悟心、有氣魄寫俗情世事而與歷史的邏輯和天地的生機相通”①張新穎:《一物之通,生機處處——王安憶〈天香〉的幾個層次》,《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4期。,并擁有自己的小說理念:“很多作家都能寫出好小說,但未必都有自己的小說觀。中國當代的小說家中,只有韓少功、王安憶、莫言、余華、北村、格非等少數一些人,對小說寫作形成了自己比較成熟的看法。”②謝有順:《小說的物質外殼:邏輯、情理和說服力——由王安憶的小說觀引發的隨想》,《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3期。她旺盛的創作力,正來自對小說敘事理論和實踐的自覺追求。
當然,批評的聲音也始終伴隨,如認為在《叔叔的故事》中,“她設計故事只不過為議論找到一個形象化的象征框架,并抹殺了‘叔叔’作為一個具有鮮活生命力的人物屬性”,使人“懷疑王安憶是否在寫一篇論文”③吳義勤:《王安憶的“轉型”》,《文學自由談》1992年第1期。。認為她這種缺少空白的敘事使讀者成了隔岸觀火者,觀看她鳥瞰的圖景和概括的思想,作品不是“展現”而是“指引”,容易導致獨斷的單向性④李靜:《不冒險的旅程——論王安憶的寫作困境》,《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1期。。
無論如何,分析其敘事理論,對照其敘事實踐,可以發現王安憶在追求過程中,有得有失,但都給她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創作力,實現了她將自我與廣闊社會相連的愿望。她在這個過程中對自己理論的修正,她的“四不”理論一半實現一半悖論的實驗,都將給職業作家創作長篇小說以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