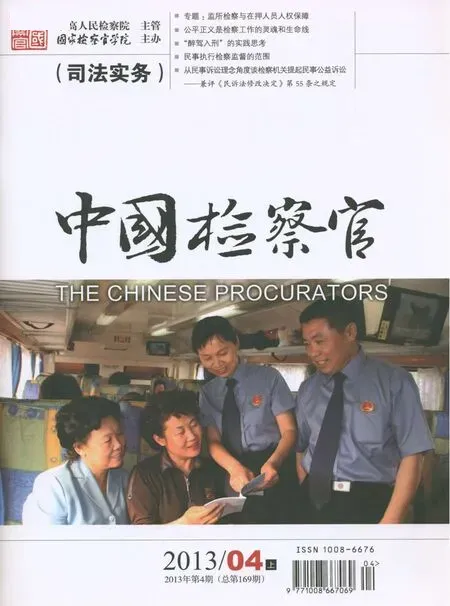試論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的統一
文◎“法律監督、訴訟監督與公訴權的關系研究”課題組
試論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的統一
文◎“法律監督、訴訟監督與公訴權的關系研究”課題組*
*本文系2011年度浙江省人民檢察院重點課題《法律監督、訴訟監督與公訴權的關系研究》【sy2011A05】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組成員:高杰(浙江省寧波市江北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王淑玲、丁連連、張福祥、鄭培金(浙江省寧波市江北區人民檢察院干警),何斐明(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研究室主任)。
公訴職能和訴訟監督職能在法律監督屬性上具有一致性,都是實現法律監督的必要載體。并且,公訴職能是訴訟監督的核心權能,是訴訟監督得以實現進而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主要手段。兩者的聯系不言而喻,然而關于公訴職能和訴訟監督職能,特別是和訴訟監督中的審判監督能否并存卻有諸多爭議。
一、對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分離說的回應
我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者地位早已在憲法中得到明確,但仍有部分學者認為公訴與監督職能存在角色沖突。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要求把檢察機關的公訴職能和訴訟監督職能,特別是與審判監督職能相分離,甚至主張改變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者”地位,使其成為單純的刑事追訴機構,不再同時承擔法律監督和刑事追訴這兩項“相互矛盾”的訴訟職能。梳理這些觀點,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幾種:
1.從刑事訴訟構造看,檢察官作為公訴人,與被告人處于平等的地位,作為審判監督者,又在法律上取得超越當事人的地位,這就難免改變控辯平衡的格局。此論者忽視了我國刑事訴訟結構特點,而將我國的公訴權置于英美法系的刑事訴訟結構背景之下。
2.從訴訟角色看,檢察機關作為追訴者,要積極地進行追訴活動;而作為監督者,則需要盡量保持其超然性和中立性以求社會公正,存在角色沖突。這種觀點在邏輯上混淆了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之間手段和目的的關系。
3.法院的審判具有司法終局性,如果對法院審判的活動進行監督,就會弱化法院審判權行使的獨立性,損害審判權的權威。這種觀點錯誤地把公訴權提請追訴的程序性權力當作一種實體處分的權力,把不同主體之間的制約式監督當作上級對下級的監督,過分夸大了檢察機關的權力。
二、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在司法實踐中的統一
從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上看,公訴職能和訴訟監督職能可并行不悖,共同實現法律監督目的。
(一)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并存不影響控辯平等
1.刑事訴訟模式決定了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并存的必要性。有觀點認為,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并存會使檢察官凌駕于當事人之上,改變控辯平衡格局。這種觀點忽視了英美法系與我國刑事訴訟結構之間的區別。
英美法系實行當事人主義的刑事訴訟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檢察官只是單純的犯罪追訴一方當事人,不具有專門的監督權力。究其原因在于,陪審團的制約、判例法的約束以及充分說理的判決書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保證了法官在實體上的自由裁量權較小且不易被濫用。程序上,由于訴訟主要由當事人進行推進,法官并不積極主導和指揮庭審,而詳實縝密的證據規則使得庭審過程比較規范,法官在程序上的自由裁量權也較小,因而賦予控方的法律監督權實無多大必要。[1]
在我國的訴訟模式中,法官積極主導整個審判程序的進行。同時,與英美法系相比,我國刑事被告人所享有的訴訟權利范圍更窄。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唯有保持對法官的適當監督,使其以法律監督者的身份監督法庭審判的合法性,才是維護控辯平衡的關鍵。由此可見,部分學者在英美法系刑事訴訟結構的背景下審視我國的公訴職能,從而得出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不能并存于同一個機關的論斷,難免存在著 “拿來主義”的偏頗。
2.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并存有利于控辯平等。檢察機關究竟作為單純的公訴機關時片面控訴傾向大,還是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時片面的控訴傾向大?答案顯而易見。當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時,將維護法治和公平正義作為宗旨和價值追求,公訴權僅是其諸多權能中的一項,是實施法律監督的一個手段。檢察官和被告人之間只是形式上存在某種對立關系,被告人要維護的是其自身權益,而檢察官要維護的是包括被告人正當權益在內的公共利益。[2]在法庭上,公訴人不僅負有指控犯罪之責,還負有根據事實和法律公正地闡述被告人罪輕或法定從輕、減輕的事實和情節,并且對法庭損害被告人合法權益的情況進行法律監督的職責。庭審后,公訴人不僅要對有罪判無罪、重罪輕判的判決提出抗訴,而且要對輕罪重判的判決或損害被告人合法權益、違反程序的判決提出抗訴或者提出違法糾正意見,從而確保司法公正,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3]
可見,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并存,是立足于中國現階段刑事訴訟模式的選擇,有助于檢察機關保持客觀公正立場,防止以控訴犯罪為終極目標,從而維護了控辯平衡。
(二)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并存無損于審判權威
首先,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作為一種程序性的行為,只能引起法院對有關規定或裁決進行重新審查或審理,并不會對案件的實體處理有裁決權,也不會產生不當的影響。一方面,對于法院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可能影響判決實體內容的,雖然檢察機關可以通過抗訴引起二審或再審消除違法行為的影響,但其只能開啟程序。另一方面,對于其他違法行為,檢察機關僅能向法院提出糾正違法的意見,如果法院不認可或不進行糾正,在目前法律規定下,檢察機關尚無進行制約的手段。因此,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不可能損害法院的審判權,更不會影響司法權威。
其次,我國檢察權的本質屬性表現為 “法律監督權”,但這一權力并非是絕對的、超然的、自上而下的“上位監督”。實際上,檢察權是一種對審判權有限的、平位的制約性監督。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權本就是一種異議權,這種異議和訴訟當事人所提出的異議是一樣的,法院并沒有必須遵行的義務。另一方面,檢察機關依托公訴權履行訴訟監督職能的同時受到公安機關及法院的制約。由此可見,檢察機關的訴訟監督并非“凌駕于法院之上”,而是一種相互獨立、互相平等的制約性監督。
再次,訴訟監督不會對嚴格司法的法官產生負面影響。那種認為法律監督會對法官判案造成壓力,進而導致法官屈從于檢察官的觀點,完全是對法律監督的誤解。審判監督對法院及其審判人員來說,都不存在產生威懾力的問題。訴訟監督是對法官違法行為的監督,是對實施違法行為的法官的威懾,而非對公正司法法官的威脅。
綜上,公訴履行訴訟監督職能是一種程序上的權力,是不同主體間的制約式監督,無損于審判權威。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一方面通過審判活動合法性監督,糾正審判中的違法行為,實現審判程序公正;另一方面通過對確有錯誤裁判的抗訴,糾正錯誤判決,實現審判結果公正,只會有益于審判權威的實現。
(三)公訴與訴訟監督職能不具有分離的現實可行性
有些學者認為,有必要將公訴職能和審判監督職能的行使分離開來,成立專門的刑事審判監督部門和公訴部門。我們認為,這種通過割裂兩種職能以求達到司法公正和獨立的設想,會切斷刑罰適用內在的連續性,是脫離司法實踐的臆想。眾所周知,一個案件在移送審判以前,檢察機關審查起訴、作出起訴或不起訴決定、退回補充偵查等行使公訴職能的行為,其實都是對刑法適用問題的不斷判斷,也是在為審判階段對法院有關事實、罪名、量刑等多個方面的審判監督做好準備工作。如果分設部門,審判監督部門在不充分參與整個訴訟過程的情況下,又如何去發現訴訟的瑕疵?在另一種假設下,單設的審判監督部門和公訴部門一樣參與訴訟程序,分司不同職責,那么,如此情形又和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由同一部門行使有何區別?這種做法不僅使機構的設置更為復雜,而且浪費了司法資源,忽視了法律的社會效益。
更應強調的是,在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分離模式下,抗訴權的歸屬問題。眾所周知,抗訴是公訴權不可分割的重要權能。若將公訴與訴訟監督職能割裂分離,就會出現抗訴權在部門歸屬問題上的兩難。假設一,將抗訴權保留于公訴部門,公訴僅僅以控訴犯罪為目的,那么具有明顯監督屬性的抗訴權,特別是有利于被告的抗訴行為將與公訴權追求的控訴犯罪相矛盾,導致部分與整體相沖突;假設二,將抗訴權歸屬于訴訟監督部門,這樣不僅閹割了公訴權,同時造成監督者游離于刑事訴訟程序之外,導致監督不力或無法監督的后果。由此可以看出,“分離模式”脫離了中國的憲政制度和司法實踐,根本不具有現實可行性。
三、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統一的條件——遵循訴訟規律和監督機制
毋庸諱言,檢察人員難以把握控訴職能與監督職能間的平衡,顧此失彼的情況確實存在。因此,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的統一必須遵循訴訟規律和監督機制的內在要求。
(一)公訴權實現訴訟監督必須遵循訴訟規律
訴訟監督遵循訴訟規律,就是尊重各方當事人的平等地位和權利義務平衡、維護三方訴訟構造的平衡,維護司法權威,實現解決糾紛、監督權力、維護秩序、保障自由的功能。[4]遵循訴訟規律應當注重以下三個方面。
1.強化控方的法律監督者義務。理順公訴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的根本途徑在于淡化人民檢察院的訴訟當事人色彩,強化其法律監督者身份。因此,檢察機關應當從維護法律公平和正義、監督國家權力的正當行使、保護訴訟當事人權利角度去履行公訴職能,而非一味追求對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同時,檢察機關并不因其法律監督者的身份而擁有凌駕于公安機關、人民法院之上的地位,其法律監督職能必須通過與其他機關之間的分工和制衡獲得實現。
2.保障并強化辯方的權利。新刑訴法在保障辯方權利方面實現了歷史性的進步,但能否落到實處,除了需要相關配套制度的完善,也需要控方嚴格遵循法治原則履行監督職責,不得凌駕于辯方之上,損害訴訟構造。履行公訴職能時,須注重維護辯方的辯護權,保護犯罪嫌疑人權益,不斷提高公訴活動的透明度和辯方的參與度。
3.注重維護裁判者的司法權威 。司法的權威,建立在司法的終局性上。反復無常、肆意變化的裁判會動搖民眾對司法的信賴,進而動搖整個社會對法律信仰的根基。這就要求檢察機關在行使公訴權進行訴訟監督時,妥善處理監督者與控訴者的角色定位,客觀公正地處理檢法關系,不能直接或間接地對法院的活動進行干涉,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范圍、程序和方式進行監督。
(二)公訴權與訴訟監督并存必須遵循監督機制
訴訟監督作為實現法律監督的一種形式,是國家整體監督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公訴與訴訟監督職能并存要遵循監督機制。一般認為,監督機制內在的本質要求包括以下幾點。
1.監督主體的獨立性。公訴權實現訴訟監督職能要求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地進行訴訟監督,不受其他任何機關、組織和個人的非法干涉。當然,強調監督主體的獨立性并非排斥與偵查、審判機關之間的協調配合,訴訟監督作為一種間接控制的監督行為,需要被監督者或其他主管部門的配合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2.監督對象的公開性。公訴作為實現訴訟監督職能的主要方式,其監督對象主要指偵查機關和審判機關。監督對象的公開性要求在立法上盡力疏通訴訟監督的知情渠道,具體規定偵查機關和審判機關在一定范圍內公開相關信息的法定義務,從而保證監督信息的對稱性。
3.監督關系的對等性。公訴權實現訴訟監督職能主要通過啟動訴訟這一程序性權力,監督決定一旦做出,只有被監督對象在法律上做出相應的反應,訴訟監督才有效果。這就要求立法賦予偵查機關和審判機關一定范圍和強度的權力時,就應當賦予檢察機關以相應范圍和強度的權力,從而使權力與所受到的監督約束對等。
4.監督手段的強制性。立法不僅應當賦予檢察機關針對具體事項提出糾錯、整改或處置的檢察建議權,而且同時要對監督對象落實糾錯、整改或處置并附時限地反饋相關信息的義務作出規定。
注釋:
[1]張少林:《構建雙向三角訴訟結構——堅持公訴權和審判監督權統一行使新論》,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
[2]汪建成:《論訴訟監督與訴訟規律》,載《河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
[3]孫謙:《檢察:理念、制度與改革》,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頁。
[4]曹建明:《堅持法律監督屬性,準確把握工作規律,努力實現民事行政檢察工作跨越式發展》,載2010年7月26日《檢察日報》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