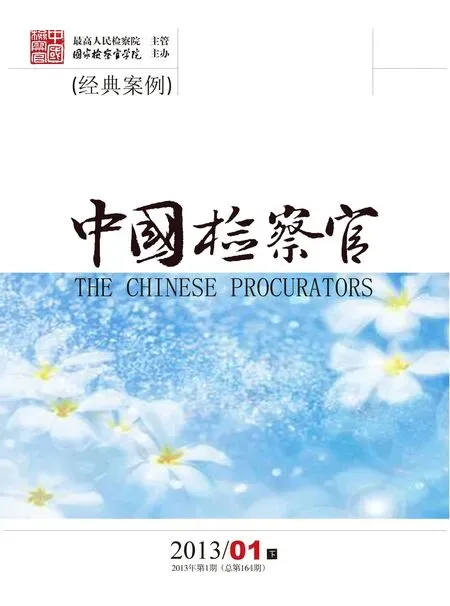借用他人資金炒股牟利型受賄案的實務難題
文◎王會麗
借用他人資金炒股牟利型受賄案的實務難題
文◎王會麗*
[基本案情]丁某,原系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副庭長。2003年9月,某造紙有限公司向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時任經二庭助理審判員的丁某主辦該案。2006年6月,破產企業國有土地及地上附著物進行破產拍賣程序。該市一拍賣公司董事長彭某為取得拍賣權,多次請求丁某給予幫助,并且暗示如果取得拍賣權不會忘記丁某。在丁某幫助下,彭某取得了破產企業的拍賣權。拍賣結束后,彭某多次提出要給丁某錢物以示感謝,丁某提出如實在要感謝,就往股市投點資金,由丁某操作炒股,賺了錢均分。彭某專門就此召開公司股東會,商議決定拿出100萬元給丁某炒股,賺了算丁的,賠了算公司的。彭遂后將100萬元資金注入自己在股市的賬戶,并將炒股所需手續與密碼交給丁某,丁某修改了密碼。自2007年3月至2008年2月,丁某利用彭提供的100萬元炒股取得收益共計106.85萬元,并陸續全部提出,其中最后一筆30萬元系丁與彭二人一起提出,彭又交給了丁。丁某將炒股收益中的25萬余元用于歸還個人購房貸款,30萬元存入父親名下銀行賬戶,20萬元存入愛人名下賬戶,20萬余元丁某存入自己在股市的賬戶,其余款項用于個人日常花銷。炒股本金100萬元留存股市。2008年3月案發。
一、案件爭議焦點
本案的爭議焦點有兩個:一是丁某是否構成受賄罪;二是丁某的行為如果系受賄,其受賄數額應該如何認定。
認為丁某不構成犯罪的理由是,盡管丁某利用職務便利為彭某謀取了利益,但丁某只是從彭某處借用100元進行炒股,并從中獲益,100萬元既然屬于借用,當然不能認定受賄;而炒股收益106.85萬元的獲得基于丁某的智力因素,屬于一方出錢、一人出力的合作經營,不屬于“兩高”相關司法解釋中的合作投資型受賄,不能以受賄論。
主張丁某構成受賄罪者則認為,丁某利用職務之便為彭某謀取利益之后,以合作炒股名義要求彭某無償提供100萬元人民幣,并進而獲取全部炒股利潤106.85萬元的行為屬于變相受賄,應當以受賄罪定罪處罰。在此基礎上關于受賄數額還有三種完全不同的意見。一是認為彭某提供的100萬元炒股本金為丁某受賄數額,100萬元名為借用實為索要,丁某屬于以借為名的變相受賄;二是認為丁某利用彭某提供的100萬元進行炒股所獲收益106.85萬元為其受賄數額,屬于以合作炒股為名的變相受賄;三是認為應將100萬元同期銀行貸款利息6萬余元作為丁某受賄的數額,100萬元是借款,106.85萬元為投資收益,均不能認定受賄,但是丁某基于職務行為而無償使用請托人100萬元借款整整一年,屬于可以用金錢衡量的財產性利益,應當以同期銀行貸款利息作為其受賄數額。
二、觀點剖析
本案中對丁某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利這一基礎事實并無爭議,對丁某從請托人處獲取巨額利益與其職務行為密切相關也沒有爭議,可是在定性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這固然與我國刑法對受賄罪的規定比較嚴苛有關,但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對我國受賄犯罪有關法律規定的理解不同。自1997年刑法修訂以來,對受賄罪構成要件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直到2003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才對“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等語詞的涵義進行權威解讀,統一了認識。隨著社會發展,受賄手段日益翻新,各種新型權錢交易方式不斷涌現,這些新型權錢交易是否構成受賄犯罪又成為司法實踐中的爭議焦點。2007年“兩高”專門出臺《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對交易型受賄等多種新型受賄犯罪行為進行明確具體的界定。但是,立法規定越是詳盡,其滯后性越是凸顯,司法實踐中不能與 “兩高”司法解釋完全契合的情況比比皆是,對于這些司法解釋未涵蓋的新型權錢交易形式如何定性,就需要司法工作者根據法律精神,對各種行為進行深入解析。如何結合具體國情、社情與案情正確理解、準確運用現行法律規定,正是考量司法實務工作者智慧的關鍵所在。
本案中丁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幫助請托人彭某獲得破產企業土地及地上附著物的拍賣權,請托人彭某向其表示感謝要送錢,丁拒絕要錢,并提出借用其資金炒股以及一人一半的分紅建議。彭某公司召開股東會,議定拿出100萬元給丁某炒股,賺了算丁的,賠了算公司的。此后,彭某將錢注入個人股市賬戶,并將炒股所需手續及密碼交給丁某,丁某收下后修改了密碼。至此,這100萬元已完全由丁某支配。一年間,丁某用此賬戶炒股獲利106.85萬元。至案發,100萬元本金尚在股市賬戶,炒股盈利由丁某陸續取出并全部用于其個人或家庭消費。上述行為過程頗為復雜,但如果透過表象看本質,本案實質為:丁利用職務便利為彭某謀取利益,彭某為此拿100萬元供其炒股,丁獲利巨大。就此分析丁某的行為是否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是否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答案無疑是肯定的。筆者認為,丁某的行為應當以受賄罪定罪處罰,理由如下:
1.與一手收錢、一手辦事的普通受賄相比,丁某的這種權錢交易有著更為隱蔽的外衣,其社會危害性更大,影響更加惡劣。
2.本案的爭議之一是針對丁某系列言行不一的客觀表現,如何判斷其有無受賄的主觀故意,事實上,只要注意到丁某的法官身份,就能夠得出肯定的結論。丁某作為一名受過本科系統教育、從事法律工作十余年的法官,嘴上說不要對方感謝,卻又提出讓對方出錢炒股;嘴上說100萬是共同炒股,私下卻修改密碼、獨自支配;嘴上說盈利一人一半,實則個人全部侵吞。這種種矛盾正是因為丁某具有高于普通人的法律理解能力,并且有意實施逃避法律追究的行為。
3.本案的另一個爭議點是丁某的受賄數額如何認定。關于100萬元,請托人與丁某的表述完全一致,即100萬元系借用,雖然由丁某完全支配,但案發時仍留存于股市彭某名下賬戶,其所有權自始至終沒有轉移,因此不應認定為受賄數額。通過炒股賺取的106.85萬元利潤,丁某最初“一人一半”的提議顯然只是托詞,彭某對此心領神會,該公司股東會議定丁只享炒股收益不承擔風險以及丁某將收益全部歸己的客觀事實充分證明,丁彭二人以“合作炒股”之名行變相受賄之實。盡管炒股獲利需要丁某的智力因素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本案發生于2007、2008年,當時我國股市全線飄紅,投資者只有賺得多或少之分,因此最能體現丁某聰明才智的,恰恰是丁某在彼時精心籌劃這種掩人耳目的方式謀取非法利益,而并非其作為業余散戶的炒股才能。反對者會提出,炒股能否賺錢或能賺多少,對于行受賄雙方都無法事先確認,因此將炒股利潤認定成受賄數額是客觀歸罪的結果。事實上,本案中,彭某、丁某商定以彭某出資供丁某炒股獲利,體現了雙方明確的行受賄故意,丁事后獲得多少利潤,就是受賄多少,這正是主客觀相一致的結果。以盜竊罪為例,其犯罪數額同樣是依據行為人實際得手的財物數額來認定。如果盜竊未能得手,只能認定盜竊未遂,而在本案中,即使炒股賠了錢,仍然不能認定其受賄未遂,因為巨額炒股資金的銀行同期貸款利息,以及損失的炒股本金數額,都是能夠用金錢衡量的財產性利益,都可以成為行為人受賄罪的對象。
綜上,2007年3月,當請托人彭某將注有100萬元的股東卡交給丁某操作時,丁某得到的絕非辯方所稱的一個炒股機會而已,更是一種可衡量的財產性利益,因此其行為性質屬于受賄確定無疑,只是當時的受賄數額尚需以丁某事后實際獲得的利益來最終確定。
三、判決結果及評析
本案訴訟過程一波三折,在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歷經幾級檢察委員會多次研究,最終以丁某涉嫌受賄206.85萬元向法院提起公訴。2012年3月,一審法院判決認定,被告人丁某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公司謀取利益,作為回報,請托人提供100萬元本金交由丁某炒股,并約定虧賠風險請托人公司承擔,雙方行受賄意思明確,符合受賄罪的權錢交易本質特征。炒股盈利悉數為被告人占有、使用、支配,“五五分成”的口頭約定與事實不符,丁某與請托人之間不存在真實的合作炒股關系。炒股行為僅為本案受賄行為的具體方式,丁某實際獲取的利益即106.85萬元均應認定為受賄數額。檢察機關指控丁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罪名成立,關于100萬元股本金亦為受賄款的指控,理據不足,不予支持。判決丁某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丁某沒有上訴。
筆者認為,法院判決對丁某行為實質的判斷是準確的,但在論證丁某行為的受賄性質,特別是在認定106.85萬元炒股利潤屬于受賄數額上,說理稍顯不足,沒有充分反駁對方觀點,有些自說自話之感,影響了作為司法判例的分量。當然,作為一起頗有爭議的受賄案例,本案判決無疑具有很高的實踐參考與理論研究價值。
*河北省人民檢察院[05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