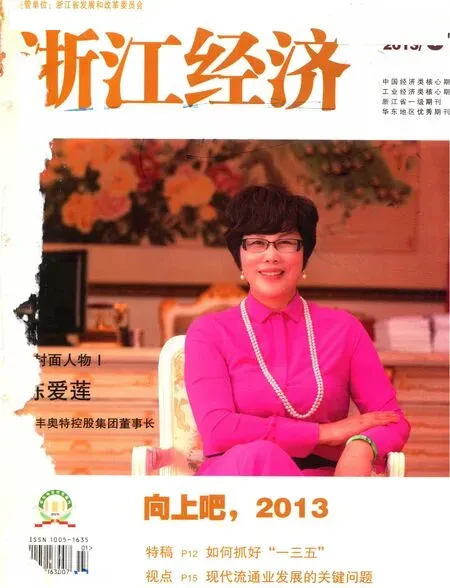好一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好一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城市化的本意,是“農村人口的城市化”,是“農民的轉移轉化”,是“農民工及其贍養人口的市民化”
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論及“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時,提出了一個鮮明的命題:“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明確指出:“要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緊接著,李克強副總理在主持召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調研工作座談會時再強調:“推動城鎮化,把農民工逐步轉為城市市民,需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這是“一個好命題”,就像2006年8月8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提出“新型城市化”一樣。
一是廓清了過往城市化的內涵。城市化,自制定“十五”計劃并同時見諸黨的正式文獻以來,大家耳朵聽得起繭,幾乎都達到了“爛熟于心”、“脫口而出”的境界。但是,城市化到底是個什么涵義,其實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單就國務院的各部門而言,發改委有發改委的城市化,建設部有建設部的城市化,中農辦還有中農辦的城市化,“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加之城市化和城鎮化的混用,字面上還有三分之一的不同,倒真是把人們生生“墮入五里云中”了。再看看這些年來所謂城市化實踐中的偏差,城市化更被理解為一種城市自身的規劃、管理和建設,一種城市自身的美化、綠化和亮化。
筆者一直堅持城市化的本意是“農村人口的城市化”,是“農民的轉移轉化”,是“農民工及其贍養人口的市民化”(詳見1998年10月,《城市化:我國跨世紀發展的戰略選擇》等文),現在看來,這些見諸于正式出版物的“白紙黑字”,還是站得住腳的。伴隨著生產方式的工業化,社會結構必然有一個城市化的同步跟進,這是客觀規律,是誰都別想繞過去的發展大勢。過去我們一心想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勒緊褲帶早日干成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所以采取了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一整套城鄉分割的體制。但沒有想到的是,新中國成立60多年了,這套東西愣是沒有實質性的變化。甚至是搞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這一塊依然是“年復一年、山河依舊”!
當然,農民進城打工是被允許了,沒有數億農民兄弟姐妹涌動的“民工潮”,就沒有“世界工廠”的美稱,也沒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桂冠,當然更沒有當下中國超過50%的城市化率。但是,這是真正的城市化嗎?不是,根本不是!可以這樣說,算不得有些專家痛斥的摻雜使假的“偽城市化”,起碼也是短斤少兩的“半城市化”!好了,現在有了十八大的“一錘定音”!我想,城市化的本意到底為何該是不言自明了;那種“見物不見人、要地不要命”的所謂城市化,也該得改弦更張、另辟蹊徑了吧。
二是明確了今后城市化的重點。城市化干了這么多年的城建,這方面的成績還是有目共睹的,但要做到“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還得讓農民工能在城里的二、三產業崗位上充分地就業才行,更得讓他們贍養的一家子老小,能夠在城市的房子里安穩地居住、均等化地享受到城里人同樣的教育、醫療、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才行。為了能夠承載真正的城市化所集聚的大量產業和人口,建好和管好城市都是必須的、不可或缺的。但是,城市不能只是新中國老體制下城市戶籍人口的城市,農民工只能是暫住者、是季飛的候鳥、是無根的浮萍。只允許農民打工而不接納其為市民的城市化,是無法擴大內需的城市化,也是無法促進社會進步的城市化。
在中國的國情下,“以人為本”的城市化,其實就是“以農民為本”的城市化,“因為農民是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又是中國人口中發展水平最低的一個群體。不‘以農民為本’,不但小康無從‘全面’,就是現代化也無從‘基本’(詳見2006年6月,《一個好命題》)”。所以于今開始,以后的城市化要拎得清重點何在了:不是人為再來一個“造城運動”,也不是官辦再來一個“換籍行動”,而是實實在在地怎么改革一切橫亙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道路上的體制性障礙,怎么造就一個農民工及其贍養人口在城里“安居樂業”、“有尊嚴地工作和生活”的環境!這一點恰如李克強副總理所言:“把城鎮化最大潛力和改革最大紅利結合起來,形成疊加效應,中國經濟就有長久持續的動力。”
好一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我們要的就是這樣的內涵和這樣的重點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