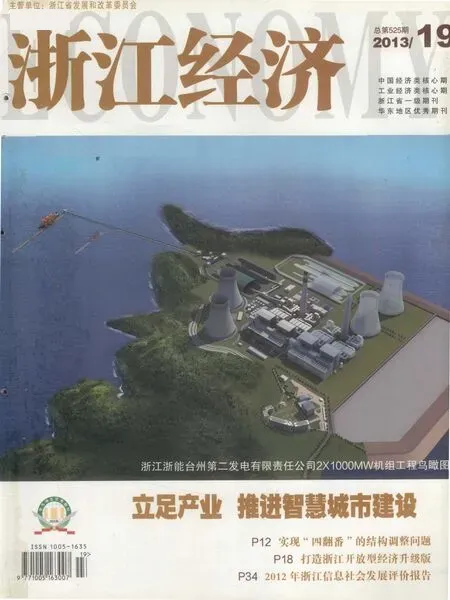“以房養老”之外的期盼
文/吳可人
“以房養老”之外的期盼
文/吳可人
“以房養老”只是養老的一種模式而已,緩解養老困境的當務之急是抓好改革
9月13日,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其中提到了要試點金融養老、以房養老,不料在國內掀起軒然大波,質疑聲四起。政府養老保障供給不夠、能力不足,造成公眾的養老擔憂。“以房養老”的提出,觸動了公眾的房子和養老雙重利益,產生較大抵觸情緒也在情理之中。
——養老金缺口讓公眾難以放心面對未來。2011年全國養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多達14個,收支缺口達766.5億元。浙江雖不在其列,但在通脹預期下,養老金保值增值壓力顯見。近十年來,浙江養老金資產構成中銀行存款比重超過90%,年均投資收益率不到2%,已呈隱形縮水態勢,未來養老金支付面臨挑戰。
——延遲退休年齡讓公眾產生養老悲觀展望。一項民意調查顯示,94.5%的受訪者反對延遲退休。有人坦言,對于工薪階層而言,延遲退休無異于剝奪了原本屬于他們的福利,加重其繳納養老金負擔。事實上,在多數藍領及低層次白領崗位中,老齡職工可能由于受教育程度和專業技術水相對較低、開拓精神相對較弱,處于未到退休年齡就已被市場“強制退休”境地,延遲退休年齡將延長其既無工資、又無社保的無收入狀況。
——全社會養老服務能力不足和養老醫療資源分配不公并存,老有所養任重道遠。以養老機構為例,公立養老機構收費不高、服務規范,但是一床難求;民營養老機構呈典型兩極分化狀況,服務好的收費較高,普通居民負擔不起;收費一般的服務大多不盡如人意,老人及其家屬都不太愿意去,民營養老機構尚難以成為養老服務資源的有力補充。
——較早進入老齡化促使浙江多途徑應對養老先行先試。浙江于1987年進入統計學意義上的老齡化社會,比全國早13年。長期來,浙江積極發揮民營經濟優勢,鼓勵支持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已取得較好成效。目前全省養老機構床位數25.8萬張,民辦機構占據48%之多,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成為政府提供養老服務的有力補充。
對于民營養老機構占據全省近半壁江山的浙江而言,民辦養老機構發展狀況直接決定全省的養老服務發展狀況。而筆者最近在金華等地調研中了解到,受多重因素影響,民辦養老機構發展困難重重。
體制機制制約較難破解。當前正是由于民營養老機構落地難、融資難、醫保定點難等問題未能得到有效解決,服務收費、人力資本積累、信譽等方面又難以與公辦實現公平競爭,民辦養老機構生存發展壓力較大。
人力資本需求較難滿足。老齡專業化護理和全科醫生緊缺。按平均每3名老人需要配備1名護理員計算,全省僅滿足當前居家和機構需要的養老護理人員就達10萬人左右,若按照至少滿足一半80歲以上高齡老人需要為標準,這個數據擴大至20萬人以上,但是全省目前僅有4萬養老護理人員。
多元定位較難實現。由于無法與實力懸殊的公辦機構競爭,民辦養老機構收費標準在相當時期內必須維持在較低水平。這一狀況影響民辦養老機構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提升,形成養老市場多元需求和民辦機構層次較低的矛盾,公辦機構“一床難求”與民辦機構“床位空置”的矛盾,進一步影響養老資源優化配置。
浙江老齡化形勢更加嚴峻,養老任務將愈加繁重。2012年,浙江老齡化程度17.9%,僅次于上海,列全國第2,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6個百分點。預計至2020年全省老年人口將達到1186萬人,占總人口比例達24.2%,接近總人口的1/4。
養老,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益。養老機構畢竟只能解決不到5%的老年人撫養問題,絕大多數老年人更需要的是居家養老。而浙江居家養老仍比較薄弱,特別是農村地區現有的居家養老服務站,大多僅能為老人提供一日三餐,較少能夠提供家政服務、醫療服務等,更難以實現對失能老人、臨終關懷等的照護。
說到底,“以房養老”只是養老的一種模式而已,緩解養老困境的當務之急是抓好改革。當前需要著力破解養老服務供給不足、水平不高,以及養老保障體制不完善等問題,同時積極應對多元化、品質化養老需求,鼓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養老事業。
(供稿: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